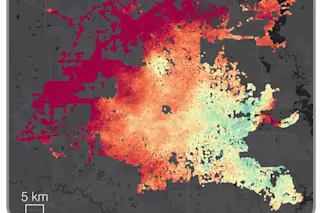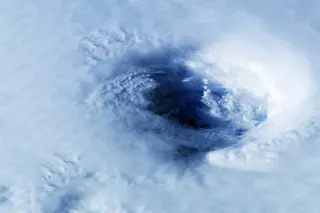气候安全问题,许多专家在此讨论串中讨论过,在美国政策和政治圈中日益受到重视。但正如我在去年十一月这篇报道中所写,“世界各地的军事和情报界也一直在建立一种紧迫感。”气候安全也已跃升为美国(见这里,这里,和这里)和英国智库议程的重中之重,在英国,Jeffrey Mazo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气候变化的安全和政策影响。Mazo刚刚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气候冲突:全球变暖如何威胁安全以及如何应对》。他在引言中写道:
科学证据毫无疑问地表明,气候正在因全球变暖而发生变化。过去,气候变化曾影响过社会、国家和文明的稳定,因此科学家们正在观察的历史上空前的变化,预示着在本世纪剩余时间和未来,社会、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动荡将日益加剧和加速。
昨天,我通过电子邮件对Mazo进行了简短的问答。
问:在您的新书中,您用一个章节来讨论史前时期气候变化导致国家衰落的案例。您的结论是:
很明显,气候变化并非总是导致收缩或崩溃,而且收缩或崩溃也可能在没有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发生。但气候不能被忽视,因为气候变化在历史上一直挑战着文化。它们应对挑战的方式,以及挑战本身的性质,为我们现在面临的空前变暖带来的安全挑战提供了一面镜子。
那么,我们应该关注某一个特别的历史案例吗?是否有某个国家成功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闪光例子?JM:确实没有一个闪光的例子,因为每种情况都是独特的。正是贯穿于各种不同案例的共同线索教会了我们宝贵的经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这有点像托尔斯泰的格言的反面:“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国家和文化在面对气候变化时往往以相似的方式失败,但成功的例子却各有不同。而最能揭示问题的是相同环境下的不同应对方式的配对例子,例如中世纪格陵兰的因纽特人和诺斯人,或者现代的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或者19世纪、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的美国西部干旱。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不同社会适应的能力是最重要的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社会能负担什么,但更关键的是一个社会或政治系统是否足够灵活,能否及时做出必要的改变来应对气候冲击。西方和整个工业化世界足够富有,至少在中期能够应对。但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灵活性是另一回事。然而,在短期和中期,最贫穷和欠发达的国家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得不够,我们可以在那里预期安全挑战的增加。问:近年来,达尔富尔一直被视为气候变化和族裔冲突的一个警示故事。在2007年《华盛顿邮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写道:
在各种社会和政治原因中,达尔富尔冲突始于一场生态危机,至少部分原因是由气候变化引起的。
但一些环境安全专家认为,将达尔富尔冲突归咎于气候变化或资源稀缺过于简单化,甚至在历史上是不准确的。在您的书中,您用一章来论述达尔富尔。您对此有何看法?JM:我认为环境安全专家在这点上的分歧仅仅是强调和视角的差异。达尔富尔冲突不是由气候变化引起的,如果您指的是气候变化是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的话。但事实上,在达尔富尔的案例中,距离一个简单、还原论的因果观越远,气候变化(可能还有温室气体引起的气候变化)就越是暴力事件的一个关键潜在因素。如果我们问“达尔富尔冲突是如何引起的”(或任何其他冲突),这就需要考察不同因素的相对贡献,以及它们是决定性的还是预测性的。可能存在任何数量的同等有效的答案,其中一些对于找到解决方案或分配道德责任更为相关。但如果我们问的是气候变化是否会引起(或导致冲突),达尔富尔就可以很容易地被用作证据。说其他因素在政治上或道德上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并不是否认达尔富尔在这个特定意义上是一场气候变化冲突。潘基文对达尔富尔冲突原因的解读,实际上比一些批评家所认为的更为细致。问:鉴于区分政治、文化和环境因素的难度,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将气候变化评估为一个合法的安全问题?JM: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一种方法是着眼于气候变化长期的、危险的、甚至潜在灾难性的影响,将其视为一种生存威胁,需要采取安全领域之外的必要措施来避免这些影响。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避免安全威胁,因此需要尽快减少排放并转向低碳经济。这并不是我在书中真正关注的,我的书侧重于短期和中期。在接下来的三十年左右(这是国防和安全规划的通常时间范围),其影响将如您所说,难以与政治和文化因素区分开来,尤其考虑到我们在这一时期预期的气候变化程度相对温和。在中期,趋势将更多地是“旧事重演”——公民动荡、暴力和内战等方面的渐进式、定量变化——而不是质变的新威胁,如资源战争、(海平面上升导致)海洋边界变化和(冰川融化导致)陆地边界变化。尽管我们可以确信安全威胁的总体数量会增加,但具体在哪里和何时显现是无法预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