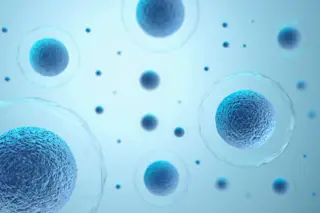我一直不太喜欢坐飞机。我知道很多医生也有同感:天性使然,我们喜欢掌控一切,而飞行意味着要放弃控制。
但我正要从 3000 英里外的一个会议返回家中,那段路开车太远了。所以,当飞机起飞时,我安顿在靠窗的座位上,做了我通常会做的事情:闭上眼睛,试图让自己入睡。
我上周一直在值班,可能已经精疲力尽了;接下来我醒来时,是我的邻座在推我。
“你说你是医生,对吧?”他急切地问道。“前面有人在找医生。”瞬间,我猛地惊醒了。
医学训练让我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所以当被告知有人“现在”需要医生时,我不会想到胃痛或焦虑发作——我想象的是心脏骤停。知道可能耽误不起时间,我挤过我这一排的两个人。前方十几排,一个年轻男子焦急地摇晃着他的邻居,他的身体笨重地 slumped 在座位上。“他醒不过来了!”那年轻人喘着粗气说。
我钻进座位排,把手指按在他的脖子上。我的新病人脸色蜡黄,眼睛睁着却无神,他没有呼吸。在他的颈动脉处,我找不到脉搏。
“把他弄到过道去!”我开始拉他的胳膊,但动不了他。前面排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探身过来,我们费力地把他弄到了过道上,他静静地躺在那里。他仍然没有呼吸,也探测不到脉搏,我双手交叠,开始有节奏地按压他的胸部。
萨缪尔·谢姆关于医学训练的小说《医学院》中有句名言:“心脏骤停时,第一步是检查自己的脉搏。”它提醒我们要深呼吸,排除恐慌,然后有条理地进行。
我遵循了处理心脏骤停的既定“ABC”算法——气道、呼吸、循环——但尽管我的胸部按压正在循环我病人血液中残存的氧气,制造了一种人工脉搏,但这显然不够。我需要更多帮助。
幸运的是,其他受过医学训练的乘客也站了出来。一个人接替了按压,另一个人将病人的头部向后倾斜,以便我们开始输氧。空乘人员带来了飞机后部存放的医疗设备。我停下来,开始协调我们的工作。
盲飞
即使在最佳情况下,医院内心脏骤停的患者也只有三分之一能存活到 24 小时。(而在医院外发生心脏骤停的患者,存活率不到十分之一。)
在医院,我会得到至少五名其他医务人员和一辆设备齐全的“急救车”来治疗心脏骤停。飞机上的设备没有那么齐全。我打开了除颤器,这是一组连接到心律监测器的粘性电极片,但发现它是为非专业人士设计的——没有屏幕显示心律。
该设备旨在 foolproof,只有一个开/关按钮和一个“电击”按钮。我将电极片贴在病人的胸部。“正在分析心律,”电脑语音说道。然后,几秒钟后:“未指示电击。继续按压。”
没有屏幕,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病人的心脏根本没有电活动——心静止——或者是否存在其他异常心律。只有少数心脏骤停是由室性心动过速或心室颤动引起的,这两种心律可以通过电击纠正。如果不能电击病人,我们就必须继续做心肺复苏,并尝试建立静脉通道输注药物,以帮助恢复他的脉搏。
工具包里有令人垂涎但又令人沮丧的各种选项。大多数常用的复苏药物都在这里,但我们只找到了一套静脉输液工具,一名乘客打开它,开始尝试将其插入我们病人手臂的静脉——在这架正在快速下降的飞机上,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对于医院内的骤停,一旦心肺复苏开始,就有人需要开始考虑可治疗的原因。例如,如果我们知道病人高钾血症,我们可以针对性地治疗,而不是仅仅遵循一套通用的方案。通常,“有人”是响应呼叫的众多专业人员之一,而不是领导者或进行胸部按压的人。
尽管如此,我还是快速地在脑海中梳理了主要的诱因。严重的酸中毒,或严重的血液化学失衡?很难想象在飞行中会发生这种情况,而且我手头无法进行检测或治疗。
大血栓?这可能发生在飞机上,因为活动不足(“经济舱综合征”),但在短途飞行中相当罕见。
气胸,当空气积聚在肺和胸壁之间时,可能会在高空发生并导致心脏骤停,但这通常会将气管推向一侧;我们的病人的气道是完全居中的。
循环血量过少?如果有人脱水或大量出血,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对我来说,两者都不明显。
病历可能会提供线索,但当然当时没有。但我偶然看到了病人从裤兜里掉出来的钱包。我抓起它,几乎立刻找到了我想要的:一份药物清单。
另一句好的医学格言是,80% 的诊断仅凭病史就能做出。这个病人无法说话,但他服用的药物清单却能说明一切。看到几种降压药和一种抗凝药,我推断他有心脏病和高血压。
锁定在直立位置
我想到狭窄的飞机座位,以及我们发现病人时的姿势:直立但失去知觉。也许他的药物导致血压偏低,他晕倒了。由于无法倒下,他一直直立着,无人察觉,大脑供血不足,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心脏骤停。
在智能手机出现很久以前,这种潜在致命的组合就被称为“电话亭晕厥”。摔倒是身体保护自己免受低血压的方法,因为它能利用重力帮助现有血压将血液输送到大脑。晕倒并被保持直立,就像在老式电话亭里,或在飞机座位上,或当好心旁观者在某人昏倒后将其扶直时,都可能促使中枢神经系统关闭——特别是大脑控制的呼吸。
如果这个病人患了电话亭晕厥,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将血液输送到他的大脑。胸部按压有帮助,我们也在准备给他输液药物。现在我们抬起了他的腿,以帮助恢复中心循环。
尽管这种干预非常低技术,但在我们进行时,病人开始微弱地移动。我感觉到手腕上有一个微弱但稳定的脉搏。几秒钟后,我感觉到一个震动:飞机已经着陆。
感觉像是过了一个世纪,但飞行员找到了一个机场,并在我们的复苏工作开始不到 30 分钟内就着陆了。着陆后几分钟,急救人员就登机了。我用 30 秒的时间向他们简要介绍了情况,病人被装上担架带走了。机长叫我到飞机前面,我告诉他我所认为发生的情况。
“干得好,”他说。“现在,你怎么看这次紧急着陆,嗯?”我告诉他实话: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这次着陆的担忧是我的最后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我的病人后来怎么样了;我甚至没问到他的名字。但自从这件事发生以来,我一直想着他。飞机上心脏骤停的生存率是 7:1。
但长期生存率实际上取决于事件的原因。而且我乐观地认为我的诊断是正确的。研究表明,飞机上的诊断在病人到达医院后往往得到证实。如果问题是电话亭晕厥,他很有可能存活了下来。
[这篇文章最初以“凌空而起”的标题刊登在印刷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