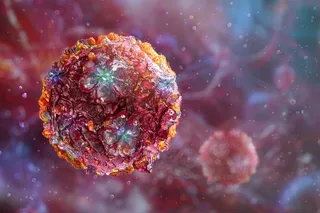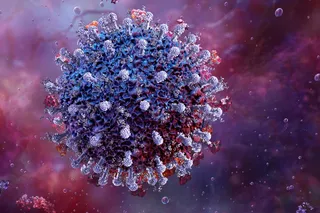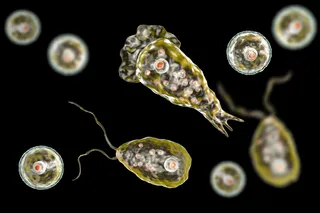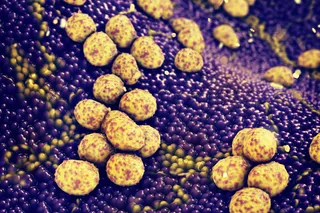2019年,内科医生Lydia Kang与图书管理员兼历史学家Nate Pedersen合作撰写了一本书。两年后,他们的著作《零号病人:世界上最严重疾病的奇特历史》问世,深入探究了众多令人恐惧的人类疾病的确切起源。这些详尽的章节证明,流行病学工作很少是一帆风顺的,这是我们今天都太熟悉的一个教训。
当Kang和Pedersen研究从中世纪麦类谷物引起的幻觉,到20世纪80年代令人费解的疯牛病疫情,再到2001年的炭疽袭击时,COVID-19悄然在中国武汉爆发。Discover杂志采访了两位作者,了解当前疫情如何影响了他们的工作——以及我们在应对疫情时是否会从过去的失误中吸取教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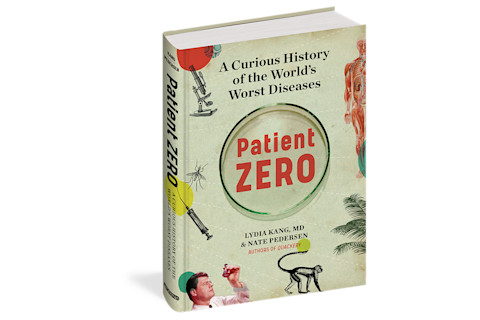
(图片来源:Workman Publishing)
Workman Publishing
问:COVID-19的出现如何影响了您的写作过程?它是否强化了您研究的疾病疫情的某些历史模式?
LK:就在我们筹备提案和撰写章节时,我们听到了中国出现疫情的最初迹象。老实说,我们当时认为这只是个小插曲——总会有一些担忧出现,然后又被压下去。所以,这有点令人震惊。
关于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章节尤其触动了我。这次疫情与那次流感大流行有很多相似之处,人们抵制戴口罩的规定,以及各种江湖骗术盛行,人们试图用尽一切办法来治疗这种疾病。和每一次大流行病一样,也存在关于其起源的问题。我们关于那次流感疫情的章节有很多内容都涉及其起源,因为如果我们能回答这个问题,或许就能帮助我们弄清楚如何应对其他的疫情。
NP:在我们(至少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经历这种全球性事件的同时,这本书的销售时机很有意思。我认为很多人已经把大流行病视为历史记录,仿佛我们已经超越了它们。这样想很容易,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过去一年半里,我们都非常直观且痛苦地被提醒了这一点。

作者Lydia Kang是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一名执业内科医生。她曾于2017年与Nate Pedersen合作出版了《Quackery: A Brief History of the Worst Ways to Cure Everything》一书。(图片来源:Workman Publishing)
Workman Publishing
问:考虑到看似层出不穷的传染病可能性,这本书是否影响了您对待日常生活的方式?
NP:从某种程度上说,COVID-19并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我们最近研究过很多更糟糕的疾病和疫情。这并非贬低这次疫情的严重性以及因此丧生的人数,或者健康受到严重负面影响的人们。但与我们涵盖的某些疾病相比,死亡率仍然相去甚远。
书中还强调了人类物种令人印象深刻的韧性:在历史上,从比COVID更糟糕的疾病中一次又一次地复苏的能力。

Nate Pedersen是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一名图书管理员、历史学家和自由撰稿人。(图片来源:Workman Publishing)
Workman Publishing
问:您认为为什么人们在疫情期间倾向于归咎于他人,特别是针对边缘化群体?
LK:当我们写这本书并决定书名时,有很多的顾虑,因为我们意识到书名本身听起来就带有指责的意味。我们想给人们一个惊喜:我们指出“零号病人”这个概念,虽然它在流行病学和寻找病因以理解疾病方面非常重要,但它本身是一个有缺陷的概念。
NP:一场可怕疾病的爆发,就成了人们倾泻其他社会不平衡情绪的载体。人们倾向于将愤怒发泄在边缘化的“他者”身上,或者发泄在他们认为是疾病来源的任何对象上。
LK:在上个世纪之交,当鼠疫传入美国时,存在着巨大的排外情绪,人们指责华裔美国人给他们的土地带来了这场灾难。旧金山的唐人街被隔离了,尽管他们会允许白人离开,但却把华裔美国人关在这个区域。围绕这场最初疫情爆发产生的种族主义和排外情绪,与今天惊人地相关。旧金山市长当时在1920年参议员竞选时使用的口号“让加州保持白色”(Keep California White),让我不寒而栗,因为我觉得它听起来太熟悉了。
问:您研究的任何疾病是否特别引起了您的兴趣或令您感到惊讶?
NP:最令人惊讶的章节之一是关于狂犬病。在研究这本书之前,我不知道狂犬病毒的致命性有多高:在疫苗出现之前,它基本上是绝症。这种病毒几乎太擅长致死了,因为它降低了传播的机会。它有一些非常不寻常的症状,让我感到惊讶,比如恐水症。
LK:有几章对我来说写起来特别困难,包括关于艾滋病起源的章节。有很多文章需要挖掘,关于它在哪里发生的。许多其他作者也做过这个研究,他们花了整本书来写。我却不得不在一个章节里完成。
在我纽约市贝尔维尤医院的住院医师培训期间,我们总是有一个轮岗在病毒病房,几乎专门收治艾滋病病毒感染患者。那是90年代初,我太年轻了,没能经历80年代发生的一切。我当时身处一个开始有药物可以使用的时期,但病人仍然病得很重,这仍然是绝症。
在我最后一次轮岗在那里,我不小心被针头扎到了,我记得当时想,我会得艾滋病吗?我会吃药吗?我感到了那种恐慌,因为我知道这段历史,知道这是一种绝症,而且可以通过这样细小的针头感染。
我们最终将那部分内容从章节中删除了,但考虑到我曾照顾过艾滋病患者的历史,那是一次非常奇特的经历。那绝对是一次跌宕起伏的经历。
问:像mRNA“即插即用”疫苗这样的新技术,是否让我们比过去的几代人在面对下一次严重的传染病时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流行病学的社会层面又如何呢?
LK:科学方面正在变得越来越好。对于COVID,在武汉出现了几例奇怪的病例和死亡。他们在得到样本后的几天内,就获得了样本和病毒的DNA序列。
检测和疫苗的开发速度异常快。阻碍这一切的都是政治、金钱和国际上的虚张声势。在很多方面,科学的东西更容易,也更直接。在这个个人主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选择权都如此重要的时代,要做好公共卫生工作是很困难的。这很可能在未来每一次重大疫情或大流行病爆发中都会出现。
随着数据不断涌现,人们对于“移动的针头”(指不断变化的科学认识)感到非常不适。你会得到看似毫无争议的信息,但问题是,任何一项研究的完成,所有的数据都是可以争论的:研究是如何进行的;可能的偏见;谁支付的费用。有无数因素会影响这些数据是否可靠。
NP:科学自我反思非常重要。这才是关键:反复审视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效的方法和最佳策略会浮出水面。希望这能为未来的决策提供信息。
LK:我认为问题在于人们没有耐心,所以往往没有时间让事情自行解决。然后在这个过渡期,当对数据和科学存在不确定性时,这种不确定性就被武器化了。这可能是自疫情爆发以来,科学家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士一直在斗争的一个主要问题:虚假信息的武器化,以及利用对研究结果的不信任或不确定性,将其引向一个非常可怕和危险的境地。由于科学的本质,这个问题不会消失。
本次采访经过编辑和精简,以求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