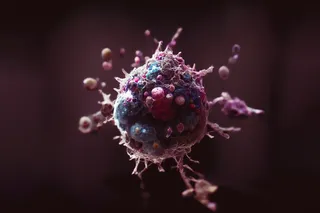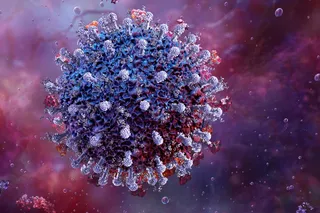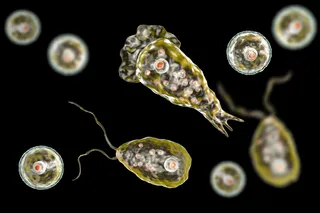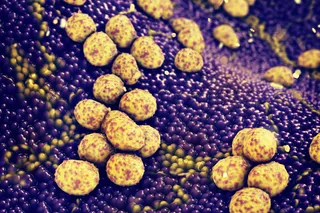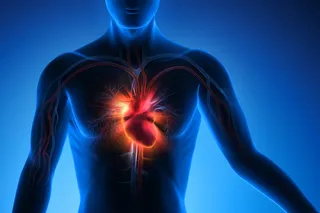本文最初发表于我们 2023 年 9 月/10 月刊,题为“有效利他主义病毒式传播”。点击此处订阅以阅读更多此类文章。
Paresh Patel 以前害怕打针。然后他志愿感染 COVID-19。当他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得知英国牛津大学的科学家正在寻找愿意感染 SARS-CoV-2 病毒的志愿者时,Patel 报了名。他已经在 2020 年 10 月感染并康复了 COVID。除了几天内失去了嗅觉和味觉外,这次经历并无大碍。
而且,他才 27 岁,年轻、健康,没有基础疾病,所以他不担心血栓、呼吸困难甚至死亡等潜在风险。
“奇怪的是,我唯一担心的是打针,”他说。Patel 希望他能帮助科学家研究这种病毒——同时顺便进行一些业余的暴露疗法来治愈他的针头恐惧症。
当 Patel 报名参加牛津试验时,他成为了全球近 40,000 名通过 1Day Sooner 志愿参与感染试验的人之一,1Day Sooner 是一个倡导更广泛采用人体挑战试验的非营利组织。在这些试验中,参与者自愿暴露于一种疾病,以便科学家研究他们的免疫反应并测试疫苗和治疗方法。这类试验对于开发疟疾和黄热病疫苗至关重要,1Day Sooner 认为这将加速 COVID-19 疫苗的问世,可能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
尽管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对于试验是否有用——更不用说是否符合伦理——存在分歧,但 1Day Sooner 的创始人还是继续前进,组织了国会简报会,撰写了观点文章并招募了志愿者。位于美国并在英国和非洲设有分支机构的 1Day Sooner 的总裁兼联合创始人 Josh Morrison 表示,监管临床试验的体系过于家长式。“人们应该有权做出影响自己生活的决定,”他说,并且知情者应该被允许选择他们愿意承担的风险。
但事情并未按计划进行。乔治城大学肯尼迪伦理学研究所所长 Daniel Sulmasy 说:“就英国的 SARS-CoV-2 试验而言,1Day Sooner 的结果晚了三天。”“在实验完成之前,mRNA 疫苗就已经问世了。”
1Day Sooner 可能错过了加速 COVID 疫苗问世的机会,但该组织本身仍在蓬勃发展,它是受一种被称为有效利他主义(EA)的流行哲学理念启发的更大运动的一部分。EA 的前提是人们应该利用自己的时间、金钱和精力以最大化地造福最多的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它已从一个狭 niche 的学术概念发展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捐助者、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生态系统。
但关于 1Day Sooner 方法的争论以及该组织在实现 EA 看似简单的原则方面遇到的挑战,都体现了在现实世界中执行这些原则所面临的一些挑战。计算出最“有效”的行动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再加上人体医学试验令人不安的历史、专家之间的分歧以及全球大流行的紧迫性,你就面临着一个伦理困境,暴露了该运动的潜力和潜在的危险。

“对抗疟疾基金会”是 EA 最常见的捐赠目标,该基金会向高危人群提供抗疟疾蚊帐。(图片来源:Mile 91/Ben Langdon/Alamy Stock Photo)
Mile 91/Ben Langdon/Alamy Stock Photo
道德义务
有效利他主义的哲学根源在于功利主义。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像 John Stuart Mill 和 Jeremy Bentham 这样的理论家提出,个体应尽可能地增进幸福并减少痛苦,这符合社会的最大利益。因此,行动可以根据其带来的幸福与造成的痛苦的比例来评判。粗略地说:在功利主义中,目的可以证明手段是正当的。
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 Peter Singer 在 1972 年将这些想法推进一步。在一篇题为《饥荒、富裕与道德》的文章中,Singer 将西方世界在当时的东孟加拉邦发生的严重饥荒期间的袖手旁观与眼睁睁看着一个孩子溺水而无动于衷相提并论。他认为,捐钱帮助有迫切需求的人不是慈善,而是道德义务。
几十年后,Singer 的著作启发了前对冲基金分析师 Holden Karnofsky 和 Elie Hassenfeld。2007 年,两人创立了 GiveWell,一个评估不同慈善机构有效性的组织。Singer 还启发了哲学研究生 Toby Ord 和 William MacAskill,他们于 2009 年承诺将自己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捐赠给慈善组织。两年后,他们启动了一个在线社区,以识别全球性问题,寻找并实施解决方案,并研究这些解决方案对现实世界的影响。这些组织汇集在“有效利他主义”这个总称下。
简而言之,EA 将 Singer 的行动呼吁与功利主义思想相结合,即认为一项行动的良好效果可以量化和比较。在 Facebook 和 Asana 的创始人之一 Dustin Moskovitz 和他的妻子 Cari Tuna 决定在有生之年捐赠大部分财产后,该运动才从一个相对较小的社区发展起来。这对夫妇于 2011 年与 GiveWell 合作,利用该组织的分析,最大化地发挥他们金钱的影响力。自那时以来,Tuna 和 Moskovitz 已成为关键人物,向 EA 智库和事业捐赠了数百万美元,并经常在推特上谈论其原则。这种哲学在 Skype 联合创始人 Jaan Tallinn 甚至 Elon Musk 等科技亿万富翁中广受欢迎。
对于 1Day Sooner 的联合创始人 Josh Morrison 来说,EA 社区和哲学激励他成为一个最好的人。2007 年,Morrison 是一名成功但不满足的公司律师,当时他决定将自己的一颗肾脏捐献给陌生人,这一举动受到了 Singer 思想的启发。(尽管他指出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读过 Singer 的任何文章。)“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极其积极的经历,”他说。为了继续追求这种积极的感觉,他创立了 Waitlist Zero,一个致力于通过使人们更容易将健康的肾脏捐赠给需要的人来解决全国肾脏短缺问题的非营利组织。当 COVID-19 到达纽约时,Morrison 和其他有效利他主义者组成了一个团队,创立了 1Day Sooner。

医生向患有梅毒的黑人男性提供了安慰剂(并告知他们正在接受治疗),同时拒绝向他们提供青霉素等药物,这是从 1932 年到 1972 年进行的塔斯基吉梅毒研究的一部分。(图片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美国国家档案馆
哲学付诸实践
到 2020 年底,当 Patel 将自己的名字添加到一份愿意参加牛津挑战试验的名单时,世界卫生组织已报告了超过 170 万例 COVID 死亡。Patel 居住的英国感染率居世界前列,病例数不断攀升。人们渴望提供帮助,参与科学试验似乎是一种为更大利益做出贡献的真实、切实可行的方式。
2021 年 5 月,Patel 成为牛津试验中第一个自愿感染 SARS-CoV-2 病毒的人。他在牛津大学约翰·拉德克利夫医院的一间病房里住了两个多星期,白天远程工作,晚上与朋友视频聊天或看电影。他的母亲很担心他,但他的朋友和同事大多支持他。
然而,许多医学伦理学家并不支持。创造一个思想实验是一回事;将其付诸实践又是另一回事。关于哪些问题最重要,哪些解决方案值得投入时间和金钱的无休止的辩论在 Twitter、在线博客和 LessWrong、有效利他主义论坛等讨论组中激烈进行。答案往往有些令人惊讶。
例如,EA 最常见的捐赠目标之一是“对抗疟疾基金会”,这是一个在非洲分发抗疟疾蚊帐的组织。该非营利组织报告已分发 2 亿顶蚊帐,并估计已阻止 15 万人死亡。每顶蚊帐 2 美元,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投资回报——理论上,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做出改变。有效利他主义者会认为,这比向当地食物银行捐款更能“物超所值”,因此是更好的花钱方式。
但牛津试验并非关于捐款去处的在线辩论。EA 已从理论领域转移到一个非常现实的局面,即 1Day Sooner 要求人们冒着健康和安全的风险。
决定何时可以进行人体挑战试验需要权衡一系列复杂的变量,包括人体医学试验的漫长历史。研究人员曾以科学和人类福祉的名义犯下许多虐待行为。1932 年,美国政府开始了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研究,他们招募了已患有该病的黑人男性,并拒绝为其治疗,以研究其进展。后来,在 1946 年,美国在危地马拉感染了 5000 多名不知情且未经同意的人,让他们感染了梅毒和其他性传播疾病。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纽约斯塔滕岛 Willowbrook 州立学校的医生强迫家长同意进行故意感染发育迟缓儿童肝炎的研究。这些实验一直持续到 1970 年代。
为了应对这些侵犯行为,国会于 1974 年通过了《国家研究法案》,要求机构审查委员会评估何时适合使用人体受试者,英国也有类似的规定。这些要求很多,并且与 EA 的标准明显不同。为了证明挑战试验的合理性,研究人员必须证明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收集他们想要的 数据;研究设计必须良好;疾病必须是自限性的,意味着它不会有严重的、长期的并发症;并且必须有一些救援疗法来防止参与者死亡。除此之外,参与者需要代表科学家希望治疗的人群,而不会给无家可归者、儿童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带来额外的负担。
尽管自 Willowbrook 和塔斯基吉等事件的恐怖以来,美国和国外已通过了许多法律,但美国伦理学家仍然警惕重蹈覆辙。那些过去的、严重的错误对于创建当前的研究结构至关重要。尽管像 Morrison 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可能认为该体系是家长式的,但 Sulmasy 认为这些保护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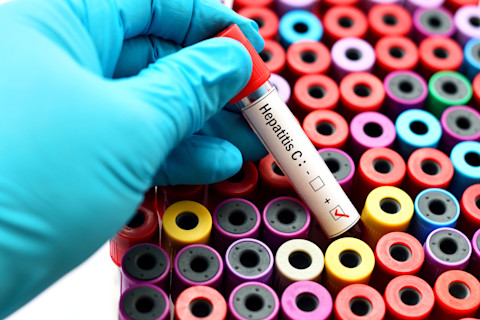
(图片来源:Jarun011/iStock via Getty Images)
Jarun011/iStock via Getty Images
大多数时候,医学伦理学家会逐案辩论人体挑战实验的优点——而且他们并不总是达成一致。“这将是一个善意人士得出不同结论的算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伦理学伯曼研究所所长 Jeffrey Kahn 说。在英国,一个由 18 名经验丰富的成员组成的伦理审查委员会认为,牛津 COVID-19 试验将揭示新信息,研究人员可以通过仔细审查参与者并在高度受控的医院环境中对其进行研究来管理长期 COVID 和严重感染的风险。但 Kahn 和其他人认为,在 2021 年,牛津试验是危险且不必要的。没有救援疗法,也无法预测参与者是否会患上长期 COVID。“这就像在赌博,”Kahn 说。“这太疯狂了。”
Sulmasy 同意。“确实,在最初的 SARs-CoV-2 试验中没有人死亡。但有人可能已经死了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任何否认这一点的人都大错特错了,”他说。现在,有了 Paxlovid 和 Remdesivir 等治疗方法,Sulmasy 认为运行这些试验会更安全、更符合伦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需求不再像以前那样迫切了。
挑战试验常常陷入一个悖论:尽管通过感染参与者患上一种致命疾病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实际这样做可能是不道德的。与此同时,一种不太严重的疾病可能不值得进行试验。而且,科学家对一种未知的疾病了解不够,无法就是否适合给予志愿者做出明智的判断。
71 次生命体征检查,31 次鼻拭子和喉拭子,17 天的住院治疗和 8 次血液检查后,Patel 带着阴性的 PCR 检测结果走出了约翰·拉德克利夫医院,并且对针头的恐惧有所减轻——尽管他承认它们仍然让他紧张。他不后悔这次经历,但他也没有抓住机会报名参加其他任何试验。
与此同时,1Day Sooner 继续推进,在科学期刊上撰写观点文章,起草政策建议,为丙型肝炎挑战试验招募志愿者,并游说将挑战试验纳入美国的国家大流行病防备计划。Morrison 继续认为,知情的参与者应该能够选择是否承担挑战试验带来的风险。“当专家之间存在分歧时,就应该听取直接受影响者的意见,”他说。对他来说,道德计算很清楚:像肺结核、丙型肝炎和 COVID-19 这样的疾病导致数百万人死亡,而挑战试验可以发挥作用。
尽管如此,参加挑战试验并非易事。1Day Sooner 和更广泛的 EA 的假设是,人们可以在良好的数据和证据的指导下自由地做出关于自己的决定。但报名参加挑战试验不仅仅是个人决定。人体试验和疫苗研究涉及政府、基金会和研究中心的大量资金。这笔资金是一种隐含的认可,它给研究参与者增加了一层分量和压力:为了国家、经济和人类的福祉而做这件事。
Kahn 使用了 Peter Singer 五十年前使用的类比:想象一个孩子正在溺水。政府不会设置围栏来阻止人们冲进去拯救他们。另一方面,也没有制度压力推动人们跳进去。当政府开始要求人们冒生命危险去为他人牺牲时,就需要达成共识,认为回报足够大,足以承担这项请求。“人们想牺牲自己并被称为英雄,”Kahn 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机构应该要求他们“躺在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