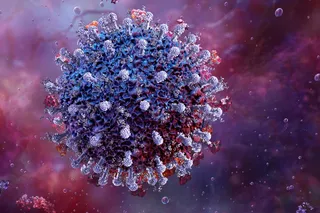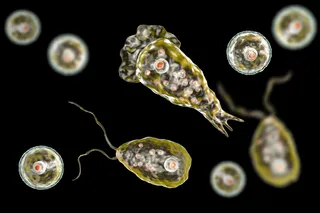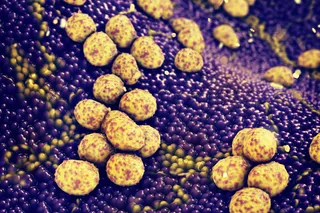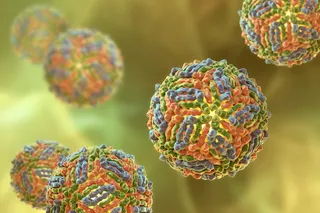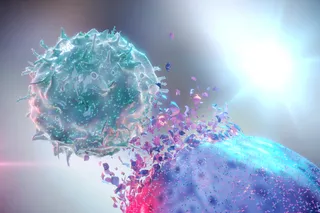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市一个晴朗的清晨,彼得·杜斯伯格推着他的自行车沿牛津街前行,同时兴致勃勃地解释他关于癌症的新理论——全然不顾自己即将走到一辆汽车前面。作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分子与细胞生物学教授,71岁的杜斯伯格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他身材瘦削,白发,五官分明,今天穿着一件黑色皮夹克,里面是纽扣衬衫。癌症是他长久以来的热情所在,一个他研究了40多年的课题。如今,他关于该疾病起源的激进理论终于赢得了郑重的关注。
他如此专注于谈话,以至于灾难即将发生时才抬头看到那辆朝他驶来的汽车。杜斯伯格咯咯地笑了起来,仿佛在享受一个私人的笑话,然后退回到路边,把自行车也拉了回来。但还没等他完全回到人行道的安全地带,他又继续解释起了非整倍性,这是他癌症成因理论的基础。
杜斯伯格对争议——或迎面而来的车辆——并不陌生。1987年3月1日,他在《癌症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质疑HIV在引发艾滋病中的作用。这篇论文成了一条分界线,将杜斯伯格划分为两面:一面是生物学界的天之骄子——他是最早绘制逆转录病毒基因结构的团队成员之一,1970年共同发现了第一个病毒性癌症基因,一位聪明的批评家;另一面则是杜斯伯格这个恶魔。
杜斯伯格说,在该论文发表前的23年里,他申请公共研究资金从未被拒绝过。1986年,49岁的他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同年,他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杰出研究员奖,这是最负盛名、最令人垂涎的资助之一。HIV的共同发现者、杜斯伯格的前朋友罗伯特·加洛(Robert Gallo)在1985年曾称赞他“精力非凡、异常诚实、极富幽默感,并具备罕见的批判意识”。他补充说:“这种批判意识常常让我们对许多人已认定为定论的结论,再三审视。”
自1987年那篇关于HIV的文章发表以来,杜斯伯格成了科学家中的“贱民”。他超过20项政府资助的申请被拒。艾滋病活动家在公开抗议和媒体宣传中谴责他。朋友们,包括加洛在内,都离他而去。他的实验室曾配备两名秘书和众多研究生、博士后,如今只剩下杜斯伯格本人和一名研究生——尽管仍有本科生进进出出。他没有秘书。他的妻子会帮忙充当助手,她低声谈论着丈夫被学术界、社交活动和正常生活排斥在外的痛苦。
那些以言辞谨慎著称、曾经可能称杜斯伯格为生物学界爱因斯坦的温和科学家们,如今对他恶语相向,发表着伤人的评论,而他声称这些话对他毫发无伤。为了尖锐地影射那些否认纳粹大屠杀的人,他和那些挑战“HIV是艾滋病病因”这一主流观点的其他人被贴上了“否认主义者”的标签。
这个标签不无讽刺意味。杜斯伯格于1936年出生在德国明斯特的一个医生家庭;他的母亲是眼科医生,父亲是著名且具有开创性的内科医生。尽管欧洲很快将战火纷飞,杜斯伯格却形容他的童年出奇地田园诗般,那段时光里他沉浸在玩乐和小恶作剧中。作为一名祭坛助祭,他负责在天主教仪式中手持燃烧着熏香的香炉。杜斯伯格发现,比必要速度更快地摇摆香炉很有趣,产生的浓烟让教区居民咳嗽不止。这对他和其他祭坛助祭来说是件乐事,而当神父们责骂他们时,乐趣反而增加了。他享受在德国与奥地利、瑞士交界的康斯坦茨湖度过的夏天,在那里他游泳、骑自行车,和别的孩子一起玩游戏,“仿佛没有明天”。
杜斯伯格坚称他当时免受战争的影响。然而,即使在他生活和玩耍的小镇上,战争也远非无形。“我仍然记得……收音机里的那些演讲,”他说。“我们本应相信‘最终胜利’。”他的老师,夹克上别着纳粹十字记号,告诉全班德意志帝国将凭借“奇迹武器”(Wunderwaffe)赢得战争。
“我们当时太年轻,没把这事太当真,”杜斯伯格说,并补充道,预警轰炸机来袭的警报声反而激起了一种男孩式的兴奋感。“我们会去看炸弹,收集碎片,”他说。但在1944年12月25日,当警报响起,杜斯伯格一家躲进一个临时防空洞时,位于法兰克福附近克罗伊茨纳赫海因里希街11a号的家被炸了。直到后来的一次谈话中,杜斯伯格才承认,即使在今天,伯克利街头的消防车或救护车警报声仍会激起他一种原始的恐惧反射——这是战争年代的持久影响。
杜斯伯格的父母都是鄙视政治的知识分子,他们无法或不愿公开对抗纳粹的威胁。为了逃避加入纳粹党的压力,杜斯伯格的父亲自愿参军。在俄罗斯担任医生后,他在比利时被英军俘虏,并在英国作为战俘被关押了一年,之后于1946年获释返回德国。战后不久,杜斯伯格的父母分居了。
杜斯伯格对自己的出身很在意,战争和他父亲在德军中的角色或许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这一点。这些因素可能也为他身上至今仍存的复杂、令人不安的一面埋下了种子。当被问及他的父亲时,杜斯伯格表现得异常克制,甚至 evasive。他对问题耸耸肩,脸上既无亲情也无怒气。当被问及他父亲对心血管休克理解的开创性贡献时,这位功成名就的儿子谦虚地说:“我并不真正了解他的休克理论是什么。”
然而,就像他父亲一样,科学定义了杜斯伯格的一生。战后岁月带来了“科学的巨大飞跃”,他说。聚合物(即重复的蛋白质链)的发现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这是胰岛素序列被测定的时期,”他说。“这是高中生们谈论的话题。”
起初,杜斯伯格的兴趣在于化学聚合物而非生物聚合物。新发明的可能性似乎无穷无尽。然而,在他于1963年从法兰克福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后,他的一位教授西奥多·维兰德(Theodore Wieland)告诉他,最重要、最激动人心的工作是在寻找被认为导致癌症的病毒。杜斯伯格记得维兰德建议他:“去西部吧,年轻人。去西部。”杜斯伯格认为这会让他“名利双收”,于是决定采纳教授的建议,移居美国。
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杜斯伯格全身心投入他对科学的热情,远离故土数千英里。即便如此,他的谈话中,无论话题如何,仍然充满了二战的比喻和对希特勒及其党羽的提及——以及对那些遵从政府要求的“好德国人”的提及。有时很难理解他,不仅因为他尖锐的德国口音和奇怪的措辞,还因为他的思维跳跃会让听者筋疲力尽。他会迅速地从科学细节跳到宏大的政治比较(病毒、细菌、癌基因,甚至研究这些实体的研究人员都可以被转化为戈培尔或“好德国人”),然后他可能会抛出一个全新的想法,几秒钟内又回到最初的话题。1964年,杜斯伯格作为博士后研究员来到伯克利,希望解开癌症的秘密。他最近沿着大学里长而平缓的小径散步,回忆起他早期癌症研究的兴奋,以及他如何加入寻找逆转录病毒的行列。当时,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几乎所有癌症都是由病毒引起的。逆转录病毒被认为是可能的罪魁祸首,因为它们能使细胞过度增殖。
通过将它们的遗传物质插入宿主基因组,它们会引发细胞增殖,有时还会形成肿瘤。1911年,佩顿·劳斯(Peyton Rous)证明,一种现在称为劳斯肉瘤病毒(RSV)的逆转录病毒,在注入健康的鸡体内后可以产生肿瘤。1970年,杜斯伯格和同事彼得·沃格特(Peter Vogt)分离出了导致这些肿瘤的RSV基因——SRC基因。这是有史以来发现的第一个癌症基因,即癌基因——一个广受赞誉的突破,真正让这位年轻的德国人在科学界崭露头角。
在此基础上,哈罗德·瓦慕斯(Harold Varmus)和J·迈克尔·毕晓普(J. Michael Bishop)于1976年在正常人体细胞中发现了同源的SRC基因,他们后来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当时认为,人类或“细胞”的SRC基因经过突变后会引发癌症。这开启了癌症研究的新时代,引发了寻找癌症基因的狂潮,这些被一位研究员称为“内在敌人”的小定时炸弹,据说存在于原本正常的DNA链上。
杜斯伯格并没有沉浸在作为首位分离出癌基因的荣耀中,反而开始怀疑敌人是否真的在“内部”。他开始怀疑癌基因并不会导致癌症。杜斯伯格说,要证明它们能致癌,研究人员应该能够通过将人类癌症基因插入人类细胞,在细胞培养中制造出癌症。但经过二十年、数百万美元的公共和私人资金投入,以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癌症研究人员的最大努力,杜斯伯格说,没有任何基因组合曾在组织培养中产生过癌症。
这一点遭到了许多备受尊敬的癌症研究人员的强烈反驳,例如马萨诸塞州剑桥怀特黑德生物医学研究所的罗伯特·温伯格(Robert Weinberg)。温伯格同时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生物学教授,他说他通过添加癌基因在培养皿中制造了癌细胞——他强调,成百上千的其他人也做到了。“这一点没有争议,”温伯格说。“这就像白天是否跟着黑夜,或者3是否跟着2一样无可争议”——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争议。但杜斯伯格坚称温伯格的实验被错误解读了;他现在说,那些实验中看到的染色体缺陷是癌症的原因,而不是结果。
尽管杜斯伯格取得了开创性的工作、获得了荣誉和联邦拨款(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中期),一旦他开始质疑癌基因作为癌症病因的公认角色,他的同事们便开始对他冷眼相待。他们鄙视的证据是令人尴尬的公开的。
大约在1984年,当他的一名学生指出杜斯伯格没有参加一个研究肿瘤病毒的科学家的西海岸会议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再被邀请参加这些非正式会议了。在过去的12年里,杜斯伯格定期与他的同事们会面,包括彼得·沃格特和诺贝尔奖得主瓦慕斯和毕晓普等人。“我们有过激烈的辩论,”杜斯伯格说。“但我认为那是好的科学。你挑战思想。我以为那都是出于善意的。”其他研究人员不这么看。杜斯伯格不断喋喋不休地谈论癌基因作为癌症病因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一种干扰,甚至是阻碍。于是他们干脆不再邀请他参加会议。他们不回复他的信件和电话。他们不再欢迎他在外地开会时住在他们家里,而过去他们是这样做的。
温伯格在20世纪70年代初次见到杜斯伯格,称他是个“逆向思维者”,有着“腐蚀性和尖酸的机智”。他觉得是这些特质,而非科学本身,后来引导杜斯伯格决定挑战HIV理论。“他就像一个在岛上遭遇海难的人,挣扎着爬上海滩,环顾四周,然后说:‘这里有政府吗?如果有,我就反对它。’”
1984年,当杜斯伯格正在研究细胞和病毒癌基因时,他听时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的玛格丽特·赫克勒宣布,他当时的朋友罗伯特·加洛发现HIV是导致神秘新瘟疫——艾滋病的病因。杜斯伯格立刻起了疑心。他知道HIV是一种逆转录病毒——这是他自己备受赞誉的研究课题——而逆转录病毒并不会杀死它们感染的宿主细胞。相反,它们会使细胞增殖。这与艾滋病的情况恰恰相反,在艾滋病中,被称为CD4细胞的特殊免疫细胞被消灭。杜斯伯格越是寻求答案,就越相信顶尖艾滋病研究人员最初的假设实际上是正确的:这种疾病——至少在美国——是由吸毒和其他免疫抑制原因引起的。
在他位于伯克利著名的斯坦利大厅内宽敞而繁忙的实验室里,杜斯伯格绘制了1960年代和70年代药物滥用(包括海洛因、可卡因和其他毒品查获)的流行图表。然后他将这些图表与说明艾滋病兴起的其他图表叠加。考虑到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差,他发现这两组图表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虽然吸毒并非新鲜事,但使用的强度和类型似乎出现了新情况,尤其是在男同性恋群体中。杜斯伯格将这个问题比作吸烟:如果你抽几根烟,即使超过十年,你得肺癌的几率可能仍然很低,但如果几十年来每天抽几包烟,你的风险就会飙升。众多研究人员的研究表明,最初患上艾滋病的男同性恋者大多有长期的吸毒史,其中常常包括“poppers”——一种治疗心脏病的亚硝酸盐药物。Poppers不仅被广泛用于致幻,还用于放松肛门肌肉以便于性交。根据几份研究报告,其中一些男性每天有多个性伴侣,一生中的伴侣数量可能轻易达到数百人。由于亚硝酸盐是强致癌物,杜斯伯格认为这解释了为什么男同性恋者频繁患上卡波西肉瘤这种癌症,而其他风险群体,如血友病患者和异性恋吸毒者,则很少患病。他现在说,卡波西肉瘤最终的减少是由于poppers使用量的下降——一项研究发现,短暂接触poppers的小鼠出现了免疫功能下降的迹象,这为他的立场提供了支持。
1986年,经过两年多的研究,杜斯伯格深信HIV是艾滋病病因的理论大错特错,他花了九个月的时间为《癌症研究》撰写了关于HIV的论文。
反应是爆炸性的。杜斯伯格和他的假说都遭到了绝大多数艾滋病研究人员的严厉谴责,其中许多人曾是他的朋友。哈佛大学传染病学教授马克斯·埃塞克斯(Max Essex)是最早怀疑HIV是艾滋病病因的人之一,他在1970年代中期认识了杜斯伯格;他说杜斯伯格总是很有趣,“每个人都想和他一起去喝一杯”。如今,埃塞克斯将杜斯伯格斥为一个怪人,其讽刺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刻薄。“每个人,”他谈到那些抛弃杜斯伯格的人时说,“都觉得他是个应该远离的人,因为他太我行我素,说话不经大脑。”
杜斯伯格说,他的批评者未能对关于艾滋病的令人困惑的矛盾之处提供满意的答案。例如,他问道,为什么卡波西肉瘤(一种血管癌)几乎只发生在男同性恋者身上,而不在异性恋吸毒者中出现?为什么艾滋病在欧洲很少通过异性恋接触传播,却据说在非洲异性恋者中迅速传播?如果艾滋病是由病毒引起的,为什么在花费了20年和数百万美元后,研究人员仍然无法开发出疫苗?最后,会不会像杜斯伯格所说的那样,用于攻击HIV的抗逆转录病毒(ARV)药物实际上弊大于利,与它们已显著降低艾滋病死亡率的普遍看法相反?
埃塞克斯温文尔雅,轻声细语地驳斥了杜斯伯格关于ARVs的观点:“现在有15或20种不同的药物,以8或10种不同的方式起作用,它们唯一的共同点是抑制病毒复制,并将病毒载量降低到可忽略不计的水平。如果你同时使用三种……一旦这样做,免疫系统就会恢复。”
由于他所持的立场,杜斯伯格面临了如此猛烈的个人和专业攻击,以至于在1996年,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的编辑、同时也是杜斯伯格批评者的理查德·霍顿(Richard Horton)打破常规,在《纽约书评》上写道:“杜斯伯格值得被倾听,他所经历的思想上的暗杀将成为现代科学反动倾向的一个尴尬证明。无论人们对杜斯伯格某些论点的有效性有何看法,我们都不得不问:在如此迫切寻求新思想和新研究路径的时刻,艾滋病研究界怎么能不资助杜斯伯格的研究?”
坐在伯克利唐纳大厅他被重新安置的狭小拥挤的实验室里,杜斯伯格的一番话让这位作者感到惊讶,他评论道:“科学上的孤立也有其好处。”自他对HIV表明立场以来的这些年里,他看到自己的资源日益减少,但他也摆脱了公共资金附带的束缚。“我可以自由地按照我认为的方式追求事物,”杜斯伯格说。
坐在从地板到天花板的书架之间,架子上堆满了论文、期刊盒子和关于肿瘤学、艾滋病、医学病毒学、生物化学和免疫学的教科书,杜斯伯格在回答一个关于大卫·杰克(David Jack)所著《汝不可思:一部坦率得残酷的人生指南》这本书的问题时说:“作者把那本书寄给了我,”他谈到这本解释正统思想如何被强加的书时说。“我们本应是‘好士兵’,听从上级的命令,”他轻蔑地补充道。
在1980年代末,杜斯伯格在继续为自己对HIV的立场辩护的同时,重新投身于他最初的工作:试图解开癌症之谜。如果坏基因不是癌症的病因,那么,是什么导致细胞如此可怕地失控呢?他在科学文献中寻找线索,偶然发现了西奥多·博韦里(Theodor Boveri)被遗忘的研究。1914年,博韦里观察到染色体物质数量异常(一种称为非整倍性的状况)的海胆胚胎看起来像癌细胞。经过持续研究,博韦里推测非整倍性可能导致癌症。
杜斯伯格发现博韦里的观察很有趣。基因突变远不如含有数千个基因的错乱染色体那样能造成混乱。杜斯伯格说,遗传突变,无论是遗传的还是后天的,都类似于从汽车装配线上撤掉一两个工人;汽车仍能生产出来,几乎没有缺陷。但他说,对整个染色体的损害,就像移除装配线的整个部分,然后把它放到不该放的地方。突然间,生产出来的汽车可能会有两个引擎或根本没有引擎——或者化油器装在了排气系统该在的地方。
1996年,杜斯伯格没钱、没支持、没员工,他给他的老朋友兼同事、德国曼海姆海德堡大学备受尊敬的医学教授吕迪格·黑尔曼(Ruediger Hehlmann)打了个电话。最近,黑尔曼在他一丝不苟的办公室里,穿着深蓝色西装,外面套着一件全长实验袍,谈论了杜斯伯格和他的许多成功。黑尔曼是他朋友癌症研究的坚定支持者,称他为“癌基因之父”和该领域的天才。但当话题转到艾滋病时,他的脸色阴沉下来。“我认为他错了。这就是我的想法,我也告诉他了。”
即便如此,黑尔曼还是向医学院院长申请资金来设立一个教授职位。院长认识并敬佩杜斯伯格的父亲,他热情地回应说:“哦,那是他的儿子!好的。我们接受他。”自从1997年在海德堡大学任职以来,杜斯伯格在过去的10个夏天里,每年都在曼海姆黑尔曼的办公室隔壁进行癌症和非整倍性的实验。曼海姆坐落在莱茵河与内卡河的交汇处,鹅卵石街道两旁是高档商店和露天咖啡馆,在这些夏天里为杜斯伯格提供了一个安静的工作场所和避难所。正是在这里,他完善了他关于非整倍性是癌症病因的理论。
同样是在德国,1993年,杜斯伯格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西格丽德·萨克斯(Sigrid Sachs)。她是一位迷人的金发女郎,有着天蓝色的眼睛,大家都叫她西吉(Siggi),她立刻就被杜斯伯格迷住了。“从一开始就很好,”她说。“我喜欢他的讽刺,他与众不同——非常风趣和聪明。”两人在波恩的一个会议上相遇,西吉是组织者之一,杜斯伯格被邀请去演讲,同行的还有他的宿敌罗伯特·加洛。
当杜斯伯格来到西吉负责的签到处时,他看到了一个恶作剧的机会。他无意中听到加洛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行程,所以当她问他名字时,他大胆地宣布:“我是加洛博士!”这个玩笑几分钟内就被揭穿了,但杜斯伯格和萨克斯都很享受这个恶作剧,这成了两人之间的一个老梗。会议后不久,她辞去了工作,搬到了伯克利,现在她在那里整理杜斯伯格的研究数据和他关于癌症和非整倍性的会议。
根据杜斯伯格的理论,癌症发生在染色体未能正常分裂时。在细胞分裂或有丝分裂过程中,23对染色体必须完美排列并分裂,以产生46条单独的染色体,其中正好一半——每对中的一条染色体——进入两个子细胞。有时分裂是有缺陷的,染色体对不规则地撕裂,就像纸巾未能沿着虚线撕开一样。这种分离给了其中一个子细胞过多的染色体物质,而亏待了另一个。这种非整倍性,即染色体的不均等分布,对细胞通常是致命的。
但在某些情况下,非整倍性细胞存活了下来。然后,就像一个失控的陀螺,每一次新的细胞分裂都会导致染色体发生更奇异的变化。由于缺乏正确的生长蓝图,这个过程产生的细胞越来越难以辨认。它们既不是肝脏也不是鼻子,既不是乳房也不是睾丸。它们也不局限于它们起源的器官。它们是癌症,是一簇不顾自己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行为而生长的细胞。
杜斯伯格关于癌症的理论在某些圈子里引发的反应几乎和他声称HIV不会导致艾滋病一样激烈。几位接受采访的研究人员在要求不具名后,对杜斯伯格发起了恶毒的攻击,称非整倍性是癌症的结果,而非原因。但最近,一些主流科学家已经转变看法,同意非整倍性可能在癌症中扮演一个角色(即使不是唯一的角色)。
2005年,曾长期排斥他和他的研究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邀请杜斯伯格就他的非整倍性研究做一次大查房报告。其他研究人员,如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托马斯·里德(Thomas Ried),正在进行自己的研究,并与杜斯伯格一同参加关于该主题的国际会议。一些科学期刊甚至发表了杜斯伯格关于该主题的文章,其中包括2007年的《科学美国人》。那里的编辑对杜斯伯格的声誉心存戒备,发表了一篇题为“当贱民有好主意时”的长篇社论,解释他们选择发表他论文的原因。他们写道:“仅仅因为一个科学家持有一些错误或有争议的观点就将其摒弃,有可能会将宝贵的真理一并扫除。”
尽管《柳叶刀》的编辑在1996年呼吁资助杜斯伯格关于艾滋病的研究,尽管十多年后《科学美国人》恳请科学界考虑他关于癌症的理论,彼得·杜斯伯格仍在进行艰巨的科学斗争。而且他是在资金微薄、只有一小撮支持者的情况下进行的。其中一位支持者是维也纳的妇产科医生克里斯蒂安·菲亚拉(Christian Fiala),他说杜斯伯格“显然遵循着理性和基于证据的思维,并据此论证。”菲亚拉最初怀疑HIV是艾滋病病因,是因为专家警告说该疾病将蔓延到已知的风险群体——男同性恋、静脉注射吸毒者和血友病患者——之外。这对他来说不合逻辑。他说,局限于风险群体的疾病会一直局限于风险群体,除非发生像病原体突变成一种新的、更具毒性的疾病形式这样的重大事件,而当时并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菲亚拉告诫不要轻易否定像杜斯伯格这样的研究人员,他说历史上异见者是正确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也曾迫害过塞麦尔维斯,”菲亚拉谈到这位19世纪在维也纳行医的著名匈牙利医生时说。尽管那座城市现在有一家以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命名的医院,菲亚拉回忆说,这位医生曾因提出医生是1800年代成千上万妇女因“产褥热”(一种产后不久发生的子宫感染)死亡的主要原因而受到严厉抨击、被解雇并被禁止进入该市。又过了好些年和更多死亡之后,医生们才意识到塞麦尔维斯是对的:医生们在分娩过程中感染了妇女。当医生们遵循塞麦尔维斯洗手的告诫后,产褥热死亡率降至先前水平的十分之一。
与塞麦尔维斯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可能更具启发性。历史学家认为,塞麦尔维斯是他自己最大的敌人——他固执而傲慢,拒绝写下自己的发现。他们说,如果他更圆滑一些,也许他的观点会得到更仔细的评估。同样的情况也可能适用于杜斯伯格。塞麦尔维斯不愿动笔,而许多人说,杜斯伯格则不愿倾听或闭嘴。
尽管杜斯伯格可以非常迷人,但他有时也可能粗俗得令人不安。例如,他多次将同性恋者称为“homos”,将黑人称为“Schwartzes”。在为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沃森关于种族的争议性言论辩护时,他说:“在这里,你本应是诚实的科学家,一切都基于证据,然后你却应该说,好吧,我们都一样,我们同样为非洲的某个黑人[和]在伯克利的一个亲戚或朋友或随便谁感到难过。显然你不会。”
西吉·杜斯伯格非常清楚围绕她丈夫的种族主义指控。杜斯伯格对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的影响——姆贝基曾引用他的理论拒绝为南非的HIV/AIDS患者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使杜斯伯格在他的批评者看来,与一项他们称之为对许多未接受ARV治疗而死亡的非洲人进行“谋杀”的政府政策同谋。马克斯·埃塞克斯认为,历史将把杜斯伯格评判为“一个只是戏弄科学界的疯子”或“大规模谋杀的帮凶”,因为许多非洲艾滋病患者的死亡。尽管埃塞克斯没有指控他种族主义,但他表示,杜斯伯格的主张必定源于某种“不可告人的动机或严重的心理盲点”。
杜斯伯格自己,则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消除这场持续发酵的争议。当他的妻子站在伯克利一家餐厅外时,她忍不住对他翻白眼,显得既无奈又恼火,她说:“我丈夫有时候就是嘴巴太坏了,我告诉他,‘你就闭上嘴吧。不太了解你的人有时不懂你那种幽默。’”在后来的一次通话中,她说:“他不是种族主义者。”但她补充说,夫妻俩为他说话的方式“争吵过很多次”。然后她叹了口气说:“我也意识到我真的改变不了他。没人能改变他。”
除了曼海姆,唯一能让杜斯伯格摆脱困扰他的争议的避难所就是他伯克利实验室的四壁之内。当他进入实验室准备给本科生上课时,几个学生用灿烂的笑容迎接他。学生们举着纸片,专心地盯着看,空气中弥漫着勤奋的气氛。他们正在进行Southern印迹测试,以检测他们插入大肠杆菌DNA中的λ病毒基因组。几个学生走近杜斯伯格,就其他项目寻求建议。他对每个人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在实验室的一个角落里,围着显微镜、煤气灯和烧瓶,六七个学生在谈论他们的教授。一个学生说杜斯伯格是“校园里最支持学生的老师之一”。其他学生点头同意。“别的老师都躲着学生,但杜斯伯格博士不会,”另一个学生补充道。“他是这里最好的老师。”当学生们被问及对围绕他们教授的争议有何看法时,他们的表情变得茫然。很明显,他们并不知道围绕着他的这场纷争。这些彼得·杜斯伯格粉丝俱乐部的成员中,有些人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关于艾滋病和HIV的争议达到沸点时甚至还没出生。一个学生不确定被问的是什么,试探性地回答说:“我们几乎所有的教授都很有名。”
离开学生们,杜斯伯格思绪飞转,解释说他多么渴望有研究能证明或证伪他关于HIV的假说——比如用“poppers”对小鼠或大鼠进行长期治疗,看它们是否会患上艾滋病和卡波西肉瘤。他说,这正是当今研究人员极度需要却未予追求的功能性证据。
他还建议追踪美国军队申请者的健康状况——在过去的22年里,军方已经对数百万潜在新兵进行了HIV检测。一些检测呈阳性的人正在接受治疗,一些则没有。杜斯伯格说,这样一项研究将显示“其他方面健康的HIV感染者患上艾滋病定义性疾病的几率是否高于没有HIV的匹配对照组的正常水平”。如果HIV只是他所认为的“无害的过客病毒”,那么未经治疗的HIV阳性个体的情况可能会与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HIV阳性患者一样好,甚至更好。
埃塞克斯对这样一项研究不以为然,他说:“我认为这完全不道德。”埃塞克斯说,只有在某种疾病没有现有治疗方法时,才应该允许使用安慰剂或不进行医疗干预。“一旦有人说,好吧,这种药比安慰剂效果好,那么它就成了你测试下一种药或药物组合的标准。这是你在伦理学中学到的第一件事……就像在塔斯基吉进行臭名昭著的梅毒实验一样。完全一样。这完全不道德。”
杜斯伯格不认为研究未经治疗的患者有什么问题。“这有什么不道德的?”他问道。“没有人会被要求不吃药。”一小部分科学家,包括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同意杜斯伯格的观点,并认为不检验他的理论才是不道德的。也许令人惊讶的是,一些HIV检测呈阳性甚至被诊断为艾滋病的人也相信杜斯伯格是正确的。其中一位是住在纽约市的47岁男同性恋者,他HIV阳性已有23年,从未服用过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他认为这些药物“有毒”,并将自己的存活归功于杜斯伯格。“我看着我的朋友们吃越来越多的药,然后病得越来越重,”他说。他声称,是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而不是HIV,导致了他们的死亡。
无论对错,二十多年来,杜斯伯格无疑为他的信念付出了代价。即使是亲密的朋友也曾恳求他收回一些言论,只为让他不被针对和排斥。当被问及为何在艾滋病问题上坚持提问,尽管这已导致他和他家人的经济损失、专业上的排斥和社交上的孤立时,杜斯伯格推着他的自行车,沿着一条蜿蜒穿过伯克利校园葱郁草地和庄严树木的小路走着。他停下脚步,思索片刻,然后说:“我不想成为一个‘好德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