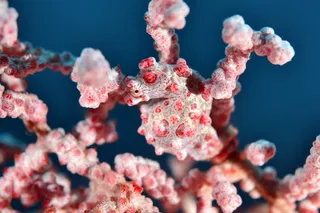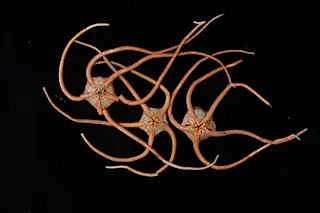布伦特·肯尼迪19世纪的祖先从他的相册中凝视着,他们有着黑眼睛、高颧骨、橄榄色皮肤和浓密的黑发——一个等待被解开的遗传谜团。埃尔维斯·普雷斯利、艾娃·加德纳和亚伯拉罕·林肯可能是他们的亲属,这并不奇怪,但这个部落的成员从未完全符合美国的种族分类。根据人口普查员或税务员的划分,他们被归类为白人、“有色自由人”或混血儿,经常在他们从一个县搬到另一个县时跨越肤色界限。
肯尼迪称自己是梅伦吉人,但没有人确切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今美国可能有多达20万梅伦吉人,他们都源于一个神秘的、橄榄色皮肤的族群,他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阿巴拉契亚山麓。有人说梅伦吉人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葡萄牙水手,或殖民时期的土耳其丝绸工人。另一些人则指向吉普赛人、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失落的罗阿诺克殖民地,或古代腓尼基人。甚至不清楚“Melungeon”这个词的来源:它可能来源于法语的“mélange”,甚至是阿拉伯语或土耳其语中“被诅咒的灵魂”的讹传。
肯尼迪认为,解开这个谜团的关键之一在于DNA分析。三年前,他和其他梅伦吉遗产协会的领导人寻求弗吉尼亚大学怀斯学院生物学家凯文·琼斯的帮助,并开始从当地家庭收集基因样本。现在,在一个闷热的六月下午,在田纳西州金斯波特举行的第四次梅伦吉人聚会上,研究结果即将揭晓。布伦特·肯尼迪和他的族人终于要了解他们的构成。
讲台上,琼斯穿着外套打着领带,看起来又热又难受。这位留着刷子状胡子的伦敦人,语气略带嘲讽,他习惯了大部分时间研究真菌、细菌以及黏菌之间的进化关系。他原以为这个项目会很有趣,甚至可能具有医学重要性。但此刻,他看起来宁愿在树林里思考一块粘稠物。
基因分析似乎有望为身份的无底问题提供最终答案,对我们物种数十万年在全球漫游提供一个直接的解释。然而,琼斯却无意中发现,像他这样的研究往往会搅动祖先的锅,颠覆坚如磐石的理论,撕裂个人身份和民族起源神话。简而言之,正如梅伦吉人很快就会发现的那样,DNA会让人心碎。
人类基因组就像一位古怪的曾祖母一样,将秘密藏匿起来,把传家宝用破布裹起来放在阁楼里,把珍贵的家庭肖像埋在报纸剪报堆下。在杂乱中寻找有意义的模式很难,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分子生物学家开始做到这一点。他们意识到,我们的基因组在数千年里积累的突变并非一无是处。它们可以像账本一样被解读。
大多数时候,人类基因组中30亿个核苷酸都能正常复制。然而,偶尔也会发生组成分子的一对核苷酸碱基被替换,或者一小段遗传密码被复制。科学家们已经意识到,找出谁与谁有亲缘关系,仅仅是比较这些突变的问题。拥有共同近亲的人会有许多相同的突变。远亲则共享较少的突变。
为了确定谁捐赠了哪些基因,分子人类学家会观察基因组中直接从父母传给孩子的两个部分。在男性中,那是著名的Y染色体,每个父亲都会传给他的儿子。在女性中,则是线粒体DNA——储存在大多数细胞线粒体中的小环状遗传物质。每个人都有线粒体DNA,但只有女性会将其传给后代。
线粒体DNA是这两种分子中更容易处理的一种:它短小——只有16,569个核苷酸长——可以从发丝中分离出来。它还频繁突变,留下了丰富的祖先记录。Y染色体研究更棘手,也更费力,因为染色体巨大(大约6000万个碱基长),且编目不完善。因此,线粒体DNA研究首先兴起,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蓬勃发展。Y染色体研究直到几年前才流行起来。
最初的分析纯属苦差事,但随着DNA技术的进步,从基因中读取历史变得自动化。现在,人类学家将Y染色体DNA或mtDNA从其余细胞碎片中分离出来,并将纯化、制备好的DNA输入机器。然后他们读取另一端输出的A、C、T和G的核苷酸序列,并将突变模式与各种公共遗传数据库中的模式进行比较。这些模式被称为单倍型,相似单倍型的集合被组织成单倍群。单倍群说明了特定谱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来源(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东亚)。通常——但并非总是如此——单倍型会指向更具体的地理区域,如日本或南印度。
在过去的几年里,这种基因分析变得如此经济实惠,以至于催生了一个“休闲基因组学”公司的家庭手工业。现在只需150到500美元,你就可以寄送一份颊拭子或头发样本,了解你是否拥有美洲印第安血统,是否与拥有相同姓氏的其他人有亲戚关系,或者你是否属于犹太祭司科亨血统。一家公司甚至承诺,只需319美元就能告诉客户他们精确的种族构成——以百分比表示。
基因分析擅长显示哪些现存人群关系最密切。但要追溯历史以找出更精确的关系,则需要令人费解的数学。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的群体遗传学家彼得·安德希尔说:“我们有这张漂亮的快照,展示了谁与谁有亲缘关系。但你可能同时有三四种不同的说法,它们都会导致相同的基因图景。争论总是围绕着:哪种说法更合理?”
在美国,曾经一滴血足以区分自由民和奴隶,讲述这些故事远不止是一种消遣。例如,不到一个世纪前,梅伦吉人模糊的种族地位就足以让他们树敌无数。弗吉尼亚州的镇民曾将他们告上法庭,指控他们试图投票,并因他们与白人妇女结婚而将他们绞死。一位积极的弗吉尼亚州户籍登记员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发起了一场运动,追捕所有梅伦吉人并将其重新归类为“有色人种”。
直到近几十年,“梅伦吉人”一词才不再是贬义词。杰克·戈因斯是一位退休的玻璃切割工和电视技术员,他花费了几十年研究自己的祖先,他说:“梅伦吉人总是住在另一座山脊上的其他家庭。”达琳·威尔逊,一位50岁的管理员兼肯塔基州东南社区大学的历史教师,她说在20世纪60年代她还是青少年时,在弗吉尼亚州诺顿的一家快餐店工作,她的老板在梅伦吉人吃完饭后让她擦洗座位。
在弗吉尼亚州的怀斯长大,布伦特·肯尼迪完全不知道他与那些住在阿巴拉契亚山区的害羞的人有亲戚关系。他长着矢车菊蓝的眼睛和古铜色的皮肤,看起来并不特别像盖尔人,但梅伦吉人的血统是体面人不会谈论的事情。在他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进行家谱研究后,一位曾祖母烧毁了一批家庭照片和信件,其他亲戚也停止与他交谈。
当肯尼迪向学者们提出他的问题时,他们不屑一顾。他们说,华盛顿特区印第安事务局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如弗吉尼亚·德马尔斯,已经解决了梅伦吉人问题。肯尼迪的族人是一个孤立的群体,就像路易斯安那州的红骨人(Red Bones)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铜踝人(Brass Ankles)一样。他们是一个由白人、美洲原住民和非裔美国人血统组成的“三族隔离群体”——历史上的一个注脚。
因此,肯尼迪转而进行自己的研究。他的著作《梅伦吉人:一个骄傲民族的复兴》既是回忆录,也是宣言。它借鉴了他家族的故事和家谱,展示了梅伦吉人如何像非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一样,成为恶毒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以及他们如何通过同化来保护自己。肯尼迪的论点成为许多梅伦吉人的号召,但历史学家嘲笑他不那么严谨的方法。德马尔斯在1996年《国家家谱季刊》中写道,肯尼迪“实质上发明了一个‘新种族’”,一个“历史上不存在的受压迫少数民族,这与他自己的血统不符”。
1998年,肯尼迪的研究变得更加紧迫。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与莫名其妙的发烧作斗争,最终被诊断出患有遗传性疾病。这种疾病被称为家族性地中海热,会导致间歇性高烧和严重的腹痛。它在叙利亚人和土耳其人以及田纳西州和弗吉尼亚州的梅伦吉人中很常见。多亏了秋水仙碱这种药物,肯尼迪最终能够控制住病情。但这段经历让他确信自己一定有地中海血统。否则,一个苏格兰-爱尔兰血统的白人男孩为什么会有这种基因疾病呢?
DNA研究提供了最好的答案希望,但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一些梅伦吉人反对它。另一些人则希望它最终能埋葬关于非洲血统的古老理论。还有一些人对摆脱种族不纯洁的兴趣不如庆祝它。在聚会上,几位看起来是白人的男子骄傲地宣称他们有非裔美国人血统;另一些人则吹嘘有萨波尼印第安人或塞法迪犹太人祖先。肯尼迪在台上情绪激昂地为DNA项目辩护。他英俊且口齿清晰,拥有传播研究博士学位和温和的南方口音,已成为梅伦吉人中的名人——既受人敬仰又遭排斥。“我们一直被边缘化和排挤,我把矛头指向学术界,”他告诉人群。许多人点头表示同意。肯尼迪说,梅伦吉人的历史太广阔,太混乱,不适合历史学家。“这就是DNA研究的原因。它被强加给了我们。”
不幸的是,生物学家几乎没有权力纠正历史的错误或安慰其受害者。他们说,一些梅伦吉人寄予希望的种族概念,在生物学上毫无意义。与其他哺乳动物相比,所有人类实际上都是表亲。一群黑猩猩的基因多样性比所有60亿人类的基因多样性还要大。此外,任何一个大型人类群体都拥有整个物种约85%的基因变异。一个普通的希腊人与一个蒙古人的共同基因可能与他或她与另一个希腊人的共同基因一样多。事实上,最近的基因证据表明,所有人类都源于几千名在不到15万年前从撒哈拉以南非洲迁徙出来的猎人。
DNA所能揭示的关于种族的微弱光芒,往往并不受欢迎。例如,三年前,在亚利桑那大学,遗传学家迈克尔·哈默研究了来自欧洲、非洲和中东的犹太男性的Y染色体。他发现,他们的基因彼此之间比与大多数非犹太邻居有更多的共同点。但他们与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人却无法区分。在类似的另一项研究中,犹他大学的遗传学家迈克尔·班姆沙德检查了来自不同种姓的印度亚洲人的DNA。他发现,种姓越高,欧洲典型遗传模式的比例越大——尤其是在男性中。他的团队的数据支持了人类学和语言学理论,即印度种姓制度是数千年前由西方入侵者建立的,可能来自安纳托利亚和高加索地区。
像安德希尔和哈默这样的分子人类学家已经习惯了此类研究引发的争议。但这对凯文·琼斯来说却是一个糟糕的惊喜。“我进入人类遗传学领域时,对它的含义极其天真,”他说。“没有任何东西让我为它的炒作面做好准备。”研究开始后,一些梅伦吉人打电话询问何时能看到结果;另一些人打电话说他取样错了人。琼斯甚至收到了一个梅伦吉人的死亡威胁,因为他无法接受自己可能有非裔美国人血统。“我认为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有多危险,”他说。“它搅动了马蜂窝。我们通过科学的纯粹性来支持或驳斥假设,但这是一种极其天真、纯粹、上帝般的方法。天哪,它确实搅动了凡人。”
那天下午,琼斯走向金斯波特讲台时,梅伦吉人正在扇风。琼斯被宣传为最终将为梅伦吉人问题提供明确答案的人,但他一开始就告诉他们,他们的DNA根本无法证明多少。在伦敦大学学院遗传学家马克·托马斯的帮助下,琼斯检查了120个mtDNA样本和大约30个Y染色体,他得出结论,梅伦吉人主要是欧亚人,这是一个涵盖从斯堪的纳维亚到中东地区人民的总称。他们也有一点黑人血统和一点美洲印第安人血统。在琼斯检查的mtDNA单倍型中,有四个不寻常。它们只与全球数据库中2万个序列中的一个相符,来自一个名为西迪的印度族群,该族群可能起源于北非,并产生了欧洲的罗姆人,即吉普赛人。其他一些梅伦吉人拥有一种在叙利亚人和土耳其人中常见但在北欧并非闻所未闻的单倍型。
在Y染色体中,有几个是完全无法解释的。当琼斯在伦敦大学学院的欧洲人口数据库中搜索时,这些样本与4500个条目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匹配。至于肯尼迪的家族性地中海热,仍然是个谜。虽然有些模式确实与土耳其发现的相似,但梅伦吉人的DNA中没有葡萄牙或土耳其血统的证据。这项研究作为一个整体,证明了多民族血统很常见,即使在该国历史上种族分歧很深的地区也是如此。“如果有人叫你近亲繁殖,”琼斯打趣道,“他们是在撒谎。”然而,这并没有提供太多依据。DNA数据告诉那些与美洲原住民有着深厚联系的人,他们的祖先大多是白人。它告知许多金发碧眼的人,他们至少有一些祖先是黑人。它还给肯尼迪带来了尤其残酷的信息:他深爱的自我认同和社区感可能永远无法被证明,而差点要他命的罕见遗传病症的起源可能永远无法知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你想它意味着什么,它就意味着什么,”琼斯告诉观众。“如果你希望有一个DNA序列告诉你你是梅伦吉人,那就别想了。”
人群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就散去吃午饭了。很多人没有回来,尽管聚会还有两天。一位参加聚会的人在街对面的Shoney's餐厅说:“他们试图说没有多少美洲原住民血统,这简直是个笑话。”有些人耸耸肩,但另一些人似乎真的很失望。“很多人都希望能有一些异国情调的东西被呈现出来,但并没有,”达琳·威尔逊后来表示。“也有一些人希望非洲血统的说法被排除,但也没有。”
这种反应对其他分子人类学家来说并不意外。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留下了深刻但非常狭窄的祖先记录,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遗传学家、分子人类学先驱道格拉斯·华莱士说。想象一下,你的曾曾曾曾祖母是北非人,而碰巧,她的女儿和她们的女性后代都嫁给了法国人。五代之后,你仍然拥有纯粹的非洲线粒体DNA,但你的基因组其余大部分将来自家族的法国一方。“那么你是非洲人还是法国人?”华莱士问道。“人们认为基因组的一部分代表了所有基因,但这显然不是事实。你更多的是你认为的自己,而不是你的基因告诉你的。”
当人们认为基因信息凌驾于文化、语言和教养之上时,他们注定会失望。华莱士被问及梅伦吉人项目时说:“我不赞同人们为了弄清楚自己是不是腓尼基人而撸起袖子(献血样本)。”“那只会让人受到伤害。”琼斯不太确定。“我该做这个吗?”他在演示后想。作为一名科学家,他不得不说是——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些信息的潜在医疗效益。但除此之外,他无法确定。“这是个奇怪的行当。黏菌安全多了。”
下个星期日清晨,七名梅伦吉人挤进一辆小型货车,颠簸着驶上纽曼山脊,进入田纳西州梅伦吉人聚居地的中心。梧桐树上挂满了槲寄生,沿途许多房屋都种着小块烟草。坐在驾驶座上的杰克·戈因斯开玩笑说,发夹弯太急了,“你会碰到回头的自己”,而其他人则开玩笑说谁的法外祖先杀了谁。
这就是他们来参加这次聚会的原因——看看他们的祖先曾耕种的山谷和山顶,分享传说,并在墓碑和破旧的小木屋前合影留念。其他人可能将身份寄托于DNA,但对于这群梅伦吉人来说,汉考克县甜蜜空气中的一个夏日早晨比任何基因信号模式都更有意义。
在纽曼山脊下的山谷里,梅伦吉人爬出来,走向那座粉刷成白色的原始浸信会教堂。塞文·吉布森正在布道,他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几个主要的梅伦吉家族。教堂前,一个喷泉收集着上方刀背山流下的泉水。它只不过是一个低矮的石槽,上面有一个屋顶和一个水龙头,但上面的牌子上写着:“这水能解你身体的渴。只有耶稣能解你灵魂的渴。”
戈因斯递出一些泡沫塑料杯,每个梅伦吉人依次喝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