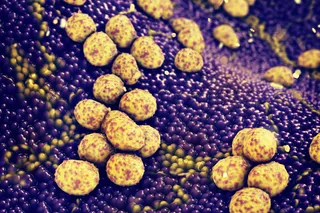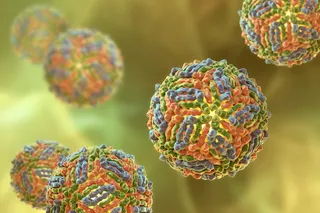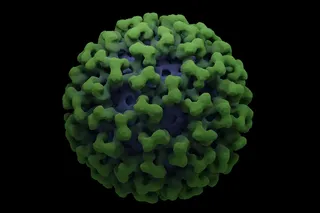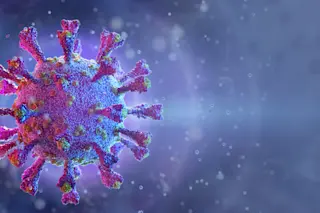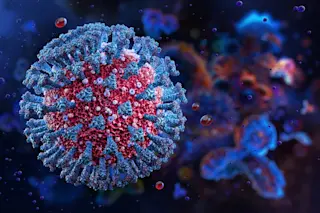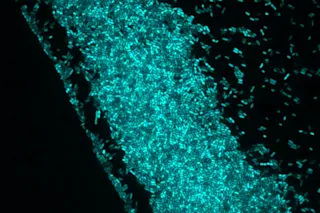几个月前,我表哥史蒂夫的婚礼盛大而隆重,在招待会结束时,琳妮,也就是他嫂子,把我堵在了酒吧旁,我们俩都有些微醺,毕竟喝了几杯香槟。
“所以,我听说你照顾艾滋病患者,”她一边抿着续杯,一边说道,“但我不太明白。我一直听说对他们没什么可做的。那你到底做什么呢?握着他们的手?你怎么受得了?”
当时我头脑有些昏沉,觉得礼貌地微笑、耸耸肩然后赶紧去洗手间是最好的应对方式。但如果当时不是太晚,音乐没有那么响,香槟没有那么烈,我就会告诉琳妮关于比阿特丽斯·凯的故事。
去年,凯女士住进了我工作的医院的艾滋病病房,那段时间我正担任该病房的 the supervising attending physician(主管主治医师)。在那几个月里,我每天早上都会和住院医师及实习医师开会,检查前一天入院的新病人,并讨论其他病人遇到的问题。按照传统,这些晨会称为“查房”,尽管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而不是在巨大的病房里从一张病床走到另一张病床。
那个月,我有一支非常出色的团队,实习医师和住院医师们都勤奋而认真。没有人带着那种会败坏大家心情的态度来对待艾滋病患者。与一个讨厌病人并害怕他们疾病的实习医生共处一个月是场噩梦,但这个月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算顺利。
“昨晚我们只收了一个病人,”高级住院医师克里斯在我端着咖啡杯出现查房时说道,“从医学上看,我认为没什么好谈的,但她有很多其他重要的问题,值得和实习医师们一起探讨。她有关于临终问题、停止治疗问题、能力问题、监护权问题、生前遗嘱问题,甚至还有协助死亡的问题。这将会是很棒的一上午!”克里斯是医院社会医学项目的住院医师,他有时会因热情而有些激动。
但他说的没错。凯女士的故事是艾滋病护理中社会心理问题的教科书案例。她才 26 岁,患有艾滋病多年,感染源是她已不知去向的丈夫。过去四年里,她曾因六次主要的艾滋病相关肺炎和一次严重的艾滋病相关脑部感染而住院。就在几天前,她刚从市中心一家医院出院,在那里她因虚弱、腹泻和腹痛住院两个月。
克里斯前一晚联系了那家医院,详细了解了凯女士的住院情况,包括她腹部、肠道和肝脏的所有可能检查和 X 光检查。所有结果都是阴性的。凯女士最终出院,但她沮丧且病情没有好转。回到家,几天没有静脉输液后,她变得非常虚弱和恶心,以至于家人叫了救护车将她送往我们附近的急诊室。
“很可怜,”今天早上汇报病情的实习医师瑞奇说道,“所有人都知道她想在家去世,但当她真的开始不行了,她全家人都会害怕。她家里有一个四岁的儿子和六岁的女儿,这实在太难了,尤其是对孩子们来说,所以他们把她送回来了。但她不想住在这里,她不想再做任何检查了。她想回家。也许我们能给她一些护理支持,过几天就能让她回家了。也许还需要给孩子们做些心理辅导。她真的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对于每一个艾滋病患者,都会有一个时候,需要有人说“够了”。有时是患者先说,有时是医生。理想情况下,是双方一起说。信息总是一样的:是时候停止用 X 光、抗生素和痛苦的住院来对抗这种无法征服的疾病了——是时候放弃斗争,平静地为生命的终结做准备了。凯女士似乎已经达到了那个点。我们的工作将仅仅是让她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周尽可能舒适。
当值班医生带我去见凯女士时,她蜷缩在床上,一个瘦弱、精致而美丽的女人,用呆滞的眼睛看着我们。她低烧,而且她坐起来时血压会变得危险地低。虽然她腹部触诊时都有压痛,但我摸不到任何异常的肿块或增大的器官。她精神萎靡,几乎濒死。她的早餐放在床头桌上,一口未动。她只对我说:“别再做检查了。”
回到会议室,我们为凯女士制定了一个计划,包括止痛药、不进行心肺复苏的医嘱,以及为凯女士和她的孩子们提供心理辅导。医院的访视护士联络员将帮助我们安排门诊护理。我们都对这个计划感到满意,当我们与凯女士商量时,她似乎也很满意。
但是,当我中午离开病房回到办公室时,有件事一直困扰着我。整个午餐时间,以及下午看其他病人时,这件事都让我心神不宁。我就是无法忘记凯女士例行入院血液检查的结果。她的血液检查结果完全不像一个据称在家因腹泻和脱水几乎死亡的人。腹泻会使身体流失富含钾的肠道液体,导致血液中的钾水平下降。但凯女士血液中的钾浓度异常高,而不是低。她的肾功能,在脱水状态下通常是不正常的,却出奇地正常。她的钠浓度异常低,毫无明显原因。她的血糖也低。这些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单独来看,在晚期艾滋病患者身上出现都不会让人感到惊讶。然而,它们结合在一起,却指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诊断。
“忘掉她有艾滋病这件事,”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对克里斯说,“我让你想象一下,凯女士只是一个年轻女性,有发烧、腹泻、低血压、腹痛、低钠、高钾、低血糖和肾功能正常。那你觉得是什么病?”
克里斯犹豫了一会儿。“嗯,”他说,“我可能会说她是肾上腺功能衰竭。”
没错。
因为人体对疾病的反应方式只有少数几种,完全无关的病症的症状常常几乎相同。例如,慢性咳嗽可能是由肺炎、哮喘或心力衰竭引起的。恶心可能是由食物中毒、胃溃疡或心脏病引起的。同样,凯女士的虚弱、嗜睡、恶心和体重减轻都是晚期艾滋病的典型症状——但它们也是当肾上腺停止分泌足够的激素时常见的症状。这些激素就像汽车的机油一样,能保持身体的新陈代谢系统润滑和顺畅运行。尽管凯女士刚出院的医院的医生们已经认真评估了她,但他们显然忽略了这种可能的诊断。
克里斯和团队的其他成员并没有需要太多说服就同意了一个小小的例外,打破了我们与凯女士的“不再检查”的约定。即使是她,也勉强同意,再抽几管血送去化验检查她的肾上腺功能,也不会有坏处。那天早上,值班医生们学会了知道何时说“够了”的重要性。现在,他们将要学会有时知道何时可以收回这句话的重要性。
肾上腺是位于肾脏顶部的两个小金字形组织,它们分泌皮质醇、醛固酮和其他激素,调节血压、食欲和能量水平。有时,这些腺体会在被癌症或结核病等感染侵蚀和破坏时停止工作。有时,由于对肾上腺组织的异常免疫反应而导致腺体衰竭,就像约翰·F·肯尼迪总统一样,他在 30 岁时被发现患有特发性肾上腺功能不全,即艾迪生病。有时,腺体尽力工作,但就是无法满足身体对激素的需求。在一些 HIV 感染者中,病毒本身似乎会影响细胞处理肾上腺激素的方式,导致身体需要比腺体供应更多的激素。尽管研究人员尚不完全了解艾滋病患者肾上腺功能衰竭的确切原因,但医生们正在学习警惕区分艾滋病的持续衰退与艾滋病相关肾上腺功能不全的可逆性衰退。
肾上腺功能衰竭通过药物治疗效果很好。一旦诊断确定,肯尼迪总统在他的余生中都通过激素替代治疗方案正常生活。然而,如果没有药物,或者他的病情没有被准确诊断,他可能也会像凯女士一样,因疲劳、体重减轻和虚弱而日益残疾。他可能会出现维持血压的问题,并可能出现发烧、恶心和腹泻。他的血液检查结果将反映醛固酮的缺失,这种激素维持着正常的钠和钾水平。他的皮肤可能会因垂体激素 MSH(黑色素细胞刺激素)的作用而略有变黑,这种激素在肾上腺功能衰竭时会急剧升高,试图刺激衰竭的腺体工作。
尽管肾上腺功能不全很容易治疗,但诊断起来可能很棘手。它往往会模仿许多其他疾病——抑郁症、神经性厌食症以及其他慢性消耗性疾病,如癌症和艾滋病。血液检查在区分这些病症方面非常有帮助。通过测量注射肾上腺刺激激素前后皮质醇(一种易于测量的能量调节激素)的含量,可以判断肾上腺是否能正常工作。但即使是血液检查,有时也无法提供明确的答案。令人费解的是,在艾滋病患者中,即使存在肾上腺功能衰竭的症状,皮质醇检查也可能正常。
我们找出凯女士情况的最佳方法是测试她的血液皮质醇水平,并观察她对替代肾上腺激素的反应。我们必须谨慎诊断,因为用于治疗肾上腺功能衰竭的激素会损害正常的免疫功能,如果长期使用,实际上可能会加剧艾滋病的免疫缺陷。尽管剂量通常足够小,可以尽量减少这种副作用,但在开具长期治疗方案之前,我们想对凯女士的病情有十足的把握。
在值班医生为凯女士抽血测皮质醇水平后,他们开出了她开始服用替代肾上腺激素药片的医嘱。三十六小时后,当我来病房查早房时,会议室是空的。我在那里独自等了几分钟,然后去找团队。我他们在凯女士的床边找到了他们。他们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迟疑地笑了笑,坐了起来,吃着她的早餐。这是她几个月来吃的第一顿完整餐。那天晚些时候,她开始在病房里走动。第二天下午,她出院了。“我感觉很好,”她说,“我得回家照顾孩子们。”
她出院一周后,我们收到了她的血液检查结果。她的皮质醇水平是正常的。尽管如此,凯女士戏剧性的康复证实了她确实患有肾上腺功能衰竭。她只是需要比正常水平更高的肾上腺激素来维持她身体的新陈代谢平衡。
凯女士出院一个月后,我接到了一位卡尔曼医生的电话。他是凯女士接受门诊护理的社区 HIV 诊所的医疗主任。他打电话时声音洪亮得我不得不把电话拿远一点。
“我的护士们都没认出她!她只是来续药的。她看起来完全是另一个人。她胖了 25 磅。她说她要回去工作了。她让我替她向你们所有人说‘谢谢’。”
他停顿了一下。“你知道,”他声音稍稍放低了一些,“我们都认为她没救了。我们告诉家人联系殡仪馆,做好一切准备。我们和她、和孩子们一起做了临终关怀……我猜我们有点太早了。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大约六个月后,卡尔曼医生又打来了电话。情况没有变化,凯女士实际上已经回到市中心一家办公室工作了。
这就是我想在表哥史蒂夫的婚礼上告诉琳妮的故事,但当时我却又喝了一杯香槟——为比阿特丽斯·凯默举一杯沉默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