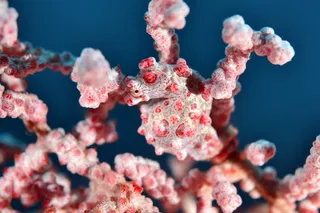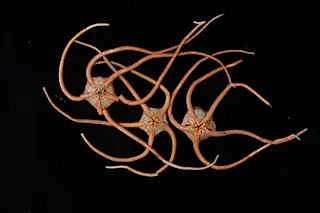去年,科学家们对一块尼安德特人骨骼上的一小段 DNA 进行了描述,结果显示它与我们不同。这块骨骼来自 1856 年在杜塞尔多夫附近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化石本身的右侧肱骨(上臂骨),DNA 来自线粒体 DNA 的控制区。控制区不编码任何蛋白质,因此自然选择会忽略它;性选择也会忽略它,因为与决定我们外貌的 DNA 不同,细胞核内的 DNA(线粒体 DNA)是完整地从母亲——仅从母亲——传给孩子的。理论上,控制区就像对鸡汤的喜好一样,通过无穷无尽的母亲传递链,仅受随机突变的影响,从遥远的过去传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中的一些人有尼安德特人在母系血统中,她的印记应该是可以辨认的。慕尼黑大学的 Svante Pääbo 和他的同事们分析了他们找到的单个尼安德特人的 DNA,并分析了 1600 多名现代欧洲人、非洲人、亚洲人、美洲原住民、澳大利亚人和大洋洲人的 DNA。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亲缘关系证据。
这项工作被广泛誉为一项技术壮举——在一个关于琥珀中昆虫 DNA 的早期报告似乎正在崩溃的年份里(见第 47 页的故事),这令人感到宽慰。看来,除了 Pääbo 的实验室,几乎没有其他实验室能够从仅含有约 50 份目标分子的液化骨骼样本中提取出尼安德特人的 DNA。一位名叫 Matthias Krings 的研究生完成了这项艰苦的工作——通过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扩增稀少的 DNA,对其进行克隆,最终确定其序列。据莱茵兰地区考古负责机构 Rheinisches Amt für Bodendenkmalpflege 的 Ralf Schmitz 说,是 Krings 投入了每周 100 小时的辛勤工作。当他发现其中可能有些东西时,他一直工作到确认为止。
然而,最初促成这个项目的是 Schmitz,一位年轻的考古学家。1991 年,莱茵兰州立博物馆授权他组织对该博物馆的珍贵化石进行新的研究。Schmitz 联系了 Pääbo,Pääbo 曾从埋藏在永久冻土中的一匹 30,000 年历史的马中提取过 DNA。起初,Pääbo 并不乐观:从一块 30,000 到 100,000 年前、且未被冷冻的尼安德特人骨骼中提取 DNA 的可能性非常渺茫——渺茫到不足以说服化石保管者。Schmitz 说,这就像你在研究蒙娜丽莎的颜料而从中切下一块。你必须有充分的理由才能这样做。
然而,到了 1996 年,基因提取技术已经改进,Pääbo 也愿意尝试,Schmitz 获得了许可。1996 年 6 月,他与专业的骨骼 preparator Heike Krainitzki 一起,进入了存放骨骼的钢制保险库,骨骼被保存在钢箱内的钢制柜子里——博物馆只展出了带有著名眉脊的头盖骨。Schmitz 回忆说,当时气氛极其紧张。我们俩都非常紧张。Krainitzki 不希望有其他人 G在场。一家德国电视台曾想现场直播,但她拒绝了。两人都穿着防护服和外科口罩,以避免污染骨骼。Krainitzki 用金匠的锯子从右侧肱骨上切下一块半英寸厚、八分之一盎司重、半月形的切片——X 射线和其他测试表明这块骨骼保存最好。然后,她和 Schmitz 立即将切片带到慕尼黑。在那里,Krings 从骨皮中钻取了微小样本;骨皮中坚硬的碳酸钙在外部层提供了比骨髓更好的 DNA 保护。
五个月后,Schmitz 再次回到慕尼黑。那时,经过那些每周百小时的辛勤工作,Krings 已经提取出了一点他认为是尼安德特人 DNA 的样本。他现在正在用从那块半月形切片上钻取的另一份百分之一盎司的骨骼重复整个实验。如果他再次获得相同的 DNA 序列,他几乎可以肯定他看到的是现代人类的污染。Schmitz 回忆说,结果在一个 11 月的晚上 10:14 送达。他说,感觉就像我们攀登了珠穆朗玛峰。之后又有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结果得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Mark Stoneking 独立实验室的确认,该实验室从另一块尼安德特人骨骼中获得了相同的序列。
在去年 7 月论文发表后,像这样的严格对照似乎已经说服了研究人员的同行,Krings 和他的同事们确实拥有了第一块尼安德特人 DNA,也是迄今为止提取到的最古老的 DNA。然而,尼安德特人究竟是哪种人类,仍有争议。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尼安德特人是我们的祖先,或者更确切地说,主要是现代欧洲人的祖先;在这种观点下,现代人类在全球不同地区同时从像尼安德特人这样的古人类进化而来,同时不断交换基因,以保持同一物种的范畴。另一种观点是,尼安德特人是一个独立的物种,在很少或几乎没有与其他物种杂交的情况下,被大约 10 万年前开始从非洲迁徙出来的现代人类所取代。
尼安德特人的 DNA 并未解决这一问题——但它表明尼安德特人确实是一个独立的物种,因此支持“出非洲”假说。Krings 的 379 个核苷酸序列平均在 27 个位置上与现代人类序列不同,并且它与欧洲人的亲缘关系不比与其他现代人的亲缘关系更近。在现代人类序列之间,平均只有 8 个位置不同。想象一下,一群现代人类围坐在篝火旁,没有人离中心超过八码;而尼安德特人则在 27 码外,远离人群,在树林边缘的阴影中。根据 Pääbo 和 Krings 的计算,智人(Homo sapiens)和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必须独立进化了超过 50 万年,才能变得如此不同。
当然,研究人员只分析了一块来自一个尼安德特人的 DNA。只有当他们或其他人在第二位尼安德特人身上进行比较后,慕尼黑的结果才能被完全证实。尽管如此,第一块尼安德特人 DNA 来自第一个尼安德特人——甚至来自 1856 年矿工们的铲子未曾触及的骨骼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恰如其分的。当时,他们已经无意中将头盖骨和其他骨骼从小费尔德霍费尔洞穴(Little Feldhofer Cave)扔进了迪塞尔河(Düssel River)的山谷。实际上,并没有尼安德特河(Neander River);山谷在 17 世纪晚期得名于一位经常去那里讲道的牧师兼诗人,名叫 Joachim Neumann。用英语,他的名字是 Newman,但按照他那个时代的时尚,Neumann 将其翻译成希腊语,变成了 Neander。一个半世纪后,通过非凡的巧合,Newman 山谷孕育了一个真正的新人——现在看来,一个独立的人类物种。真是太奇妙了,一个半世纪后,尼安德特人自己又一次成为了新闻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