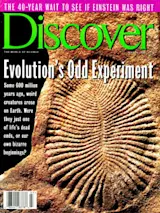我们正站在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市一间不大、有点破旧的砖混结构汽车站里,等着3:10的灰狗巴士从不知何方驶来,马克·霍斯特勒正在告诉我,所有昆虫学家都很怪异。这话出自一个用镊子从巴士挡风玻璃上捡死虫子的人之口。
总之,佛罗里达大学动物学博士研究生,31岁的霍斯特勒似乎曾经和一群动物学家住在一起,他们都在共用冰箱里放着各种稀奇古怪的研究标本。
霍斯特勒说:“所以当我约会的时候,一段关系能持续多久的一个指标就是女人打开冰箱门时的反应。”
3:10的巴士随着气刹的嘶嘶声驶入。房间对面,柜台后面的一个家伙通过公共广播系统宣布登车,然后发出一连串听不清的声音,我猜是为了告知车站里等待的六七个人巴士的目的地。
霍斯特勒仔细打量着那个人。听起来像布福德,他说。不,不是。我以为可能是布福德。1992年夏天,我每周来这里两次。等待的时候,我们常常聊天。
布福德?我问,眉毛不由自主地扬起。
霍斯特勒耸耸肩。嘿,这里是南方。
我们走出玻璃门走向巴士,他告诉我他的一位室友过去常常在晚上到树林里收集香蕉蜘蛛来赚点钱。香蕉蜘蛛是漂亮的雨林蜘蛛,有着细长的黄褐色腹部。这种蜘蛛的网丝非常坚韧,十九世纪的外科医生曾用它来缝合伤口。他把它们卖给当地的一个研究实验室,他们想了解更多信息。
“这人真是个技术迷,”霍斯特勒说。我们正站在巴士前面;霍斯特勒正仔细端详它高高的金属前部。两个坐在附近长凳上的老妇人也正仔细端详着我们。“所以他设计了一个巨大的泛光灯,绑在额头上;我有时会和他一起去观察,那盏灯能照亮半个森林。真是杀鸡用牛刀。啊,那里有一个,”他指着挡风玻璃一角的一块黄色污迹说,“蝴蝶。”
我赞许地点点头,指着另一处微小的污迹。司机下车,走向车内,回头瞥了我们俩一眼。“嘿,你们要帮我洗干净吗?”他漫不经心地说。霍斯特勒没理他,看着污迹。“不知道;也许是只苍蝇。很难分辨。太小了。”
我眼角的余光看到女士们在轻声交谈;其中一位正指向我们。
我指着“Greyhound”(灰狗)这个词中“G”字母里一个圆点。那个?霍斯特勒说,用指甲挠了挠那个标记。油漆碎片。
我叹了口气,有点恼火。我来这里是为了探寻昆虫内脏的奥秘,然而这辆巴士的前部却像传说中的哨子一样干净,尽管霍斯特勒之前信誓旦旦。我来盖恩斯维尔见他,表面上是为了了解他那些可以说狭窄、专业、深奥的研究领域之一:识别那些不幸的带翅节肢动物,它们撞击、拍打、弹离挡风玻璃后留下的四散的污迹。他甚至为此写了一本书,名为《你车上的污垢》(1996年,不羁的蟑螂)。
除了问显而易见的“究竟为什么……”问题,我还想检查一下这里的古怪程度;毕竟,博士候选人通常是埋头苦读的类型,他们把仅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抱怨研究经费的减少和博士后机会的稀缺。这位研究生是否只是神经错乱了呢?
霍斯特勒承认他对被压扁的虫子内脏的迷恋耽搁了他的博士论文写作。他的论文与昆虫内脏无关。相反,他正在撰写关于郊区栖息地侵占对鸟类群落影响的文章。但他无法放弃对内脏的崇敬,所以他自费出版了那本书。
“哎呀,为了出版这本书,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本身又够写一本书了,”霍斯特勒摇着头说,我们离开了巴士,想必那两位老妇人也松了口气。听到这话,我真想问:“你他妈的到底指望什么?!”但这会很粗鲁;毕竟,我是他的客人,而且霍斯特勒是个绅士。
他也是一位致力于向我们其他人传授昆虫知识的科学家,而他的书就是他分享所知的一种尝试。“我希望能吸引人们,让他们对科学产生兴趣,”他说。我们正走向他家;霍斯特勒想给我看看他的草坪。“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写《北美昆虫》,但除了少数昆虫学家,谁会读呢?”
除了那些对虫子有恐惧症的人,霍斯特勒的市场还包括教师,他们购买了不少他的书。(霍斯特勒最初印刷了800本,现在又印刷了2000本。)霍斯特勒很喜欢和小学生谈论生态学和昆虫学。他会带他们到户外去寻找昆虫。作为回报,他收到了孩子们写的感谢信。一个孩子写道:“你让我捡起那只蟑螂!真恶心!”另一个孩子写道:“出去玩而不是学习很有趣。”还有这封奇怪的信:“我喜欢它,因为你教给我们的那些东西我以前都不知道,啊哦,我得走了,所以谢谢,再见。”
事实上,这本书有一种……魅力,如果这个词是恰当的话,一旦你接受了它的恶心程度。它由104页巧妙的篇幅组成,里面塞满了关于昆虫的各种事实,其中有关于蚊子、飞蛾、蠓等常见昆虫的章节,这些昆虫我们通常不屑一顾。当然,除非我们恶狠狠地挥舞着某种致命工具去碾碎它们,无论是苍蝇拍还是一吨重的钢铁在高速公路上飞驰。
书中有24种昆虫的章节,并配有24幅彩图,展示了昆虫生前和死后——非常死后——的样子。这本书是平装本,尺寸适合放在手套箱里,其目的是当出现溅射机会时,你可以迅速拿出它,翻到彩色图片,然后匹配内脏。例如,普通蚊子的条目在逼真的图示下给出了它的拉丁名(Aedes canadensis);其中还嵌入了逼真的溅射图,并附有恰当的描述,题为“溅射:通常是一个小型(1到2毫米)、黑灰色、干燥的点。如果你击中一只吸饱血的雌性蚊子,溅射会带一点红色。”看到了吗?很迷人吧。
识别出你的溅射物后,你无疑会渴望了解更多关于这只已故昆虫的信息。你必须翻到第86页,霍斯特勒在那里用科学把你吸引住。例如,你知道只有雌性蚊子才会叮人吗?好吧,但你知道为什么吗?不,并不是因为它们是邪恶的、嗜血的疾病传播者,它们把短短几周的悲惨生命奉献给吸血,而且它们还用自己的唾液稀释血液,以便更容易吸取,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折磨人类和其他动物。(顺便说一句,是蚊子的唾液让我们发痒。)
正如霍斯特勒所说,雌蚊会积极寻找血餐,因为她需要动物血液中的蛋白质来产生受精卵的卵黄。反过来,卵黄又为她的后代提供营养。
啊,是的,你可能会想,但是卵是如何受精的呢?继续阅读,同时避免在你前面提到的死亡机器中从车道穿梭到车道。霍斯特勒写道,某些解剖学特征使我们能够区分人类的雄性和雌性。(显然,这是一个需要走出盖恩斯维尔,多去大城市旅行的人。)但是雄性蚊子……主要通过雌性翅膀的声音来定位雌性。在飞行中,雌性产生的声音频率介于每秒300到800次振动之间。他写道,雄性会被任何产生这种范围声音的来源所吸引,包括音叉,这对于那个额头上戴着泛光灯的家伙来说,显然是机会来敲门了。
但这并非全部。《污垢》还提供了收集和安装昆虫的技巧,包含了一个丰富的参考文献部分供进一步阅读,并建议了无聊的孩子们在漫长旅途中可以玩的游戏。有“挂蝇”,玩法就像“刽子手”一样,只不过你画的是苍蝇的头部、胸部、腹部、三对腿等等。有“收集检查”,你把一个小网伸出窗外,看看谁能抓到什么(嘿,看!我抓到了一只黄蜂!而且它还活着!)。还有——无疑是爸爸妈妈的最爱——“昆虫艺术”,孩子们把一小块保鲜膜贴在挡风玻璃上(保鲜膜要延伸到引擎盖表面以下,这样就不会被风吹走),旅行结束时小心地撕下来,就能得到一堆虫子溅射物(作者写道:“艺术的巅峰!”)。
我的想法是和霍斯特勒一起开车转转,用一天时间采样他花了两个夏天才研究出来的东西。除了在公交车站和布福德一起度过的时间,霍斯特勒在1994年驾车行驶了12000英里,在全国各地采集飞溅物。他还在他1984年的本田雅阁车顶上安装了一个网,用来捕捉从挡风玻璃上弹开的虫子。
我还想等一只虫子在我租来的汽车挡风玻璃上自毁,然后玩“考倒溅射学专家”的游戏。但我是在十二月拜访霍斯特勒的,这当然不是昆虫的活跃期。不过,霍斯特勒对我询问的最初反应是:“嘿,这是佛罗里达。总有虫子。”我们两人都没料到的是佛罗里达的一股寒流。我来的前一天下了大雨,夜间气温在30多度。寒冷天气除了使一些昆虫变慢,还会杀死其他昆虫,而且至少需要一天时间,留下的卵才会孵化。
从奥兰多机场到盖恩斯维尔,两个小时的夜间车程中,我就知道这个想法要泡汤了。当我把车停在路边的一个休息站时,我检查了挡风玻璃。我只看到了两三个令人失望的微小斑点,可能是蠓(溅射物:直径2到5毫米的小透明斑点,带有黑色斑点)。
小小的胜利:跪下来检查汽车前部时,我发现了一块粗糙的黄色物质,上面似乎有一些小小的附属物伸出来。《污垢》中最接近的描述是蝼蛄,一种两英寸长的东海岸害虫,以植物根部为食。它出名之处在于它会钻入地下建造一个巢穴,以放大其求偶叫声。溅射物:这些昆虫溅落在汽车的保险杠和格栅上。偶尔它们会撞到挡风玻璃,伴随着一声响亮的“砰!”溅射物相当大(20到30毫米长),呈白色,通常包含可识别的昆虫部分(例如头部)。对于溅射爱好者来说,也许可以识别,但对于我这个记者来说却不行。我记下要等见到霍斯特勒时给他看,但我当然忘了。
还好我没试图考倒霍斯特勒。原来盖恩斯维尔当地一家广播电台也做了同样的事,只是——你知道那些疯狂的唱片骑师——他们把一颗小薄荷糖砸到了汽车格栅上。霍斯特勒猜是棉花糖。他说得很谦虚:“那很简单,它太白了,看起来像糖。”
我们来到霍斯特勒的家,寻找野生的昆虫,但也为了让霍斯特勒给我看看他的草坪。这是他的另一个宠物项目,实际上与他的博士研究有关。“对于外行来说,这片草坪急需修剪;对于生物学家来说,它是一个原生生态系统。我的想法是让人们取消他们的草坪。对大多数动物物种来说,修剪过的草地就像混凝土一样;那里什么都没有。”
“城市-郊区景观在北美正变得越来越普遍,”霍斯特勒说,“随着婴儿潮一代退休并离开城市,这种情况只会继续下去。人们还会种植外来植物,它们会蔓延并排挤本地植物。为了野生动物的生存,它将需要像这样的自然植被斑块。”他给我看了一些佛罗里达本地植物,它们在这片未开垦的土地上自行生长回来。有美洲茅、美洲山核桃和野薄荷,但是,除了唯一的一只蚊子和一只巨大的香蕉蜘蛛,看不到任何昆虫的踪影。
我问霍斯特勒的邻居们对这种自然状态作何感想。他承认:“很糟糕。至少一开始是这样。但一旦我自我介绍并解释了我在做什么,他们就接受了。”我默默地看着霍斯特勒房子周围的院子;它们都有精心修剪的草坪。霍斯特勒耸耸肩:“他们大多数都退休了。我想他们除了打理草坪之外,没有那么多事情可做。”
我们花了下午的时间驾车去了霍斯特勒所知的几个昆虫天堂。当然,几乎看不到任何昆虫。在城外的一个州立保护区,我们确实发现了一只可爱、毛茸茸的小毛虫在爬行。霍斯特勒告诉我:“那些绒毛很可能是针对捕食者的防御机制。它可能会刺激鸟类的胃壁。”我们还看到了一群蠓,或者叫蚋。霍斯特勒说:“它们就像酒吧里的单身汉一样,成群结队地吸引雌性。”
回到镇上,沿着佛罗里达大学校园湖边,我们看到了一只孤单的蜻蜓(此时,我们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寻找昆虫,转而寻找校园里自由生活的短吻鳄;我们也都没看到)。我决定蜻蜓是我最喜欢的昆虫——它是昆虫界的F16。它俯冲、疾飞,充满活力地巡逻着自己划定的领地。正如霍斯特勒所描述的,它采用“偷袭”的方式,飞到毫无防备的猎物(蜜蜂、马蝇、蚊子)下方,然后向上猛冲,将它们从空中捕获。霍斯特勒在《污垢》中写道,它的眼睛巨大,像护目镜一样;它们可以左右、上下转动。
然而,最棒的还是蜻蜓的幼虫阶段。幼虫生活在水中,用位于——你准备好了吗?——肛门处的鳃呼吸。没错,就是肛门。恶心、古怪的进化,你说?胡说。这是双重用途的进化。蜻蜓幼虫能从那个坚固的孔口喷射出水,实现喷射般的加速以逃避捕食者。
最后,霍斯特勒提议带我去城外一个地方,那里夜里一片漆黑,除了24小时便利店的灯光。“如果阿拉丘亚县哪里有虫子,那儿肯定有,”他保证道。
晚上10点左右,我们沿着441号公路向南行驶约11英里,到达米卡诺皮小村庄的郊区。果然,在被黑暗包围的灯光浴中,利尔·查普食品店赫然在目。
我们走出车,寒冷中呼出的气息凝结成雾,然后走向侧墙上一盏高高的泛光灯。两只——就两只——飞蛾栖息在灯旁,冷得发抖。霍斯特勒指出,飞蛾是冷血动物,所以当它们感到寒冷时,它们会颤抖以提高体温,积聚能量以便飞行。
我们站着,也冷得发抖,霍斯特勒指着依附在Lil’ Champ混凝土墙上的无数蛾卵。他说,在雌蛾死去之前,她会尽可能多地产卵。这是确保其后代延续的另一种方式。
我总以为飞蛾愚蠢地把小脑袋撞到灯泡上。然而,事实证明,飞蛾是通过月光中发出的紫外线来导航的。霍斯特勒解释说,因为月亮离得很远,所有的月光射线几乎都是平行的。飞蛾以恒定的角度沿着这些射线飞行,这使它们能够直线飞行。(如果你想知道在无月或多云的夜晚它们怎么办,霍斯特勒说,生物学家不知道,尽管可能仍有足够散射的光线可供导航。)有人猜测,直线飞行是寻找雌性的更有效方式(我感觉这里有某种趋势)。所以,当粗心的人类带着车灯、路灯和头灯出现时,混乱就产生了,因为飞蛾会改变它们的飞行模式,以保持与每束辐射光线的恒定角度。霍斯特勒在《污垢》中说,由于飞蛾通常以小于90度的角度飞向光线,它们最终会绕着光源盘旋,越转越近,直到撞上它。
对我来说,和霍斯特勒相处一天,强化了几个观念。首先,昆虫已经进化出了一系列生存策略,但我想起,归根结底,所有的虫子基本上都想吃东西和繁殖。仔细想想,这与人类并没有太大区别。其次,在我试图观察虫子污垢的过程中,我再次发现,你无法支配大自然;她想做什么,什么时候做,都是她自己说了算。与她打交道,有时赢,有时输。或者,正如歌手玛丽·查宾·卡彭特所说,人生有时你是挡风玻璃,有时你是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