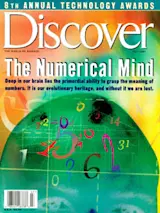为了体验生物学家乔尔·伯格的工作,我穿上了他的驼鹿服,滑下积雪覆盖的河岸,气喘吁吁地站在齐大腿深的雪中。几分钟后,我笨拙地摸索到了一头活生生的驼鹿J. Moose的30码范围内,尽管我完全没有谨慎,它仍然没有逃跑。我确信那是因为我离得不够近,构不成威胁,而且在这个严酷的怀俄明冬季生存取决于尽可能少地消耗卡路里,所以在绝对必要之前,它不会耗费宝贵的能量。要么就是它在想,哦,老兄,又不是那个穿驼鹿服的笨蛋。
尽管如此,这头体型庞大的驼鹿还是警惕地盯着我。我也警惕地回盯着它。驼鹿可能会脾气暴躁——在我看来,这与它们的体型结合在一起可不是什么好事。这头驼鹿是普通的“老艾尔”,大约七英尺高,一千磅重,鼻子下面挂着一块毛皮,耳朵像骡子,眼睛上方有十二月脱落鹿角留下的疤痕组织。欣赏驼鹿的外表可能是一种后天养成的品味。
然而,说实话,我根本看不清驼鹿,因为我的头没戴正。结果,脖子上的小网眼视孔歪斜了。当我试图把所有东西都拉回原位时,头被一根树枝卡住了,把羊毛材料完全拉到我的眼睛上。现在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你问,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如果你知道这里是二月的杰克逊霍尔,你就会问了。我来拜访伯格在他的办公室,大黄石生态系统,1800万英亩的西部地区,大致从黄石国家公园向南延伸约55英里,穿过大提顿国家公园的一部分,一直到杰克逊霍尔。正西方是提顿山脉的东坡。这里是冰川侵蚀的山峰,针叶林和开阔的起伏草地,蛇河蜿蜒其间。
伯格是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的保护生物学家,也为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进行研究,他正在研究一个当前的环境问题,他穿着驼鹿服来完成这项工作。
大约50年来,驼鹿的两个主要捕食者——狼和灰熊——已经从黄石生态系统的南部消失,被人类灭绝了。自过去两年狼被重新引入黄石以来,这些动物逐渐向南迁移,它们很快就会重新在这片区域定居。巧合的是,灰熊也正缓慢向南移动,重新定居同一区域。伯格认为,也许是灰熊数量在增加,或者1988年的黄石大火迫使它们寻找更肥沃的土地。无论原因是什么,结果是很快,大概在未来几年内,驼鹿将面临一个粗鲁的惊喜。伯格的问题是,会有多粗鲁?
着迷的我,想知道更多:随着捕食作为进化选择压力的放松,猎物——驼鹿——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识别过去捕食者的能力?对捕食者的恐惧是基因中固有的,还是后天习得的恐惧症,代代相传?如果是后者,那——哦,我在开什么玩笑?我有机会看一个成年人穿着驼鹿服四处走动。至于他研究自己的指甲,我才不在乎呢。
那么,为什么要穿这件衣服呢?毕竟,除了某些疯狂地骚扰大型动物的倾向外,谁会想打扮成有蹄类动物,在接近零度的天气里踩雪而行,然后靠近那些长腿、大蹄、脾气暴躁的哺乳动物呢?很简单。伯格必须足够靠近它们,才能把装满尿液和粪便的雪球扔过去,这就是原因。
好的。也许需要更多的背景信息。为了衡量驼鹿是否天生就能识别捕食者,伯格会扔粪球(以及适当的——这里有一个你最近可能没听过的短语——对照粪便),看看这些动物是否对气味有反应。他还使用便携式立体声播放捕食者的声音来吓唬它们(稍后会有更多介绍)。现在,伯格的投掷力道很好,但他不是罗杰·克莱门斯。为了足够靠近驼鹿进行投掷,他需要这套由当地居民制作的服装,这位居民是原版《星球大战》电影的服装设计师之一。一旦进入射程,他就会从衣服里伸出一只手臂,投掷粪便球。然后他会衡量驼鹿的反应,这可能从毫无反应到正常进食速度中断,再到盲目恐慌的全力奔跑,为生命尖叫。
他迄今发现,杰克逊霍尔地区的驼鹿对狼的气味没有反应,但对灰熊的气味有反应。(如果你想知道,伯格的灰熊粪便——嘿,哈里,有人要我们给他寄些新鲜熊粪!——和狼尿来自蒙大拿州西黄石镇的灰熊发现中心。)伯格认为,驼鹿这种适应——因为捕食压力减小而“忘记”捕食者——可能发生得很快,只需10到15代,或者50-60年。
为了验证他的发现,伯格在捕食者丰富的阿拉斯加进行了同样的粪球实验,那里狼和灰熊一直在捕食驼鹿。在那里,他发现了相反的反应,至少对狼来说是这样:当驼鹿闻到狼尿的味道时,它们的进食速度会下降。至于对熊的普遍反应,伯格推测驼鹿可能对灰熊有更强的识别能力。有趣的是,他发现杰克逊霍尔的驼鹿也对西伯利亚虎粪便的气味有反应(粪便来自安克雷奇动物园)。
记住,除了叉角羚,所有有蹄类哺乳动物都是通过白令海峡来到北美洲的,所以驼鹿在某个时候曾被老虎捕食过,伯格说。可能老虎和灰熊是更高效的猎手,它们的记忆只是更强烈地印刻在驼鹿身上。话又说回来,这项研究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这套驼鹿服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通常伯格和他的妻子兼研究伙伴卡罗尔·坎宁安一起穿着。伯格在前面,戴着高大的头部,配有黑色纽扣眼睛、下垂的口鼻和毛绒耳朵。坎宁安必须弯腰,将棕色的毛茸茸的布料披在自己身上,以模仿驼鹿的身体。这套服装只到腰部,露出这对夫妇的腿。显然驼鹿对它们和谁在一起并不挑剔。为了移动,伯格和坎宁安必须协调前后肢的运动——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因为四条腿在不同的时间穿过深雪。
我到达的第一天,与伯格见了几个小时。天气非常寒冷(气温2度),阴天,预计会下雪。在那个恰如其分地名为驼鹿的小村庄租了雪鞋后,我们向北开了几英里,然后去散步。伯格走在前面,拿着驼鹿头、小背包和一根滑雪杖以保持平衡,轻松地爬上一段陡峭的雪坡。我跟在后面,穿着雪鞋笨拙地摇摇晃晃。到达顶部时,我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赞叹。从那里,我可以以提顿山脉为背景,看到一幅哺乳动物的全景。正前方是两群驼鹿正在啃食柳枝——木材——它们基本的冬季食物。舞台右侧是一群麋鹿,有的在吃草,有的躺着。最右边是一头独行的麋鹿,正在吃草,似乎对50码外三四只狼正在盯着它,舔着嘴唇毫不在意。唯一缺少的是火箭浣熊和皮博迪先生。伯格笑着说:“真是个大草原,对吧?”他正在寻找一头特定的母鹿和它的小鹿,最终他在大约80码外发现了它们,但它们正朝远离我们的方向移动。由于天色已晚,而我冻得脸色发青,我们放弃了追逐,返回城镇。
第二天:气温2度。加上风寒效应:我不想知道。当我把租来的车开过来时,伯格正站在他那辆破旧的大众面包车车顶上,似乎对寒冷毫无察觉,摆弄着一个像是电视天线的东西。坎宁安站在旁边。这天线是无线电接收器的一部分;为了在凶猛的狼群到来之前获取驼鹿行为的信息,伯格给20头母驼鹿戴上了无线电项圈。他告诉我,检查一个物种强健程度的一种方法是跟踪繁殖率。伯格通过收集每头母驼鹿的两份——还有什么?——粪便样本来做到这一点。他把它们储存在冰柜里。一旦所有样本都收集完毕,他就会把它们送到实验室检测孕酮水平是否升高,这表明怀孕。
说话间,伯格正把天线转来转去。驼鹿的距离由接收器发出的蜂鸣信号强度表示,伯格像背相机一样把接收器挎在肩上。蜂鸣声越强,驼鹿越近。他接着说,一旦它们生下小牛,我们就会追踪小牛的存活率。(至少,我想他是这么说的,但我承认我没有我应该有的那么专心。相反,我正在数我的四肢,漫不经心地想着眼睛里的水是否可能结冰。)在确定信号来自哪个方向并实际看到一头驼鹿之后,伯格通过剪掉的耳朵上的一个缺口来识别这头特定的动物。他告诉我,在冬天,当公驼鹿脱落鹿角时,区分公驼鹿和母驼鹿最简单的方法是看母驼鹿外阴周围的白色斑块。
伯格收到一个动物的信号,但它来自附近流淌的格罗斯文特河对岸。谢天谢地,伯格不愿意涉水过去,他建议我们挤进他那凌乱的面包车,沿着89号公路向北行驶;前面,有三辆车停在路边。加入他们后,我们看到两头驼鹿正在路边吃柳枝。伯格决定这是演示驼鹿服的好地方,但他想等到一些忙着拍照的游客离开。
伯格讨厌吸引人群。他一本正经地说,这倒不是因为人们烦人,而是我曾被公园管理员训斥过,说我造成了交通危险。他费尽心思讨好每一位管理员,但正如我所看到的,打扮成驼鹿并保持低调是相互排斥的。与此同时,伯格开始准备。他伸手去拿一个水瓶,然后咒骂起来。该死,他说,狼尿冻住了。果然,塑料瓶鼓鼓囊囊的,看起来像一个尿液手榴弹。由于坎宁安很快就要去上班(她在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兼职生物学家),伯格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演示驼鹿服。
终于,游客们离开了,两人穿上衣服。伯格戴上驼鹿头显得非常巨大;它比他5英尺11英寸的身高高出足足两英尺。然而,坎宁安的工作更困难。她背着一个小背包,给身体增加体积,必须弯腰行走,无法看到。两人现在沿着公路稍微侧身行进,从侧面接近驼鹿。一辆车驶来,然后停在路中央,车里的人们盯着看。接着,一辆载满日本游客的巴士驶过;尽管我能看到很多人在惊呼和指指点点,但巴士没有停,一直开到四分之一英里外才停下来。然后它开始倒车。最后,另一辆车从相反方向驶来,也停在车道上。现在道路双向都被堵住了,一辆载满兴奋的日本游客的大巴车正在高速公路上倒车。
在所有的喧闹声中,一头驼鹿明智地跑开了,笨拙地翻过栅栏,小跑着离开了。我发誓,它跑的时候,一直回头望着伯格和坎宁安,脸上带着“搞什么鬼?”的表情。又过了几分钟,当两人在深雪中缓慢挣扎着靠近剩下的驼鹿时,那两辆车和那辆大巴车——车上的人显然很容易感到无聊——终于开走了。
为了更好地观察(我带了相机),我走近了一些,当我不小心吓到了最后一头驼鹿时,我感到很尴尬,它突然转身走开了。伯格礼貌地建议我下次站着不动,并且最好找一个更隐蔽的地方来演示这套衣服。当我们开车四处转悠时,伯格偶尔会停下来进行无线电检查,我问他们穿着驼鹿服最尴尬的时刻是什么。
事实上,最尴尬的时刻并不是我们穿着驼鹿服的时候,坎宁安说,而是我们用无线电接收器追踪的时候。当驼鹿被杀死时,无线电信号的节奏会变为死亡模式,提醒研究人员(当项圈停止检测运动时,信号会改变)。伯格和坎宁安在杰克逊霍尔外的一个高高的悬崖上接收到了这样的信号。但他们离城镇越近,信号就越强。直到最后,我们进城了,走在人行道上,乔尔把天线拿在前面,人们盯着我们看,然后侧身让我们过去。你可以想象那些评论。结果是一位生物学家发现了死去的驼鹿,取下了项圈,带回了他的办公室。两人最终找到了他的家门。
后来,我们沿着一条废弃的小路开车,穿过深雪和突出的灌木丛,小心翼翼地走在结冰的溪流上,最后放弃了,却看到三只驼鹿突然出现在离我们不到50码的地方,从树林里出来,站在路中央。
伯格和坎宁安迅速穿上驼鹿服,悄悄地向那三头驼鹿走去。这次我远远地站在后面,手里拿着相机。两人几乎进入了投掷范围(当然,如果尿液可以投掷的话),这时一辆白色面包车驶到我们旁边。两头驼鹿犹豫了一秒钟,然后跳进路边的深雪中。司机对伯格和坎宁安连看都没看一眼,径直慢慢地驶向第三头驼鹿,那头驼鹿站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可以说,小跑着沿着路跑去。我至少观察了四分之一英里,那头驼鹿拒绝让路,只是在面包车前面慢跑,时不时地回头看一眼,直到两者都消失在拐角处。
当伯格开始脱下他的头时,一辆皮卡车驶过来停下。这个害羞的家伙笑着,拿着相机跳下车。他恳求伯格把头戴回去,这样他就可以拍照。伯格照做了,那人拍了一两张(而我拍了那人拍照的景象)才终于离开。
两人走过来。这是摆脱他的最快方式,伯格说。
他甚至问你为什么打扮成驼鹿吗?我问。
没有,坎宁安摇了摇头说。他只是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告诉他我们是来自内华达州的游客,伯格说。
后来我大声想知道驼鹿看到这套衣服时是否会感到困惑。
“有可能,”伯格说。“有几次我把头套摘下来,扔来扔去,看看它们的反应。它们只是盯着看。”
“通常,当我们靠近放置尿液时,我做得很慢,”他补充道。“至少需要半个小时。我会停下来,低头假装啃食。今天的演示是相当人为的;通常驼鹿不会直接走到其他驼鹿面前。”
我们又发现了更多的驼鹿。伯格把车停在路边,给我看他的音响系统。除了向驼鹿投掷捕食者粪便外,他还播放威胁生命的声音,看驼鹿是否有反应。伯格使用便携式录音机和扬声器,播放狼嚎或乌鸦叫的声音。为什么是乌鸦?因为它们是食腐动物,伯格认为它们的叫声也可能吸引食肉动物,这对驼鹿来说是坏消息。同样,伯格通过计时动物停止进食的时间来衡量反应。(此外,作为对照,他还播放无威胁的声音,如水流声或昆虫嗡嗡声。)他再次发现,杰克逊霍尔的驼鹿对狼或乌鸦没有反应,而他在捕食者丰富的阿拉斯加研究的对照组驼鹿则有反应。
我问他驼鹿是否会很快重新学习狼的危险。伯格耸耸肩说:“我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这项研究能持续五年;我们希望能弄清楚,但这确实有道理。不过,在此期间,最大的输家将是小牛。目前,杰克逊霍尔小牛的年度存活率接近100%;然而,在阿拉斯加捕食者众多的地区,食肉动物每年要吃掉60%到80%的小牛。幸运的是,驼鹿是世界上少数尚未濒危的大型哺乳动物之一(讽刺的是,它们的捕食者却濒危了)。”
一天结束,我的访问也告一段落,轮到我扮演驼鹿了。令我大失所望的是,天依旧太冷,雪无法凝结成团。这意味着我不能赤手拿着沾着尿液的雪球,获得一生中只有一次的机会,朝驼鹿扔尿。尽管如此,我确实学到了一点:当一名戴着驼鹿头的野外生物学家绝非易事。(好吧,从技术上讲是的,因为这里是国家公园,但你懂我的意思。)我知道这一点,因为当我尝试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挣扎着把歪斜的头上的眼孔重新定位时,被一根树枝挂住了。为了避免搞砸伪装,因为附近有一头驼鹿,我对着一些柳枝点点头,笨拙地假装像真的驼鹿一样吃东西。
最后,我调整好姿势,从眼孔往外看,但那头驼鹿已经失去兴趣了。它轻蔑地哼了一声——无疑是嘲讽——然后转身慢慢走开了。我摘下头套,感觉自己不像驼鹿,倒像个傻瓜。
当你打扮成驼鹿时,尊严就得留在门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