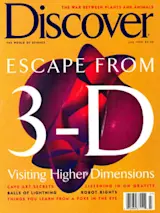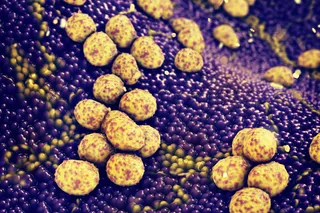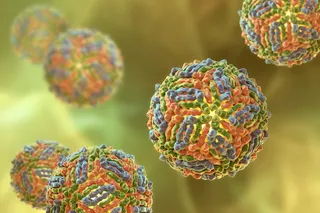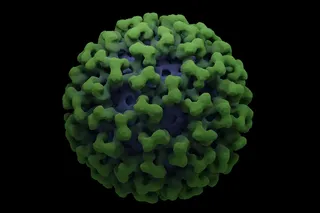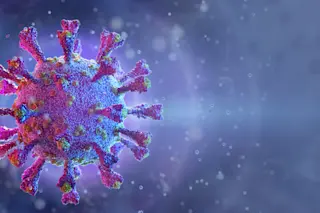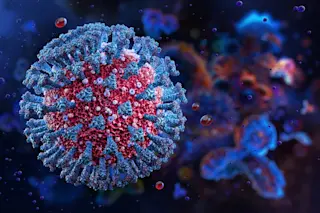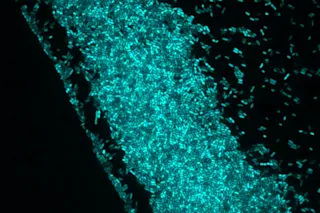1989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在布朗克斯一家精神病院的封闭病房里第一次见到Shannon Connolly。她是因为试图自杀而入院;而我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当天早上她曾问过精神科医生,是否可以找一位艾滋病专家谈谈她的病情。
当我敲响她的房门时,她蜷缩在床上,一动不动,脸朝向墙壁。但当我走进去时,她坐了起来,伸出了手。“非常感谢您来看我,”她说。她32岁,瘦骨嶙峋,面色苍白,头发稀疏,更显得她骨瘦如柴。她的一只眼睛有些发黑,大部分牙齿都掉了。手臂上布满了多年海洛因滥用留下的针孔痕迹。但她的眼神坚定,握手有力;她微笑着示意我坐下时,我努力回想,上次有病人如此礼貌地对待我是什么时候。
“我想见您,因为,嗯,我昨晚在病友会议上告诉大家我患有艾滋病,”Shannon说。“医生们知道,但其他病友以为我只是因为非常沮丧才住院。他们非常生我的气——你知道人们对艾滋病的态度。我感到不安全。没有人跟我说话。我太害怕了。我害怕一切。我该怎么办?”
边哭边擤鼻涕,Shannon的故事娓娓道来。她声称自己曾遭受父亲虐待,17岁离家出走,从那时起就一直在吸毒,时而做妓女。这是城市内部艾滋病患者中一个熟悉的故事,而Shannon明显的智力使这个故事更加悲惨。她说,她小时候想当兽医,毕业于新泽西一所郊区的高中,甚至上过一些大学程度的生物课程。但当她在1987年被检测出HIV阳性(导致艾滋病的病毒)后,她便陷入了药物滥用,只有偶尔住院才能打断。
像大多数重度吸毒者一样,Shannon过着混乱不堪的生活。她很少有固定的地址或电话号码,更不用说医生、牙医或律师了。当她感到不适时,她会去最近的急诊室;她不定期去诊所,也不服用除偶尔在街头购买的止痛药以外的任何药物。但她对自己的病情有着 remarkable 好的理解,并向我清楚地解释了她之前所有住院的情况。
她告诉我,1988年,在另一家布朗克斯医院因高烧入院后,她接受了经支气管镜肺活检——一项在显微镜下检查一小块肺组织的手术。结果她患上了卡氏肺孢子菌肺炎,这是艾滋病患者中最常见的感染。她说她对喷他脒(一种治疗这种肺炎的标准药物)反应良好,但几个月后在另一家布朗克斯医院被诊断出第二次患有卡氏肺孢子菌肺炎。
Shannon告诉我,此时,她的CD4细胞计数(衡量HIV感染者免疫系统受损程度的指标)已从每立方毫米血液约1000个细胞的正常水平下降到仅8个。她的医生解释说,如此低的计数意味着她将极易受到一系列艾滋病相关感染的侵害,他们曾考虑给她开始使用AZT,这是我们治疗艾滋病患者最有用的药物。但当她提醒他们,她年轻时曾切除过一个肾脏时,他们改变了计划,担心这种有毒药物会对她仅存的肾脏造成损害。
所以,她说,她上次出院时一无所有——没有希望,没有药物,什么都没有。她说,在那次经历之后,她仔细考虑了许多事情,并决定勇敢地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她不再需要CD4计数,不需要输血,不需要实验性药物,不需要任何绝望的措施。“我不会让这种疾病剥夺我的尊严,”她说,下巴抬起。
Shannon显然正处于艾滋病患者常见的间歇期之一,即在毁灭性的传染病发作之间的一段健康时期。确实,她非常消瘦——她身高5英尺9英寸,体重只有100磅左右——但此刻她没有严重的感染。事实上,我只发现了一些淋巴结肿大——这与药物滥用和艾滋病都有关——以及她肾脏手术留下的一个大疤痕。
在我看来,Shannon是接受AZT治疗的理想人选,即使只有一个肾脏。虽然AZT不能治愈艾滋病,但它可以延长这些间歇期,有时甚至能导致体重增加。但最重要的是,Shannon需要一个友好、稳定、永久的医疗保健场所,一个可以通过早期诊断和干预来避免重大艾滋病相关灾难的地方。
于是,我为她预约了我们的艾滋病诊所,并请她安排将她在其他医院的病历副本寄给我们。(病历只能在患者签署同意后才能从一家医院转到另一家医院。)当没有病历寄来,而且在她的预约当天她也没有出现时,我并不太惊讶。我们接诊的患者经常住院、被监禁或有其他事务缠身,因此他们迟到的概率总是很高,而且他们的文件似乎总是被忽略。当Shannon在几个月后出现时,她说她忘了寄病历。
在接下来的 L一年里,Shannon忠实地参加了我们的诊所。像我们的大多数患者一样,她有一些我们试图适应的怪癖,希望让她留在医疗保健系统中。其中最突出的是她非常不愿意抽血。我们会把验血单给她,让她去化验室;她会说头痛、肚子痛、有紧急预约,然后离开医院,弄丢单子——当她一个月后再次出现在诊所时,整个过程又会重新开始。
身体方面,她有起有伏。开始使用AZT后,她体重增加了六磅,但很快又减掉了。然后她开始抱怨头痛和身体左侧轻微无力。她的症状非常像艾滋病相关的脑部感染,于是我将她收入院。但即使进行了各种神经学检查,我们也无法找出她症状的原因。
在她住院期间,一位营养师建议我们开始通过静脉输注高蛋白液体来补充Shannon的饮食。令人惊讶的是,Shannon对这种高科技的增重方法欣然接受。所以当她出院时,她的脖子上安装了一个永久性静脉导管,并且每天晚上需要连接装有营养液的夸脱瓶。
几周后,凌晨三点,我被急诊室的电话吵醒。Shannon被救护车送来,奄奄一息。我们很快意识到她血液中发生了感染,可能是因为她的导管变脏了。她病危了好几天,直到通过大剂量抗生素治疗才开始好转。我们安慰她,她所经历的不是艾滋病,只是一种普通的、难以治疗的感染。然后,就在她即将出院时,感染突然复发;她又在医院待了一个月。
当她终于出院时,她依然消瘦,向她的“粉丝”们挥手告别:在艾滋病病房住了三个月期间,她成了护理人员和病友们心中的英雄。她因乐观、勇敢以及提供关于如何应对艾滋病的实用技巧而受到钦佩。Shannon似乎什么都知道:哪些社区教堂会给艾滋病患者免费食物,哪里可以给艾滋病患者找到一件小尺码的免费牛仔裤,如何写最好的遗嘱。
出院后,Shannon继续抱怨左侧身体虚弱。她说她的记忆力越来越差——她总是忘记服用AZT。在她正式被诊断为艾滋病两周年之际,她情绪低落,并立了一份新的遗嘱。她出现严重的头痛。显然,我想,她需要做MRI检查,以确保大脑没有感染潜伏。但要获得这项价值一千美元的检查的批准,我需要与一位神经放射学家一起回顾她的病史。于是,一个傍晚,我叹了口气,拿起她厚达五卷的病历。然后,一切都清晰起来了。
我是否只是心情多疑,还是不知不觉中我一直在默默关注着Shannon?Shannon和她一年来鲜有典型的艾滋病相关并发症。Shannon和她对验血的厌恶。Shannon和那些至今未到的病历。
我突然意识到,一个医生面对着病人在检查室的桌子对面,会自动地接受多少信息。我们几乎从不质疑病人讲述的历史是否属实,病人声称的症状是否真实存在,开出的药物是否被真正服用,以及我们想看到的病历是否真实存在。经过多年训练培养出的每一种医疗直觉,都建立在病人说真话的确定性之上。当这种确定性消失时,就没有规则可循了。
下次在诊所见到Shannon时,我告诉她我必须自己给她抽血。她耸耸肩,伸出胳膊。我抽了四管血,将其中三管送去进行CD4计数,将一管放入冰箱,并决定暂时不安排她的MRI检查。十天后,CD4计数结果出来了。Shannon不是8个,不是80个,而是每立方毫米血液中有1000个CD4细胞。免疫学上她是正常的。
在纽约州,未经被检测者明确同意,不得进行HIV感染检测。尽管该法律的目的是保护HIV感染者的权利,而不是未感染者的,但我仍然觉得在未经Shannon知情的情况下检测她有所顾忌。也许一切都是误会。也许她的检测在实验室被弄混了。也许其中一家医院不知怎么把她和其他病人搞混了,误诊了她的肺炎,错误地编码了她的结果。也许她从艾滋病中奇迹般地、前所未有地康复了。
在她下一次预约时,我热情地对她说:“Shannon,好消息,你的免疫系统恢复得非常好。”她欣喜若狂,并将其归功于我的悉心照料。“我想我们应该再做一次HIV检测,只是为了确保没有错误,”我小心翼翼地说,担心她会变得防御或甚至打我。相反,她愉快地签署了同意书,并让我抽了血。访问结束后,她感谢我带来的好消息,然后走出了诊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Shannon两次HIV检测结果都呈阴性。我让实验室重复了第三次检测。仍然没有错误。她再次测量的CD4细胞计数为1200。我乘地铁去了她声称首次被诊断出卡氏肺孢子菌肺炎的医院,并要求查看她的病历。病历非常厚,但里面没有提到肺炎或艾滋病。她曾多次因抑郁、精神行为异常和血尿(尿液带血)去看病。1984年,一位医生曾怀疑她反复发作的血尿——他找不到原因——是否可能是人为的,由病人自己制造的。
我去了她提到的第二家医院,找到了另一份厚厚的病历。这份病历记录了类似的急诊就诊,包括抑郁、血尿,以及一次,一年多前,关于AZT处方。她告诉他们,她在我们医院被我诊断为艾滋病和卡氏肺孢子菌肺炎。
几个世纪以来,病人一直在装病。有些人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样做:为了逃避兵役而跛行的年轻人,为了获得麻醉药而装作背痛的瘾君子。对另一些人来说,医生、护士和医院的世界,也许是在童年疾病期间第一次体验到的,却证明是一个诱人的滋养环境。为了回到那种爱和关怀,他们可能会不遗余力地让自己生病并保持生病,遭受危险的医疗程序,甚至自残。(Shannon的静脉导管是怎么变得那么脏的?)
一小部分病人会捏造自己的疾病,据说他们患有“谎报病”(Munchausen syndrome),以18世纪德国说书人男爵冯·明希豪森的名字命名,他到处游历,编造各种离奇的故事。谎报病患者在医院之间游荡,编造越来越离奇、完全虚构的病史,寻求手术、药物和诊断。精神科医生认为这些病人几乎无法治愈。他们经历了无数次手术,服用各种不明组合的药物,他们经常在病房里制造混乱,藐视常规规则和规定,要求特定的药物和治疗,并且在医生开始怀疑时,总是在一番盛大的表演后消失。
一位谎报病患者——他在20世纪70年代十年间,在退伍军人事务部医院辗转就医——累积的医疗档案重达近50磅。在一年内,他被送往美国39家不同的医院。这个病人通过吞咽勺子,反复获得了复杂腹部手术的机会。他反复被诊断出患有肾结石,方法是让他将一块棉花浸入自己的血液中,然后塞入尿道,这样他就可以随意排出带血的尿液和血块。在讲述自己的病史时,他曾先后声称自己是自由撰稿人、飞机修理工、美国原住民和波斯海军指挥官。
Shannon是一位现代城市里的谎报病患者。她装病的不是多种疾病,而是那种城市年轻人像医生一样了解的疾病的各种表现。她不跨越全国,而是穿梭于布朗克斯,那里复杂的医院官僚体系、疲惫的工作人员以及严格的HIV保密法为她的伎俩提供了完美的保护。就像男爵冯·明希豪森本人一样,Shannon给我们讲述了我们都想听到并相信的美妙故事。我们钦佩她勇敢地面对绝症,并被她对我们关怀的深切感激所感动。典型的谎报病患者是敌对且难以相处的,但Shannon有更好的技巧。她告诉我们我们想听的话。
我从未弄清楚她讲述的生活中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虚构的。她只是消失在纽约市的毒品世界里。两个月后,我们的社工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一位与Shannon相似的病人正在曼哈顿一家医院的艾滋病诊所就诊。不到一周后,又接到一个电话,这次是警方打来的。Shannon在她公寓被发现,死于海洛因过量。她在桌子上发现了我们社工的名片。
我们都不知道该作何感受。医生和护士习惯于哀悼病人的死亡——尤其是在艾滋病诊所。但我们通常可以安慰自己,知道我们帮助他们活得更长,或者至少活得更好。我们能说Shannon也是如此吗?回想起她给艾滋病病房其他病人带来的纯粹的慰藉,我仍然想知道,我是否能找到更好的方法来阻止她昂贵且自毁的艾滋病“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