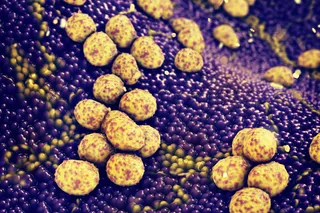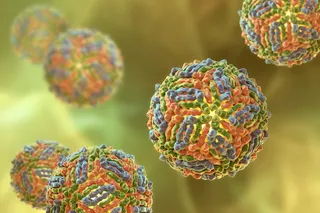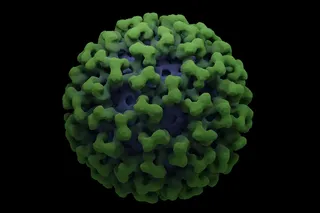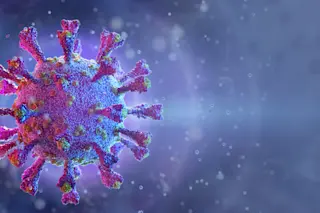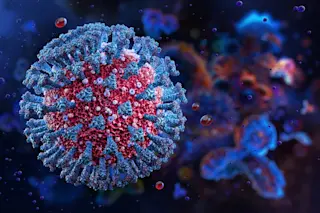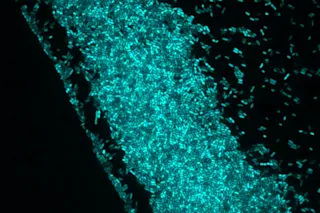在《发现》杂志11月刊中,我们评论了记者西莉亚·法伯备受争议的书籍《严重不良事件:艾滋病未删减史》。法伯在艾滋病领域工作了二十年,她的作品涵盖了所谓的艾滋病异见者——那些质疑艾滋病与艾滋病病毒关系、主流治疗方法以及科学界向公众传播艾滋病信息的人。在这篇独家网络报道中,《发现》杂志编辑苏珊·克鲁格林斯基采访了法伯。
你的写作被认为是备受争议的。你刚开始写这些的时候得到了什么样的反应,在过去的22年里又有什么变化?
我关于这方面的工作始于1986年。当我开始研究艾滋病时,我当时是SPIN杂志的研究助理。我们最终开设了一个名为“前线之声”的月度艾滋病专栏。这是鲍勃的主意(小鲍勃·古乔内,现任《发现》杂志首席执行官)。他说艾滋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越南战争。第二篇专栏是对彼得·杜斯伯格博士的采访。当时我们认为我们正在做非常直接的报道,但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我们很快意识到我们触犯了一个主要的禁忌。而这个禁忌就是质疑任何正统的东西——任何所谓的艾滋病教义。
我实际上并没有像一个完全着迷的人那样,连续22年地关注这个故事。相反,发生的情况是,我帮助这个故事进入了主流媒体,并且它开始不断发展壮大。它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我最初的梦想。
情况已经改变,因为正统观念所宣称的许多事情都没有实现。这个范式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惨遭失败。因此,现在的正统观念对任何被他们称为艾滋病否认者的人都特别恶毒和残忍。
这个范式有哪些失败之处?
最主要的一个是曾经被称为“异性恋艾滋病大爆发”的模型。它是艾滋病病毒理论的核心——认为存在一种致命的病毒,可以通过无保护性行为、针头和其他传播方式(血液传播)传播。他们实际上说的是存在一种三级传播模型。所以,任何与曾经是吸毒者的人睡过的人、与和吸毒者睡过的人睡过的人等等,都可能被感染。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模型。
所谓的异见者一直关注的一项研究是伯克利研究员南希·帕迪安的研究。她的研究考察了伴侣之间一人阳性一人阴性的传播情况。他们进行了无保护性行为。他们在10年期间对他们进行了观察。在整个群体中(在10年的研究中),没有一例传播——一例都没有。[引自研究论文:“总体而言,360名艾滋病毒感染男性伴侣中的68名女性(19%)(95%置信区间(Cl)15.0-23.3%)和82名艾滋病毒感染女性伴侣中的2名男性(2.4%)(95% Cl 0.3-8.5%)被感染……传播发生在研究开始之前……随着时间的推移,作者观察到避孕套使用增加(p <0.001)且没有新的感染。”]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嗯,对此在互联网上引发了一场喧嚣,一场激烈的辩论。至少,这意味着艾滋病毒的传播极其困难,这与我们被告知的恐怖、恐惧、鼠疫模型截然不同。这只是第一部分。我个人最感到震惊和不安的是关于AZT的历史部分。当我们对SPIN杂志进行最集中的报道时,正值AZT狂热的巅峰时期。AZT被给予极高剂量。它是一种在60年代开发的化疗药物。非常粗糙,毒性极强——有些人说它是迄今为止给予人类的最毒的药物。在AZT热潮的最初几年里,给予1800和1200毫克的剂量,人们死于非常明确的AZT死亡。当时有些人说:“是AZT杀死了这些人。”而绝大多数人则说:“这太疯狂了。是病毒杀死了这些人。”这就是AZT第一次真正划清战线的地方。AZT杀死了他们——不是病毒,不是疾病,而是药物本身。
那么还剩下什么呢?他们寄予厚望的是鸡尾酒疗法。而这些鸡尾酒疗法,蛋白酶抑制剂等等,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们的毒性远低于以前。而且,确实,人们的死亡率不再像以前那么高了。还有广谱抗生素和抗菌药物。所以,人们确实通过这些药物从这些复杂的免疫疾病中恢复过来。
所以您不认为AZT延长了生命?您不会把它与化疗或放疗相提并论,后者最初延长了生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必须进行修改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并减少毒副作用?
AZT 的历史奇怪之处在于。在细胞层面,艾滋病与癌症相反。癌症是细胞增殖。而艾滋病是细胞系统的衰减。提供的第一种药物是衰减细胞系统的药物。为什么?为什么要用强效免疫抑制剂治疗免疫抑制?这在癌症中说得通。但在艾滋病中说不通。所以这是一个我无法回答的谜团。我不认为他们(医学界)想杀人。我将其归因于当时的恐惧。对病毒的恐惧已大大消散。他们以前基本上会说你会像鼠疫一样倒在街上。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恐惧,它是在数据之前发生的。而且它依赖于那些病得很重、死得很快的人群。
我想,AZT 在 17 周内就获得了批准。药物审批过程本身也进行了改革,以适应这种可怕药物的审批。而这是一旦发生就无法回头的事情。我不相信快速加速的药物审批过程。但现在,在后 AZT 时代,唯一的观点是越快越好——这种关于药物进入市场以及在人群中进行药物测试是可以接受的全部想法。
再次强调,您不相信AZT延长了寿命吗?不。
回到南希·帕迪安,她是不是觉得你曲解了她的研究?那里有没有争议?南希·帕迪安很不高兴像我这样的人引用她的研究,因为她不希望她的研究被用于她所谓的否认主义讨论。但数据就是数据。大多数人说:“嗯,传播起来很困难。”然后你就会进一步细分成不同的阵营。有多难?是不可能吗?还是几乎不可能?
那么,您是否相信该疾病不可能通过性接触传播?我在纽约市居住了二十多年,我不认识任何通过性接触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我采访过从许多不同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人。有一些假设我还没有完全研究完。所有这一切的核心是艾滋病毒抗体检测。如果您非常非常仔细地查看艾滋病毒抗体检测,您会发现它检测的是某些蛋白质,这些蛋白质被认为是构成一种新型逆转录病毒的。因此,所有这一切的原初起源是一个问题——当我们谈论传播,当我们谈论帕迪安时——我们所谈论的一切都通过检测的过滤,通过我们通过抗体检测所看到的一切。当涉及到艾滋病毒的传播以及是否可能通过性传播时,我必须回到我所坚持的立场,那就是辩论、阅读和审查、对话、讨论和辩证法。我对许多许多问题没有答案。包括那个问题。
我不是一个安全性行为教育者,也不是一个公共卫生倡导者。我是一名记者。所以我必须让自己远离那些问题,并说:“它在我的作品中。它在我的书中。它在我写过的所有东西中。”我希望人们阅读我的书,然后他们会看到,在那本书中,我是一个承载着关于这个范式背后数据的所有类型问题、担忧和焦虑的容器。而不是一个像“我明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的人,一个dictate真理的人。我像一个人类问号。
在你的书的引言中,你写道你不是科学家,你不能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只是在呈现人类的戏剧。但是,你长期报道这个争议,这本身难道不是一种表态吗?我认为这是本世纪的故事。这是一个巨大的故事,它直接涉及信息时代的真相,以及我们如何知道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媒体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制药时代和生物技术时代,科学的灵魂是什么?
但你显然隶属于这个故事的一方。这是一个公平的问题。一开始,我采访彼得·杜斯伯格是作为一篇直截了当的新闻报道:“顶级逆转录病毒学家称艾滋病毒不会导致艾滋病。”让我们看看他怎么说。当这篇报道发表后,我受到了攻击。当你受到攻击时,你必须开始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辩护。然后你就会陷入一种复合——螺旋式上升的局面。当受到攻击时,你会变得更加“狂热”,因为你试图捍卫你的第一个行动,你认为那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报道。所以你被那些试图让你沉默的力量激进化了。在这些攻击面前坚持下去,这才是激进的行动。我并不是非要和那些不认为艾滋病毒导致艾滋病的人交谈,而是我被推入了一种未知领域。
为什么主流媒体不报道这个呢?嗯,《哈珀斯》杂志是主流媒体,你不觉得吗?[“失控:艾滋病与医学科学的腐败。”西莉亚·法伯,《哈珀斯杂志》,2006年3月。]
但是你真的没有看到其他记者报道这个。我想你应该问问他们。我想他们知道这首先是一种职业威胁。他们脊柱里能感觉到。
那主要期刊的观点呢?他们似乎已经达成共识,反对杜斯伯格和艾滋病异见者。我个人认识几十位艾滋病毒阳性、20多年来身体完全健康、未服用任何药物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人。他们很常见,并不罕见。文献中至少有5000例完全发展的艾滋病病例——即免疫衰竭但没有艾滋病毒痕迹(根据杜斯伯格的说法)。正统观点认为,艾滋病毒平均可能需要长达15年,甚至可能长达30年才能导致艾滋病。公平地说,这更接近异见者的立场,而不是22年前声称艾滋病毒会立即导致艾滋病的正统立场。所以我敢说,他们的范式已经从最初的形式被拉伸到面目全非。
我的叔叔在早期就得了艾滋病,我不同意它被描述为一个瞬间杀手。 我说的是,他们向世界上的性活跃人群判了死刑,有些人说他们有权比实际情况更加严厉和恐惧。我个人一直觉得,说“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死”是一种侵犯。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他们给了人们多少时间?他们给了六个月,一年,五年?无论如何,你难道看不出这是武断的吗?他们没有知识,没有权利那样做;他们应该说:“我们有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但他们从没那样做;他们陷入了这种几乎是法西斯式的通用语,这种教条。
所以,您对医学界看待这种疾病、其病因的方式存在异议。然后是治疗方式,即药物角度。还有医学机构向公众传播疾病信息的方式。那么,所有这些的更大意义是什么?您对医学界的论点是什么? 我觉得我得出的结论是,在美国生物技术蓬勃发展时期,随着制药行业的突然爆炸式增长——我将其大致追溯到艾滋病爆发时期——医学和科学被一种近乎工业革命般的经济利益所裹挟,这极大地混淆了真相、数据和现实,并给系统带来了新的恐惧。这并非全是金钱,但金钱是故事中一个巨大的部分。医生们甚至在给病人看病时,都很难把制药公司的销售代表挡在诊室门外。
然后是科学本身,我想说,如果我必须简单地说,它已经不再渴望好奇心了。许多科学家都在谈论这一点——如果你违背了当时的教条,老天爷都不会帮你。而当时的教条,你会发现,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由当时的既得经济利益驱动的。
您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审阅了科学界所有相关文献的人会质疑您的观点吗?
不,因为我从未提出过论点。我发表的所有内容都是砖块、砖块、砖块、砖块,都是发生过的事情,人们死去,科学家和医生说了X、Y和Z。《哈珀斯》杂志的文章开篇讲述了乔伊斯·安·哈福德的故事,她是一名在田纳西州被奈韦拉平(一种用于治疗HIV-1感染和艾滋病的药物)杀害的黑人妇女。她的孩子得救了;她却死了。他们告诉她的家人她死于艾滋病。我在文章付印时就在想,现在会发生什么,看看它是否会被理解为页面上的内容,或者他们是否仍会用所谓的我的论点来攻击我。我没有提出论点。我报告事实,发生过的事情。这是实地采访的报道。我希望人们看到这些,并说:“她编造的吗?她编造了这个人吗?”嗯,如果她没有编造,那么我们确实有值得担心的事情,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她的个性。而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女人可以像豚鼠一样被杀害的文化中。这就是NIH赞助这种试验和类似试验时发生的事情,世界各地每天都有人在人体实验中死亡。
对,但是人体实验和临床试验是完全不同于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的问题。
但是您理解我从未说过艾滋病毒不导致艾滋病吗?我所说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艾滋病毒导致艾滋病。这是对艾滋病辩证法现状的客观描述。
有些人认为,宣扬所谓的艾滋病异见者信仰可能会导致生命代价。您认为这可能是真的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立即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这是报道的区分,介于实际发生的事情和我们强加于发生的事情之间。那个核心完全由透明度构成;报道就是从那里开始的。1987年,根据罗伯特·加洛的说法,全国顶尖的逆转录病毒学家彼得·杜斯伯格发表了一篇论文,质疑当时正在出现的信念,即a)逆转录病毒导致癌症,b)逆转录病毒是艾滋病的病因。在我看来,这是新闻,简单明了。如果你的工作是报道艾滋病的科学现状,那肯定是一个事件。就像长颈鹿出现在华尔街一样。意想不到的、反常的——这就是作家在大多数传统中的建筑材料。你从冲突开始,然后寻求解决以学习教训。一场分裂发生了,事实上是病毒学领域的一场史诗般的裂痕,而我就站在那里。
是的,采访“错误”的人有风险,但也许不采访他们,因为他们可能错了——将这个过程拱手让给自封的权威、当权者、行业,风险更大。在科学领域,如果有人错了,以前这并不是世界末日。我们现在真正看到的是,在巨大恐怖时期,科学过程和精神的死亡。正如诗人查尔斯·斯坦所说:“一切通过反转都是真实的。”我们必须有勇气从各个角度看待事物。
你问:如果你采访的、你报道的科学家错了怎么办?我的回答是:那他们就错了。我无法让他们不复存在。他们确实存在。这是第一件事。我直接回答你的问题是,是的,数千名从多个角度反对艾滋病毒范式的科学家可能是错的。当我开始采访这些未被听到的声音时,我无法知道他们是否正确,但我没有要求他们在发表意见之前证明他们是正确的。我发表他们的意见是为了探索问题,追根究底。二十年后,这个问题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一样,现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变得越来越大。
加洛是如何登上那个讲台的?他展示了什么?是逆转录病毒吗?和[法国病毒学家吕克]蒙塔涅的相同吗?最重要的是,这个检测是如何构建的?它检测的是什么?最初的那些蛋白质是如何选择的,它们又代表什么?今天它们还代表同样的东西吗?近年来,我通过研究艾滋病毒检测的微观事实和历史,已经走到了终极存在冲击的边缘。这个冲击是:我们一直在检测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吗?某种一直存在于我们DNA中的东西?什么是“逆转录病毒”?什么是“逆转录酶”?为什么人类基因组科学家说我们的基因组中有98,000个逆转录病毒,而为什么在艾滋病公司里,没有人关心这些,只关心第98,001个?杜斯伯格的俏皮话是,在第98,001个上,他们中了大奖。
你未来打算写些什么?
我有两本书正在撰写提案,与此无关。我其实现在还不想透露它们是关于什么的,但我正完全转向更简单的以人为本的故事。难道我们都不想写关于人的故事吗?我对科学没有癖好。我当然,当然不希望再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了。我觉得自己有点被它束缚住了。
你知道,我觉得这是梭罗式的,这是美国超验主义式的。它揭示了我们作为一种文化是怎样的。我们是否作为一种文化在自我定义?我们是关注基于证据的现实,还是被大众的恐惧所裹挟?我的意思是,这真是科幻小说素材。这就是科幻小说作家所写的内容。我认为我与那些更受欢迎、更受人喜爱、更容易接受的科普作家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我感到警觉。这更符合科幻小说作家的传统,他们说,天哪,我们的技术已经主宰和控制了我们。这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的意义。技术已经像活了一样来统治我们。但我们误解了我们所建造的技术。
你对你的职业生涯有任何遗憾吗?
[笑] 并没有。我抱怨很多,但这真是一段迷人而精彩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