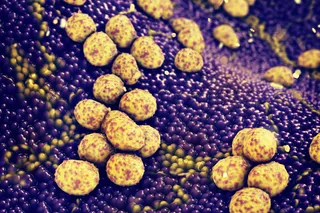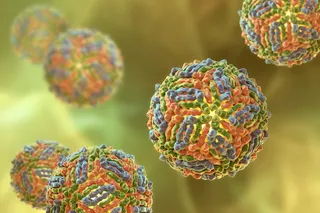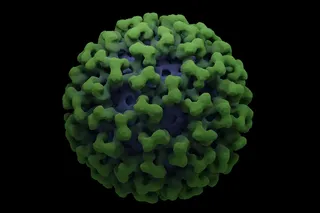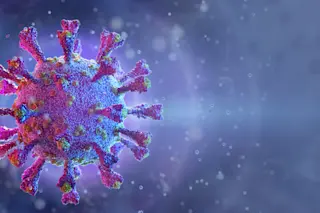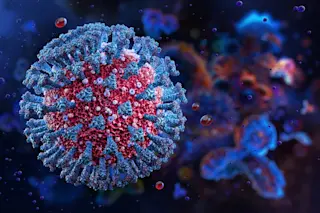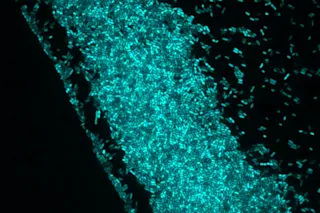性、血液和死亡几千年来一直是神话和迷信的素材。那么,像艾滋病这样一种鲜为人知且致命的疾病,成为二十世纪神话的素材,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艾滋病在14年前才被发现是一种在男同性恋中出现的奇怪疾病。一年之内,情况变得清楚,这种疾病不仅通过性传播,还通过血液传播。今天,艾滋病是美国年轻男性的主要死因。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部分地区,它以惊人的数字杀死男性和女性——例如,在乌干达西南部,它导致80%的年轻成年人死亡。与此同时,负责任的逆转录病毒HIV继续在南美洲和亚洲无情传播。如此规模的悲剧几乎必然会吸引那些将责任归咎于他人,同时暴露出其传播者执念的解释。
正如苏珊·桑塔格在她敏锐的散文《艾滋病及其隐喻》中所指出的,这种疾病已成为我们时代的祸患。艾滋病取代了癌症,成为不洁的疾病,一种与罪恶感、愤怒、无助和绝望相关的疾病。由于艾滋病的平均潜伏期约为九年,这种疾病的污名甚至影响到“未来的病人”:非常健康的HIV阳性者被拒绝购买人寿保险,并被当作死亡的预兆或我们中间的传染性麻风病人而遭到回避。然而,与一代人之前的癌症患者不同,艾滋病患者积极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寻求信息,并促进寻找治愈方法。虽然其中一些倡导团体与医生和科学家合作,但另一些则对“艾滋病机构”深表不信任,指责研究人员仅仅因为艾滋病是金钱和荣誉的来源而以此谋生。
所有这些都为神话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它们分为两大类:指责神话和否认神话。例如,有些人极度渴望为艾滋病找到替罪羊,找到一个对这场新的、不可阻挡的瘟疫负责的人。因此,科学在其起源中扮演了角色的观念具有吸引力,无论是通过设计还是通过一场灾难性的、随后被掩盖的错误。一种阴谋论认为,艾滋病病毒是人造的,是由另外两种逆转录病毒——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HTLV)和绵羊的梅迪-维斯那病毒——杂交而成的。从科学上讲,自从1985年艾滋病病毒基因序列测定以来,我们就知道这是无稽之谈。艾滋病病毒的任何基因序列都与HTLV或绵羊病毒不匹配。但是这种理论通过辩称艾滋病病毒的遗传变异性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可能很快就从其亲本病毒进化而来,从而得以幸存。
美国保守派最先假设艾滋病毒是一种“设计病毒”,是苏联用于细菌战的。(苏联与此同时将艾滋病定性为腐朽西方的疾病。)即使在今天,基因操纵的混合人-羊病毒理论仍在非洲持续存在,而罪魁祸首是美国。一些非裔美国人也认为艾滋病毒是被制造出来并针对他们释放的,作为一种种族灭绝形式。指责的矛头指向了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癌症研究与发展中心,该中心现在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部分。冷战期间,这里是美国陆军德特里克堡化学和生物防御设施的所在地。一种阴谋论认为,艾滋病毒是1960年代在那里作为生物武器制造的(尽管它几乎没有用,因为它需要数年才能致病)。据称,艾滋病毒在美国监狱的志愿者身上进行了测试,然后随着囚犯无意中通过注射毒品或肛交传播而变得无法控制。这种令人兴奋的说法具备了所有精彩科幻小说的要素,将军事科学家制造新病菌与微生物通过被禁止的——和秘密的——社会行为逃脱相结合。
然而,这个奇特的设想在几个令人尴尬的事实面前崩溃了。首先,如前所述,该病毒与据称制造它的两种病毒都不相似。相反,它类似于自然界中存在的猿猴病毒。其次,时间不对:现在可以将最早的人类感染追溯到至少20世纪50年代末,远在基因克隆和重组技术被构想出来之前。尽管如此,人造病毒理论的变体继续盛行。许多非洲人憎恶艾滋病毒“源于非洲”的说法——承受艾滋病疫情的重压已经够糟糕了,还要被指责为它的起源。
另一种流行的理论认为,该病毒是脊髓灰质炎疫苗测试的一个不幸的副作用。这个故事暗示的与其说是阴谋,不如说是搞砸了,带有熟悉的科学出现严重错误的母题。这个想法通过1992年《滚石》杂志一篇题为“艾滋病的起源:一个令人震惊的新理论试图回答是天灾还是人祸?”的文章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根据这篇文章,旧金山艾滋病活动家布莱恩·埃尔斯伍德发现了证据,表明艾滋病源于用于脊髓灰质炎疫苗研究的猴细胞。事实上,这个理论并非新鲜。我第一次读到它是在1987年,是英国动物权利倡导团体全国反活体解剖协会发布的一份小册子。
疫苗制剂真的会是原始污染源吗?脊髓灰质炎疫苗含有活的但经过刻意减毒的脊髓灰质炎病毒,这些病毒在灵长类动物细胞中培养——确切地说,是从猴子肾脏中提取的细胞。假设这些猴子携带了猿猴免疫缺陷病毒(SIV)的猿猴版本呢?该理论认为,这当然可能就是人类艾滋病的起源。当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进行测试时,SIV可能被喷入志愿者的口中,并可能在其人类宿主内部进化成为HIV。
然而,细节更为复杂。在野外,猿猴免疫缺陷病毒(SIV)仅限于非洲物种,而通常用于制造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猴子是亚洲猕猴。但根据《滚石》杂志的文章,存在一个例外:在急于开发脊髓灰质炎疫苗的过程中,目前在费城托马斯·杰斐逊大学的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Hilary Koprowski)使用了非洲绿猴的细胞来繁殖脊髓灰质炎病毒,用于在布隆迪-扎伊尔边境进行疫苗试验——靠近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艾滋病起源的地方。
即使那篇文章的事实是正确的——科普罗夫斯基对此坚决否认——这个理论也看起来极不可能。首先是事件的时间顺序。在中非的实地试验是在1957年和1958年进行的,然而第一个确诊的艾滋病病例是回顾性诊断的,患者是一名英国水手,他于1959年生病并死于艾滋病。现在,水手正是未来流行病的传播者类型。然而,没有这名水手航行到非洲的记录。如果他是在1957年或1958年接种疫苗的人那里感染病毒的,那么他从感染到发展成艾滋病的速度一定创下了纪录。
其次,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类艾滋病病毒。全球大流行是由HIV-1引起的,这种类型在中非发现。然而,这种病毒与据称污染科普罗夫斯基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猴病毒SIV并不那么密切相关。另一方面,SIV——特别是从另一种非洲猴子,即烟草猴(sooty mangabey)中分离出来的SIV——与第二种艾滋病病毒HIV-2密切相关。问题(对于阴谋论者而言)是,烟草猴从未用于脊髓灰质炎疫苗制备。此外,这种病毒直到最近才局限于西非人群,主要在几内亚比绍,距离科普罗夫斯基的疫苗试验现场约3000英里。总而言之,HIV的时间、地理和类型似乎都不符合,不足以指证科普罗夫斯基的疫苗。
话虽如此,我确实认为人类最初被动物病毒感染的可能性非常高。HIV-2与烟草猴的SIV如此接近,不可能是巧合,而且HIV-2感染最初在西非的焦点区域位于烟草猴生活并偶尔被捕杀食用的地方。事实上,伯明翰阿拉巴马大学医学中心的比阿特丽斯·哈恩(Beatrice Hahn)已经证明,西非的健康人类可能携带感染了毒性似乎较低的免疫缺陷病毒株,这些病毒株更接近猿猴株而非导致艾滋病的病毒株。至于HIV-1,一种与它非常相似的病毒已从中部非洲加蓬和喀麦隆的两只黑猩猩身上分离出来。这些猿猴是自然携带病毒还是从人类那里获得病毒,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如果黑猩猩确实是HIV-1相似病毒的天然宿主,那么它们很可能就是人类艾滋病的来源。
这种疾病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的现象称为人畜共患病。就艾滋病毒而言,极有可能最初是一种极其罕见的人畜共患病,后来发展成为人际传播的感染。目前尚不清楚艾滋病毒的SIV前体是多久以前引入人类的,尽管对病毒基因序列及其分化程度的研究表明,这种传播发生在过去50年内。
许多科学家宣称,面对对抗人类流行病的巨大问题,追溯艾滋病毒的起源是浪费时间。我不同意。我们可能会学到重要的教训,以预防未来的瘟疫。虽然脊髓灰质炎疫苗理论看似不可信,但我确实认为医源性传播——通过医疗实践无意中传播病毒——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知道艾滋病毒在西方国家通过输血传播,在东欧和非洲通过非无菌注射传播。因此,人类感染的医源性起源仍然是相当可信的。事实上,根据英国热带病专家查尔斯·吉尔克斯(Charles Gilks)的说法,早期有一些疟疾研究将黑猩猩、烟草猴和猕猴的血液接种到人类志愿者体内。给人们注射猿猴和猴子的血液——如果这些血液也被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的话——比脊髓灰质炎疫苗更有可能导致这些病毒适应并演变为HIV-1和HIV-2。
我们生活在诉讼盛行的时代,科普罗夫斯基对《滚石》杂志文章的最初反应是起诉诽谤,而不是对所谓的理论提出经过严密推理、科学论证的回应。(这样的答复最终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这份期刊比同人杂志更适合以名字命名的讨论。其中包括,科普罗夫斯基指出,他是在不含SIV的亚洲猕猴细胞中进行脊髓灰质炎疫苗工作的,就像其他人一样,而不是在非洲绿猴细胞中。)不幸的是,对于一些未经训练的人来说,这个理论后来被演变为目前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正在传播艾滋病的概念。在伊利诺伊州,一名女儿莫名其妙感染了HIV-1的父亲正在起诉提供她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制药公司。我们似乎已经回到了30年前的感恩社会,当时人们赞扬了乔纳斯·索尔克和阿尔伯特·萨宾,他们的疫苗使我们的孩子免于致残疾病和死亡。现在的危险是,公众被一个听起来很棒但不太可能的理论吓倒,可能会让他们的孩子错过挽救生命的免疫接种。
当面对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人们很容易否认它的存在。扎伊尔,或许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在1986年之前没有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任何艾滋病病例。在西方国家——艾滋病在异性恋中的传播落后于同性恋和吸毒者中看到的流行——毫无疑问,自欺欺人地认为艾滋病仅限于这些群体是令人欣慰的。但在所有关于艾滋病的迷信中,最荒谬的莫过于艾滋病毒不会导致艾滋病的说法。令人惊讶的是,这种信念得到了著名科学家的有力支持,特别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分子生物学家彼得·杜斯伯格(Peter Duesberg),以及最近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卡里·穆利斯(Kary Mullis)。对于一个艾滋病毒阳性但尚未发病的人来说,这个想法该有多么诱人啊!而当一两位专家宣称我们其他人像加达拉的猪一样,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冲去时,这是多么美妙的抨击科学的机会啊。这种否认理论在英国媒体中,特别是在曾经受人尊敬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中,奇特地占据了一席之地。
杜斯伯格的论点一直让我觉得过时;它们基于罗伯特·科赫一百多年前发表的科赫法则的狭隘观点。科赫是一位细菌学家,他规定(1)致病因子出现在每个病例中;(2)它不存在于其他疾病或健康人中;(3)纯化分离后,它能重新引起疾病——例如在实验动物中。科赫在发现“伤寒玛丽”等无症状疾病携带者后很快放弃了他的第二条法则。而他自己最伟大的科学发现——结核病细菌——他从未能满足第三条法则。另一方面,我们确实有SIV作为HIV的动物模型——纯化的、克隆的病毒形式能可靠地在猴子身上引起艾滋病。
杜斯伯格曾声称艾滋病毒不会引起艾滋病,因为血液中病毒滴度似乎不足,他忽略了病毒主要存在并繁殖于淋巴器官的事实。他还说,既然人们通过产生艾滋病毒抗体来应对感染,而这肯定具有保护作用,那么艾滋病毒就不是问题——他忘记了有些病毒感染(如登革热)中抗体并不能预防疾病,甚至可能使其恶化。此外,杜斯伯格还表示,所有其他致病微生物要么急性致病,要么根本不致病。这个惊人的错误忽略了肝炎、宫颈癌、带状疱疹以及其他可能需要一生时间才能显现的慢性或延迟性病毒疾病。
因为艾滋病毒与艾滋病如此契合,杜斯伯格将他的否认延伸为一个更普遍的假设——即艾滋病根本不是一种传染病。他说,艾滋病是由药物引起的,无论是娱乐性药物(如“poppers”)还是医疗药物(如AZT),这些药物的服用目的恰恰是为了阻断艾滋病毒。然而,即使在艾滋病毒被发现之前,艾滋病是由可传播的传染源引起的论据就已经令人信服。在1981年艾滋病被确定为一种新型免疫缺陷病后几个月内,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就表明,接受艾滋病捐献者血液的人自身患该病的风险很高。同时,也清楚地表明,病毒不仅可以在同性恋者之间通过性传播,还可以从双性恋者传播给女性,以及从血友病男性传播给他们的妻子。
艾滋病毒于1983年分离出来,1984年开发出抗体检测以发现感染后,数据开始大量涌入。流行病学家称之为横断面和纵向研究的两种主要证据证明艾滋病毒是艾滋病的罪魁祸首。横断面证据来自对不同风险程度人群的调查。艾滋病风险越高,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比例就越高。因此,艾滋病毒在较大的同性恋社区、接受了数千名捐献者血液凝血因子的血友病患者以及注射吸毒者中普遍存在。此外,当已知风险群体之外的人患上艾滋病时,他们绝大多数——99.5%——被发现是艾滋病毒阳性。从地理上看,无论在哪里,艾滋病毒都与艾滋病相关——在旧金山的男同性恋者中、爱丁堡的注射吸毒者中、东京的血友病患者中、内罗毕的性工作者中、布加勒斯特的孤儿中、曼谷的士兵中。在这些不同个体之间,不存在其他共同因素。
然而,有人争辩说,艾滋病毒在艾滋病高危人群中普遍存在仅仅是关联,而非因果关系的证明。正是在这里,纵向证据发挥了作用。例如,在1978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每年从旧金山数百名男同性恋者身上采集血液并储存,最初的目的是追踪乙型肝炎。对这些样本八年期的分析显示,艾滋病毒如何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感染最混乱的男性,并从他们传播给其他人。此外,只有那些感染艾滋病毒的个体后来才发展出艾滋病。其他“队列”研究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果。在艾滋病毒阳性母亲所生的婴儿中,大约只有四分之一感染了母亲的艾滋病毒,而且只有这些婴儿最终死于艾滋病。最令人信服的是,目前已知没有一个艾滋病毒阴性的血友病患者死于类似艾滋病的症状,然而那些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所付出的代价却是可怕的。
为了反驳这大量的证据,否认必须再生否认。去年,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不满足于否认艾滋病毒的致病作用,竟然宣称非洲没有艾滋病。诚然,艾滋病患者很容易受到其他病菌的严重感染。通常,这些感染(例如卡氏肺囊虫肺炎)是机会性的,因为它们几乎不会感染免疫系统健康的个体,而其他感染,如结核病,本身就能致病,但在艾滋病患者中往往更严重。然而,反对者声称,“艾滋病”只是结核病或卡波西肉瘤,如果某人恰好检测出艾滋病毒阳性,就会被重新命名。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这些疾病在艾滋病风险群体成员中出现,很可能导致它们被归类为艾滋病。例如,疾病控制中心以前纯粹根据症状和机会性感染来定义这种综合征。然后去年,该定义更新为包括艾滋病毒检测阳性——因此,反对者声称,将病毒与疾病联系起来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
同样,对细节的关注消除了对非洲艾滋病存在的疑虑。诚然,卡波西肉瘤在艾滋病出现之前就存在于非洲,但这种地方性疾病很少扩散到人们的下肢以外。然而,九年前,赞比亚的癌症专家安妮·贝利(Anne Bayley)清楚地意识到,在非洲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的卡波西肉瘤是一种全身性疾病,就像美国男同性恋者中的情况一样。结核病的情况也是如此。当然,结核病在没有艾滋病毒的情况下也会致人死亡,但在免疫功能低下者中,它更具破坏性。今年《柳叶刀》杂志上的一项纵向研究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在为期两年的时间里,乌干达的艾滋病毒阳性年轻男性和女性的死亡可能性是他们精心匹配的艾滋病毒阴性同龄人的60倍。这比吸烟与肺癌之间的因果关系更为强烈。
遗憾的是,往往是大众媒体而非枯燥、乏味的报告左右政治进程。受人尊敬的报纸所宣扬的否认神话,不仅可能被不幸的个人抓住不放,也可能被缺乏财政资源或决心去实施我们所拥有为数不多的艾滋病预防措施的政府所抓住。当所有逻辑都失效时,虚无主义者会指责信使。《星期日泰晤士报》自以为是地咆哮,称像我这样的艾滋病研究人员是为了发财,贪婪地吞噬政府的拨款,或者受制于制药业,而制药业本身则通过销售有毒药物获利。与此同时,攻击主流科学的同一批宣传者却对一两位在自己领域之外发声的异见科学家的言论宠爱有加。人们不禁想起已故的物理学家威廉·肖克利,他因发明晶体管而获得诺贝尔奖,却又滔滔不绝地宣讲白人相对于黑人的“智力优越性”。
然而,我们科学家也需要学习一点谦逊。我们可能确定艾滋病毒导致艾滋病,但我们对其作用机制或来源知之甚少,对其预防方法更是知之甚少。只要情况如此,神话就会继续从迷雾中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