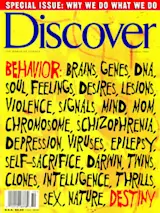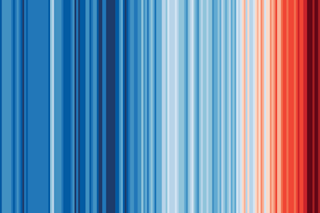二十五年前,斯蒂芬·埃姆伦(Stephen Emlen)着手调查关于非洲乌托邦的传闻。他听说肯尼亚的一些村庄里,多达300个个体生活在一起,尽管它们挤在聚集的巢穴里,却显得和谐融洽。即使食物变得稀缺,大家也会分享所有可得的食物。雌雄轮流照顾幼崽。伴侣们实行一夫一妻制,而且从表面上看都忠贞不渝。成年的子女不会离家组建自己的家庭,而是常常留下来帮助父母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有时他们还会帮助邻居。简而言之,利他主义战胜了自私自利。
这个和平王国的居民不是人类——它们是鸟类,一种叫做白额蜂虎的物种。但对康奈尔大学研究动物行为的生物学家埃姆伦来说,这个微不足道的事实丝毫没有减少这一现象的神秘感。进化本应在蜂虎个体间制造斗争,因为每个个体都试图最大化自己及其后代的生存机会——而不是一个纯粹无私的社会。当埃姆伦前往肯尼亚时,他以为自己即将发现自然法则的一个例外。但经过多年的研究,他意识到自己发现的其实是证明规律的那个例外:蜂虎实际上并非无私地帮助陌生者;相反,通过它们庞大、多代同堂的家庭中复杂的动态关系,它们帮助的是自己。蜂虎的父母、子女、叔伯姨婶和祖父母之间相互行为的种种方式,与你根据自然选择原则所做的预测精确吻合。在乌托邦的表象之下,隐藏着一场关于爱、欺骗、骚扰、离异和通奸的跌宕起伏的肥皂剧。
埃姆伦对他来之不易的发现感到失望吗?一点也不。这些发现引导他开始思考家庭。他开始自问,为什么有些物种会组成家庭,而另一些则尽快切断与子女的联系?为什么在不同类型的家庭结构中,个体的行为会有所不同,而这种行为是否可以预测?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埃姆伦开始了一项追求,旨在建立一个全面、数学上严谨的家庭模型。
他说,是时候将此阐述为一套统一的理论了——不仅是关于蜂虎家庭的理论,而是关于所有家庭,包括人类在内的理论。
埃姆伦走进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办公室时,与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擦身而过。这位电影明星的纸板人像带着极度厌恶的表情回瞪着他,仿佛迫不及待地想把他枪毙。十英尺外,印第安纳·琼斯潜伏在门口。这些纸板人是学生们摆放的——他们将埃姆伦视为某种科学界的侠客,但他试图淡化这个名声。的确,他曾在肯尼亚的草原上赤脚夜行(为了不打扰熟睡的雏鸟),尽管那里有致命的鼓腹咝蝰。而在巴拿马时,他也曾对类似短吻鳄的凯门鳄有些担心——尤其是在他兴奋地在独木舟里站起来,弄掉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或一副望远镜,然后不得不潜入水中从淤泥里捞回这些贵重物品时。但没有凯门鳄真正打扰过他;它们只对鸟和蛋感兴趣。
根据埃姆伦的经验,热带生物学家面临的最大威胁,与一个周末园丁可能遇到的威胁类似。例如,1991年,埃姆伦在巴拿马从河底淤泥中拔出30英尺长的杆子(这些杆子用于支撑捕鸟网)时伤了背。他有两个椎间盘破裂,并接受了两次手术;现在他几乎无法坐下。在办公室里,他大部分时间站着工作。地毯下的软橡胶垫缓冲了他不安的踱步;一个讲台让他可以站着阅读,他还把电话、电脑和显微镜抬高到胸部位置。埃姆乐说,在野外,他改装了独木舟的座位,使他能够以一种准舒适的方式工作。
尽管有这些困难,这个人看起来却异常开朗。他以同样的热情迎接每一个人——学生、同事、给他办公室重新装修的杂工。在校园里散步时——他似乎很乐意这样做以帮助缓解背部的压力——当讨论他的工作时,他很快变得兴奋,有时甚至是兴高采烈。如果他又丢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又有一些鸟被捕食者吃掉,或者甚至又失去了一两个乌托邦,这些都只会成为他研究的素材。
埃姆伦将他当前对家庭的迷恋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进化生物学家正热衷于为利他主义寻找科学解释。无私行为——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帮助他人——是如何说得通的?这似乎与达尔文的思想相矛盾。在那个时代,“自私的基因”这一概念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根据这一观点,身体本质上是基因为了帮助自己复制而发明的精巧机器。当一个动物拥有带来某种优势的基因时——比如捕食者获得了更好的视力,或者猎物获得了更好的伪装——这个个体就更有可能存活足够长的时间来交配并增殖其基因。就好像基因本身永远在寻找更好的策略来构建尽可能多的身体,同时将它们微小的生命密码注入其中。最适应的基因——即产生最多自身复制品的基因——在种群中占主导地位。
如果基因能以某种方式控制行为,那么行为就符合这一理论。例如,能够变得或多或少具有攻击性,或或多或少合作的动物,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比其他动物更有可能生存下来。然而,利他主义提出了一个挑战。自我牺牲似乎根本不能提供任何有益的回报,特别是如果这意味着牺牲繁殖的机会。告诉身体不要繁殖的基因应该无法存活,但这种行为显然存在。埃姆伦说,在鸟类中,最极端的明显利他主义案例被昵称为“协助者”。这些个体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放弃繁殖,转而帮助别人抚养孩子。这显而易见的代价是高昂的:你放弃了自己的繁殖;你增加了别人的繁殖。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悖论案例。
一位名叫威廉·汉密尔顿的理论家至少解开了这个谜题的一部分。从1964年开始,他发表了一系列数学研究,展示了当你帮助别人的孩子生存时,你的基因如何受益——前提是那些孩子恰好是你的亲属。当你抚养自己的孩子时,你的基因正在培育它们自身的复制品。如果你的基因能让你对那些孩子产生温柔的情感,这对你的基因的自私利益是有利的。但汉密尔顿意识到,其他亲戚也携带你至少一部分基因的复制品,他将适应性的概念扩展到包括更远亲属的生存。这就好像,通过帮助你的亲生子女的基因延续,你的基因获得50%的回报(你与他们共享50%的相同基因),或者通过帮助你姐妹的孩子、你的孙辈等获得25%的回报。关系越远,回报越低。
有了这样的算术,就变得很清楚了:在食物充足的时候,年轻的成年个体通过离家组建自己的家庭可能会获得最佳的基因回报。但在食物供应稀缺的时候,那些孩子存活的几率可能很低。那么,如果这些年轻的成年个体与其他成年个体合作,抚养一个近亲的后代,基因回报就会更高。根据汉密尔顿的逻辑,一个帮助抚养侄子侄女长大的未婚阿姨,有时可能比一个不顾一切大量繁殖的母亲在基因上更有适应性。
这是一个关于家庭行为的优雅模型——但白额蜂虎似乎公然违背了它。埃姆伦说:“我之所以研究蜂虎,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有复杂的、非家庭成员间的帮助行为。”人类会提供那种帮助,但人类学家通常用互惠来解释。他想,也许蜂虎也在以某种方式回报它们从家庭以外得到的帮助。今天,他对那个推测的评价很简单。“我错了,”他笑着说。
对埃姆伦来说,科学一直是一项家族事业。他的父亲,著名生物学家约翰·埃姆伦,在怀俄明州和密歇根州上半岛进行野外工作时都带着他。1973年,斯蒂芬第一次前往非洲研究蜂虎时,带上了他的妻子娜塔莉·德蒙;后来的几次旅行,他们还带上了孩子。(一个儿子,乔治,现在也是一位进化生物学家,将家族事业传承到了第三代。)这是一个由人类家庭观察鸟类家庭的团队。通常会有一两个学生休学一学期来陪伴他们,项目进行到一半时,其中一位叫彼得·雷格的学生成为了团队的永久成员。
他们花了八年时间深入研究蜂虎,一半时间在非洲观察鸟类,一半时间回到伊萨卡的家中,仔细研究笔记和数据。评估蜂虎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并不容易:这些鸟类以数百只的群体生活在一起,而且它们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无论雌雄:绿色的背,棕褐色的腹部,白色和红色的喉部条纹,以及优美弯曲的黑色喙。它们生活在土崖侧面挖的一两码深的洞里;埃姆伦一家在鸟儿从洞里出来时用雾网捕捉它们——布置那些网意味着要在夜间赤脚行走——并最终用翅膀标签标记了每一只鸟。娜塔莉为所有的“公寓”拍了照片,这样每只鸟都有一个地址,随着亲属关系逐渐明了,埃姆伦一家和他们的助手制作了闪卡,标明谁和谁有亲戚关系。他们一天大部分时间躲在隐蔽处,一次只关注一两个“公寓”,他们能看到鸟儿是带着食物进去还是空嘴进去,以及谁在门口迎接谁。娜塔莉发明了一种鸟类学潜望镜,由牙科镜、一盏灯和一个系在腰上的电池组制成;有了它,他们可以窥视那些深邃、恶臭的洞穴,看看谁在家。
他们连续两天不间断地观察有蛋的鸟巢,当雏鸟孵出后再次观察同样的鸟巢,然后在雏鸟即将离巢时再观察一次。埃姆伦说:“所以我们从三个不同的年龄阶段获得了严谨的信息,而且我们对许多不同的鸟巢都有同样的数据。”每天晚上,他们回到住处,吃一顿很晚的晚餐,谈论谁拜访了谁,关于求爱、出生和死亡,以及最终的非法闯入、欺凌、微妙的欺骗——所有这些都随着紧张和冲突变得更加明显而愈发激动人心。“这就像看一部肥皂剧,或者希区柯克的电影《后窗》,”娜塔莉说。然后斯蒂芬会花上几个小时在晚上转录他们在野外录制的磁带,并决定第二天要观察哪些“公寓”。
与此同时,他们绘制了家谱,并通过分子测试进行了确认。最终,埃姆伦说,“你就拥有了一个关于每个个体生存情况的完整数据库——一个关于谁与谁进行过社会互动、谁攻击过谁的数据库,一个关于对鸟巢贡献的数据库,一个关于谁分散并迁徙到其他群落的数据库,一个关于它们去哪里觅食以及作为觅食者有多成功的数据库。”回到康奈尔大学,娜塔莉和雷格帮助埃姆伦将所有这些数据库连接起来并处理数据。
他们研究蜂虎的时间越长,就越意识到,看似简单的利他主义背后是复杂的进化计算。例如,埃姆伦很早就发现,如果一个巢失败了(比如说,蛋被捕食者吃掉了),在巢里帮忙的儿子通常会搬到另一个“公寓”里,继续在那里帮忙。埃姆伦起初以为这只鸟在帮助没有亲缘关系的邻居,但几年后,随着他建立起家谱,他意识到蜂虎生活在庞大的、多代同堂的大家庭里,成员多达17个,占据许多“公寓”。每只鸟都花大量时间拜访父母、祖父母、叔伯姨婶、堂表兄弟姐妹、侄子侄女和外甥外甥女。
“它们都互相认识,互相打招呼,排斥非家庭成员。所以我忽略了的是,几乎每一个协助者都是转移到另一个家庭成员那里。如果你父母的巢失败了——砰——你就跳到你哥哥和嫂子那里去。或者如果一个繁殖者的巢失败了,它会过去帮助它的儿子和儿媳抚养孙辈。”
“一旦你有了大家庭,”埃姆伦继续说,“游戏就变得更加棘手了。”每只鸟都有更多选择去帮助谁——父亲、姑姑、祖母、表亲等等。由于埃姆伦知道汉密尔顿推导出的计算方法,他认为自己应该能够预测谁会帮助谁,以及在什么时候帮助。如果一个巢失败了,我应该能预测出得到帮助的第二备选。他认为他还能预测出在哪个点上成本超过了收益,协助者就不会再费心了。结果证明,他说,“每一个预测都惊人地正确。”你是帮忙还是袖手旁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亲缘关系的远近。提供帮助的可能性随着关系的疏远而急剧下降——砰,砰,砰,砰,砰。
埃姆伦开始察觉到一个由自私行为和合作行为构成的巨大网络。例如,雌性蜂虎有时会试图将自己的蛋产在无亲缘关系的鸟巢中,这样它们自己就无需花费抚养幼鸟所需的精力——这种现象被称为巢寄生。它们可以在几分钟内产下一枚蛋然后离开。“大多数这种寄生行为来自家庭外部。父母有应对策略:它们轮流看守自己的巢室,并且会驱赶除家庭成员以外的任何人。如果它们俩同时离开巢穴几分钟,回来时发现一枚新蛋,它们会把它扔出去。而且在它们产下自己的蛋一两天后,寄生者就来不及再偷偷放一个蛋了。一旦父母自己的蛋孵化,它们就不再孵化那枚迟来的外来蛋。所以寄生者必须在产卵期左右进入,”埃姆伦解释道——这并不容易。
“除非,”他发现,“这是内部作案,由一个能进入巢穴并得到父母信任的成员所为:换句话说,由一个没有配偶的协助者女儿所为。这个女儿破解了整个防御机制。她轮流防范其他任何人。她可以和母亲同步时间。所以她掌握了时机,她能进入巢穴——她可以骗过她的父母,而外部的寄生者则不能。”
唯一的障碍似乎是女儿没有配对。但通过仔细监视女儿们,埃姆伦发现了她们偷偷摸摸行为的全部维度。蜂虎会飞一两英里,从它们的巢穴到觅食地捕捉昆虫。在那里,埃姆伦说,“她们看到一个女儿的行为方式是我们从未在任何其他时候见过的。她就是离开,并闯入另一个家庭的领地。起初他们会把她赶走。但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她所在领地上的雄性停止了攻击,并与她交配。”
埃姆伦惊呆了。“哇,”他记得自己当时在想,“鸟类会做这种有策略的事情?”他说,那个例子,“让我们大开眼界,意识到一些非常微妙、有策略性的社会行为正在发生,也许我们过去认为鸟类是简单的小自动机,实在是太天真了。”
年长的鸟儿也不是天使。当年轻的鸟儿试图配对并开始组建自己的家庭时,它们的父母或其他年长的亲戚常常会骚扰它们——本质上是用好意让它们窒息。埃姆伦说,“当年轻的鸟儿配对,开始挖自己的巢穴时,会出现高强度的‘友好’干扰。一个年长的亲戚会守在入口——你可能觉得这很有帮助——但它会拒绝承认儿媳,导致儿媳无法进入。或者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亲戚可能会在年轻雄鸟试图喂食伴侣时频繁拜访。例如,一个父亲可能会闯入他儿子和儿媳相邻的领地,然后不停地跟他们打招呼。实际上他是在干扰儿子喂食伴侣的能力。”
根据埃姆伦的说法,在这种烦人的行为背后隐藏着一个精心计算的策略。通过骚扰年轻的亲戚,这些蜂虎增加了新巢失败的可能性,从而使年轻的鸟儿回到家中充当协助者。毕竟,如果它们自己不能产卵,那么传播基因的次优方式就是回家帮助爸爸妈妈。
埃姆伦说,直到他们深入了解这个系统,他们才会完全误解所有这些友好的姿态。“讽刺的是,你最能施加影响去骚扰的个体,正是你最亲近的下属亲戚。这也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表示,精确地说明你应该骚扰谁。所以我们看到兄弟偶尔会骚扰弟弟,祖父母偶尔会骚扰孙子,但大多数情况下是父亲骚扰儿子。所以在这个和谐、利他的画面之下,有很多事情在发生——各种各样的拉锯战。”
这是一个复杂的情景,要弄清楚在任何特定情况下什么是最佳的自私行为方式并不容易,即使对人类来说也是如此——埃姆伦需要大量数据和一台计算机来检验他对蜂虎策略的预测。那么,智力低下的鸟类蜂虎是如何如此精确地完成同样的计算的呢?显然,自然选择已经通过成千上万年的试错为它们完成了计算。埃姆伦说,“假设我们有几只蜂虎,它们都有评估不同亲属相对重要性的系统。现在假设其中一只比另一只更看重某个亲缘关系。如果它,比如说,更倾向于喂养孙子而不是堂兄弟,这将对抚养那些孩子的成功产生影响,并影响到未来基因复制的数量。如果帮助孙子的基因回报比帮助堂兄弟更好,那么识别孙子的遗传系统就会存活下来,而倾向于帮助堂兄弟的系统则会逐渐衰退。最终,一个鸟类物种的帮助行为会根据其特定家庭结构所允许的机会进行微调。”
埃姆伦很快指出,这种自然选择的结果并不是一套僵硬、决定性的反射行为。“我们不是在讨论利他主义基因的进化。基因调节的并非行为本身。”相反,基因——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许多基因组成的复合体——调节的是评估社会情境的能力。一个动物可能会发展出帮助它通过视觉、嗅觉、记忆、摇尾巴的暗号或以上所有方式来区分亲属的基因。而这个基因复合体可能包括一些能根据感知到的情况,为不同的情绪分泌不同激素的基因。所有这些都会增加以某种方式行事的几率,而不会使该行为完全由基因驱动。由于神经生物学的许多方面仍有待理解,埃姆伦将基因、激素和其他行为触发因素的具体链条视为一个黑箱。他更愿意称之为“决策规则”。“就好像你有一个装满各种行为的工具箱,”埃姆伦说,“而自然选择所微调的是从工具箱中选择正确行为并在正确情境下使用的能力。”
埃姆伦说,当他观察蜂虎的家庭传奇上演时,他越来越觉得这些家庭非常像人类。“所以,不管对错,我开始越来越多地思考蜂虎是那样构建的事实。我刚开始时并不知道。蜂虎是一夫一妻制,它们的忠诚率约为85%——比目前的人类高,但至少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处于同一水平。相似之处不胜枚举——存在离婚。早期繁殖尝试不成功的配对离婚的概率更高。”
考虑到数十万代以来,我们的祖先和蜂虎一样,很可能生活在庞大的大家庭中,这些相似之处就更加引人注目。在史前社会,人们从出生到死亡可能都被叔伯姨婶、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以及他们所有亲戚的孩子所包围。由于狩猎和采集的资源有限,亲戚之间在抚养孩子问题上的许多紧张关系(以及他们达成的解决方案)可能与在蜂虎中发现的情况如出一辙。
人类的大家庭甚至在农业革命给人们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变化中幸存了下来。直到过去几个世纪,它才开始瓦解。在许多国家,财富和流动性等技术和经济因素导致家庭规模缩小到核心家庭,即奥兹和哈里特式的家庭,然后继续缩小,单亲家庭变得更加普遍。(在人类进化的整个历程中,这两种家庭形式都是不正常的。)同样的力量正在创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继亲家庭,从进化意义上说,这与单亲家庭是一样的:更少有近亲血缘关系的人生活在一起。然而,当我们试图适应这些新型家庭时,我们仍然携带着我们在大家庭中数十万年进化而来的无意识决策规则。
继亲家庭——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物种——是埃姆伦最喜欢的例子之一。他说,“根据纯粹的自私基因逻辑,预测是我们在更换配偶后应该会看到行为上的真正变化。假设孩子跟母亲生活,一个继父进入了家庭。如果母亲和继父有了孩子,她原来的孩子应该不太愿意帮助抚养他们,因为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只共享25%的基因。这和侄子侄女的基因共享比例一样,所以搬出去帮助兄弟和嫂子应该是同样可能的选择。此外,年长的孩子应该更有可能完全离开家庭,因为留在家里的回报减少了。”
多年前,埃姆伦开始在蜂虎中测试这些预测,他观察当长期伴侣分开并选择新伴侣时会发生什么。孩子们帮助抚养由亲生父母和继父母所生雏鸟的概率下降了,而他们转而帮助大家庭中其他成员的概率增加了,他们完全离开家庭的概率也增加了。“第一次配对的孩子们会说,‘谢谢,不用了。我做得少多了,提供的食物也少多了。我要花更多时间去那边和我的其他家庭成员在一起。’”
同样的逻辑是否适用于整个动物界的家庭?埃姆伦现在正试图创建一个统一的家庭行为理论,一个能够解释在人类、其他哺乳动物、昆虫和鸟类中发现的家庭动态的理论。在这部鸿篇巨著中,埃姆伦不仅综合了他自己的工作,还综合了整整一代生物学家的劳动成果,他们研究了从鱼类到鸟类再到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等脊椎动物的家庭行为。在一个初步版本——1995年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家庭的进化理论》中,他仅用七页纸就总结了任何小说家能想象到的每一种家庭情况。一个包含15个预测的表格涵盖了可能的行为:帮助、杀婴、性冲突、扩散。在那篇论文中,他用通俗的英语解释了他的工作;现在他正在撰写下一个版本,这将是一套任何行为学家都可以通过输入数据来检验的公式。
家庭最初为何形成?理论中有解释。当资源有限,成功交配和抚养孩子的机会也有限时,家庭就会形成。家庭本质上也是不稳定的。在食物充足的时期,成熟的后代更可能自立门户,而不是留在家中作为协助者。然而,富裕的家庭比贫穷的家庭更稳定。例如,如果一个猫鼬家庭控制了一块特别好的狩猎领地,后代就更可能推迟繁殖,而是留在周围帮助长辈,因为继承家庭财富的前景看起来比试图在开辟和保卫新领地的同时抚养孩子要好得多。
在家庭之间,谁会帮助谁,以及在什么时候帮助?理论中有解释。在数百个被研究过的物种中,几乎每一个都严格遵循汉密尔顿的自私基因逻辑,无论这些生物是生活在像蜜蜂那样的奇异家庭中(姐妹啊姐妹,你们亿万个中哪个不是我的姐妹?),还是生活在我们更熟悉的家庭结构中,比如蜂虎。当一个替代配偶进入家庭时会发生什么?理论中有解释。对于子女来说,留在家里的回报降低了,同时新的性紧张关系出现了。因此,继亲家庭将比完整的亲生家庭更不稳定。
关于人类的数据很少,无法用来判断埃姆伦的预测是否也捕捉到了我们的家庭生活。但现有的统计数据是支持的。人类的继父母对前次婚姻的子女投入较少,而继亲家庭中的儿童更容易受到身体虐待。继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比亲生兄弟姐妹多,反之亦然:继子女之间根本不互动——他们互相忽视。继子女更早离家。而继父母犯下杀婴罪的比例比亲生父母高出60倍。
埃姆伦现在花很多时间辗转于各种会议,为他的家庭问题进化论观点辩护。他经常听到的一个反对意见是,鸟类,他最令人信服的数据来源,与人类差异太大,不能用作模型。“人们可以接受灵长类动物,”他说,“但是鸟类,天哪?就好像有一堵水泥墙,人们无法跨越。而我认为我的角色就是打破这堵墙。我们也许能从‘低等’动物身上学到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多。”显然,我们在生物学上与其它灵长类动物更接近。埃姆伦承认,它们是研究心智能力和认知的绝佳模型。但它们的家庭与我们的不同。例如,黑猩猩生活在群体中,雄性在抚养后代方面不起任何作用。
埃姆伦主张,绝大多数情况下,实行一夫一妻制并形成配偶关系的是鸟类。“雄性在育儿中扮演角色的也是鸟类。这完全不是灵长类动物的典型特征。生活在非常相似社会类型中的动物,会有着悠久的进化历史,面临同样类型的社会选择,因此会发展出非常相似的行为准则。”而埃姆伦所知的大家庭社会最好的例子就是蜂虎。
埃姆伦告诉他的听众,了解我们自身的基因如何预设了我们的行为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应对那些从我们现代新型家庭容器中爆发出来的旧式家庭行为。他警告说,如果这些行为确实是进化而来的,它们将难以改变。但它们是倾向,而非注定,这意味着它们可以被有意识地克服。
减少我们进化历史与现代家庭生活之间紧张关系的一种方法是操纵我们的社会环境。埃姆伦并不主张通过立法让我们回到更新世的家庭结构。但他沉思道,如果祖父母卖掉在亚利桑那州的公寓,搬回孙辈居住的城镇,帮忙抚养他们,给他们提供税收减免,或许会有所帮助。
另一种方法是认识到某些家庭情境如何可能演变成暴力和虐待的导火索。埃姆伦认为,最具爆炸性的情境之一可能是一个继父母进入一个有性成熟的儿子或女儿的家庭。他说:“继亲家庭中的性虐待比亲生家庭高得多,大约高出八倍。”鸟类中也发生同样的事情。当一个新的配偶进入时,儿子和他的母亲之间原本没有任何性兴趣。但儿子和他的继母之间却有极大的兴趣,而父亲则会攻击儿子,父亲会守护他的配偶。人类的数据显示出类似的趋势。例如,考虑一个新再婚的母亲,她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儿。埃姆伦说,即使出于最好的意图,那个女儿和母亲之间,相对于继父,也会有更高概率的潜在紧张和竞争——尽管你可能一直否认。了解这一点,预见到这一点,说这是自然的,理解这一切可能是如何产生的,我认为可以帮助化解这个导火索。
当然,你无法化解你没有预见到的事情。埃姆伦希望家庭和咨询师能够接受继亲家庭中冲突可能性更大的事实。他说,一个统计学上更大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每个家庭都会有这些问题,但人们或许可以被建议去预期问题并为之做准备。“我们是一个有能力有意识地克服我们认为不恰当的倾向的物种。而咨询比事后惊讶要好。我可以保持警惕,我可以更加警觉。我可以把大多数这些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
除了导火索之外,继父母还发现自己必须应对一种挥之不去的负罪感。埃姆伦说,“当我和社会科学家交谈并阅读文献时,有很多信息表明继亲家庭的父母感到内疚,因为他们对继子女就是无法产生与对自己亲生子女相同的情感。”这正是你所预期的。理解使我们对亲生子女和继子女感觉不同的进化压力,可以帮助人们应对经营一个继亲家庭的挑战。它能帮助你意识到你必须付出额外的努力,因为生物学不会帮助你。
最终,埃姆伦希望我们能够处理进化对我们行为的影响,就像医学处理遗传易感性一样。如果你有遗传性高血压的倾向,你就减少盐的摄入;如果你进入一个容易导致不幸结局的家庭情境,你就可以寻找应对策略。
埃姆伦说:“起初听起来很吓人,说如果你处于这种家庭状况,你就有麻烦了。但我认为这应该赋予人力量。知识应该赋予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