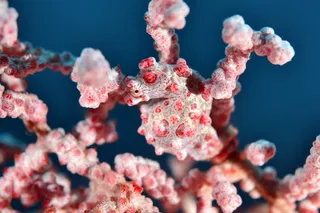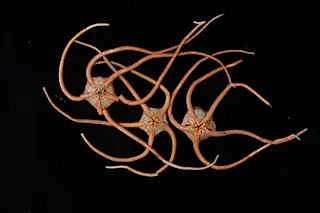与穆罕默德有关?来源:Ian Beatty 去年,一篇发表在《人类遗传学杂志》(AJHG) 上的论文报告称,埃塞俄比亚人似乎是西欧亚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的混合体。这个结果本身并不令人意外,原因有很多。首先,埃塞俄比亚人和非洲之角其他人口在地理上与西欧亚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等距。20 世纪的体质人类学家有时因此将他们归入“高加索人”种族分类。其次,非洲之角的语言与更熟悉的语言(如阿拉伯语)有“亚非语系”的亲缘关系。库希特语(例如索马里语)与更熟悉的语言(例如阿拉伯语)有深厚的渊源,但闪米特语(例如阿姆哈拉语)在历史距离上更近。第三,对这些人群进行的基因分析已经有很多,并且它们的混合性质从那些分析中显而易见(例如,线粒体 DNA 和 Y 染色体结果表明存在多种单倍群)。《AJHG》论文报告的发现是,埃塞俄比亚人的欧亚祖先在大约 3000 年前一次性混合了当地的、推测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土著居民,而他们今天在西亚最接近的现代亲戚是黎凡特人。稍微温和地说,这种测年是颇有争议的(利用基因标记在整个基因组长度上衰减的遗传相关性模式)。这不仅仅是地理分布上的变异。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这个混合的测年是正确的,那么现代埃塞俄比亚作为一个统一的生物文化实体,其出现时间比埃及文明晚了数千年。在哈特谢普苏特女王统治时期(约公元前 1500 年),曾派出一个贸易代表团前往蓬特兰(可能是索马里兰)。埃及人对蓬特人的描绘非常奇怪,因为他们看起来不像撒哈拉以南非洲人,而且蓬特兰女王似乎表现出更常见于科伊桑人的“臀部脂肪堆积”(steatopygia)。我曾推测,在古埃及文明时期,**东非在其人口构成方面正处于动荡之中**。在喀麦隆以东和以南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占主导地位的班图人,直到公元前 1000 年后才开始大规模扩张(大约 1500 年前到达南部非洲)。看来,科伊桑人的活动范围比今天更靠北和靠东是合理的。此外,当地可能还存在其他目前未被描述的人群(也许科伊桑人之所以显得突出,只是因为他们的分布区域使得遗留下来的人群至今仍得以研究)。例如,Tishkoff 实验室正在准备一篇关于在西欧亚人抵达非洲之角时,那里推测存在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群的论文(高地埃塞俄比亚人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成分似乎不像班图人)。我再次提到这一切,是因为 Dienekes 在下周的 SMBE 2013 会议上强调了 Joe Pickrell 的一篇摘要。
南部非洲的历史涉及了土著狩猎采集者与一系列进入该地区的人群之间的互动。这些互动对当前人群的遗传结构的影响尚不清楚。在这里,我们利用连锁不平衡的模式,表明南部非洲狩猎采集者和牧民的遗传历史中至少发生了两次混合事件:一次涉及与尼日尔-刚果语系非洲人群相关的群体,一次引入了与西欧亚(欧洲或中东)人群最接近的祖先。我们估计,在科伊桑人的基因中,至少有百分之几的血统来源于后者,该事件发生在平均 1200-1800 年前。我们发现,在东非各地都存在类似的西欧亚血统信号;**特别是,我们在肯尼亚、坦桑尼亚和索马里几个族群的遗传历史中也发现了两次混合事件的证据,其中最早一次涉及与南欧人群相关的群体,我们将其年代定在大约 2700 - 3300 年前。**因此,我们推测西欧亚血统是通过东非间接进入南部非洲的。这些结果表明,大规模基因组数据集如何能够为复杂的人群迁移模型提供信息,并强调了历史上未经充分描述的大规模“回归非洲”迁徙对基因组的影响。
这里没有具体说明科伊桑人,所以我冒昧地将一个布须曼人的图像放在文章的开头。
但更合理的是,他们可能是科伊,他们在遥远的过去从非班图人群(班图人抵达时他们已经拥有牛)那里获得了畜牧文化。
已有证据表明,坦桑尼亚神秘的桑达韦人(Sandawe)拥有古老的欧亚血统,因此这并不特别令人惊讶。桑达韦语与科伊桑语(有滴语)有亲缘关系,尽管作为一个整体的语系是否连贯仍存在争议(一些布须曼语本身可能并没有真正的紧密亲缘关系,除了滴语等明显的广泛相似之处)。直到我们获得更具地理覆盖范围的人群数据,桑达韦人起源的整个问题似乎都笼罩在迷雾之中。

Jan Jonker Afrikaner,奥尔兰人的领袖。至于欧亚血统如何可能进入科伊桑人,这是一个容易想象的过程,因为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更近期的欧洲和亚洲血统以历史上记载的方式进入了这些人群。其中一些是通过有组织的民族融合,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同化(就像阿兰人在被罗马人击败后被汪达尔人同化一样)。以奥尔兰人(Oorlam people)为例,他们现在是纳米比亚的纳马科伊部落的一部分。在 20 世纪初现代南非兴起和 18 世纪最初建立开普殖民地之间,大量混血个体,其祖先有北欧、亚洲(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以及本地(科伊桑人,后来是班图人)起源,这些个体源于各种接触(欧洲男性与奴隶的关系,非洲和亚洲奴隶之间的关系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开普科伊桑人。尽管语言上是阿非利卡语,宗教上是荷兰归正宗,但这个人群拥有多元化的种族血统,并被白人阿非利卡人视为二等公民。名气稍逊但仍为人熟知的是格里夸人,他们是边境居民,为了逃避殖民统治和因其“私生子”地位而遭受的种族压迫,在 19 世纪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实体,类似于他们白人阿非利卡人表亲在东方取得的成就。最后,你还有像奥尔兰人这样的群体,他们像格里夸人一样,通过他们的欧洲文化遗产和与纳米比亚更深入的丛林地区的联系,获得了对当地居民的某些优势,超出了荷兰共和国和英属南非最遥远的边界。但他们最终在被一个班图部落击败后,被科伊纳马人吞并。你在这里看到的是,随着离开普殖民地的距离不同,欧洲和本地文化传统之间的平衡变得愈发显著(一些格里夸男子据称消失在沙漠中并融入了他们“母亲的亲戚”,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布须曼人拥有欧洲和亚洲血统)。在古代非洲(以及其他地方),这种动态似乎完全有可能发生。在人口优势和环境条件有利的情况下,混合人群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与欧亚人的亲缘关系,而不是“回归本地”。这在非洲之角肯定是如此,那里的埃塞俄比亚政权干预了阿拉伯事务,并成为政治实体东方正教会社群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埃及的科普特人、亚美尼亚人和叙利亚东正教)。在很大程度上,埃塞俄比亚更像是西欧亚**世界**的边缘,而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部分。相反,你看到的是桑达韦人的情况,他们的模糊的库希特语亲缘关系早已被怀疑,但他们已经像他们的哈扎邻居一样变成了狩猎采集者,并采用了科伊桑人的语言和文化的广泛元素。最后,科伊人可能只从他们欧亚祖先那里保留了极具价值的文化知识,如畜牧业(和动物),而这些祖先本身很可能通过桑达韦人式的、已经混合的畜牧者而获得血统。*
总的来说,这些结果告诉我们,人类史前史是一个复杂而多层次的故事,通过基因来解析它将使我们得到比“答案”更多的“问题”。
十年前,“走出非洲”约 5 万年前,以及随后与非非洲人(例如欧洲人与亚洲人的分离,美洲原住民与亚洲人的分离)的分裂,是一个我们可以接受的稳健的程式化模型,让我们良心安宁。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加难以捉摸的世界,古老和全新世的混合现象充斥其间。世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例如印度)似乎是不到 1 万年前合并的非常不同的群体混合的产物。在过去的 3000 年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在文化上,甚至可能在基因上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现在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在过去的 5000 年里,东非一直受到“回归迁徙”的影响(尽管长期以来就有表明这一点的单系谱系)。一个简单的人类离开非洲伊甸园的故事已经不再可行,因为非洲并非所有人的伊甸园,而且现代非洲人本身也受到了欧亚迁徙事件以及广泛的内部民族迁徙的印记。最后,我认为,也许对基因研究最有价值的人可能是刚果东部的姆布蒂俾格米人。我怀疑他们受班图扩张和欧亚回归迁徙的影响最小。至少我希望如此。* 津巴布韦的伦巴人可能是过去 2000 年南部非洲发生的事情的一个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