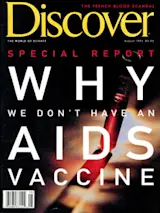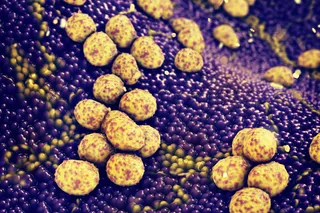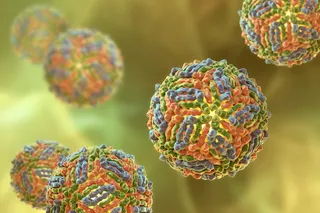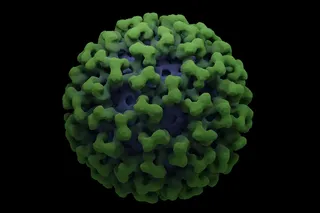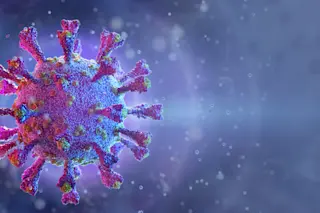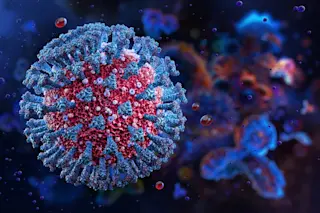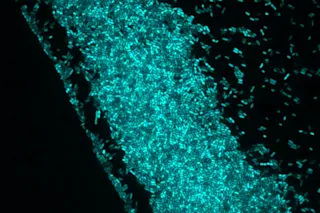这是一个恐怖故事,而且远未结束。它始于1985年的法国,一个常因其全民医疗保健体系和卓越医疗传统而令人羡慕的国家。在艾滋病疫情最耻辱的事件之一中,那里的医生和政府官员明知故犯地允许至少一千人接受受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或血液制品。其中三百人——主要是血友病患者,许多是儿童——已经死亡。其余的人,除非出现奇迹,否则都将死去。
当然,他们并不是输血相关艾滋病的唯一受害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疫情爆发时,在发现病毒病因并保护血液供应之前,许多血友病患者和接受输血的人也同样感染了受污染的血液。这种因无知而造成的悲剧几乎发生在世界各国。但在法国,最初的无知演变成了蓄意的纵容。使用受污染的血液库存成为经济权宜之计和政府批准的政策。
对该事件的冷酷处理被广泛认为是导致执政的社会主义党在去年三月选举中惨败的原因之一。两年前,当丑闻爆发时,乔治娜·迪福瓦(Georgina Dufoix),她于1985年作为社会事务部长负责卫生系统,在电视上声称自己无罪。她对目瞪口呆的观众说,我感到责任,但没有罪过。令许多人感到厌恶的是,去年夏天该案首次开庭审理时,她和她的下属、前卫生部长埃德蒙·埃尔韦(Edmond Hervé)都显眼地缺席了被告席。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较低级别的政府官员和米歇尔·加雷塔(Michel Garretta)——一名医生(现已停职)和国家输血中心(在法国被称为CNTS)前主任——承担了责任。他为自己辩护说:“我不感到羞耻”,这种不真诚的语气与迪福瓦的言论如出一辙。他说:“我当时做出的决定,如果是我自己和我的孩子,我还会再做一次。”加雷塔一直声称,即使在1985年初,对艾滋病的了解也不足以预见到血友病患者和接受输血者面临着致命的风险。他还坚称,当他知道真相时,并非只有他一人没有采取行动。他说,成千上万的人被告知了,但他们不一定能得出后果。
为什么不呢?答案是有的,但都无法提供多少慰藉。
血友病是一种几乎只影响男性的遗传病。受影响者会因缺乏凝血所需的蛋白质(最常见的是称为因子VIII的蛋白质)而发生无法控制的内出血危机。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危机通常通过医院输注新鲜全血或血浆(血液的液体部分,含有关键蛋白质)来治疗。但随着冷沉淀物的引入,这一切都改变了——冷沉淀物是冷冻血浆的沉淀物,其凝血蛋白含量是新鲜血液的五倍。很快就开发出一种方法,从数百名献血者的混合血液中浓缩凝血蛋白。这些浓缩物以易于储存的粉末形式提供,不仅让血友病患者能够自行治疗,而且还使他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工作和旅行。浓缩物的缺点是,单个感染血源性疾病的献血者(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最令人担忧的是肝炎)可能会污染由一批混合血液制成的所有浓缩物。
然而,法国的血友病患者对此风险感到相对安全。法国血友病协会名誉会长弗朗西斯·格雷夫解释说,在这个国家,血液是自愿捐献的。法国吸毒者无法以一瓶酒或一剂毒品的价格出售他们患病的血液(而在美国,直到1981年,出售血液在技术上都是可能的,并且支付血浆费用仍然是常态)。在法国人看来,献血是一种高尚的行为,献血者被尊为健康、有公民意识的人。不幸的是,巴黎的许多吸毒者献血是为了获得采集点分发的免费三明治和咖啡。
法国的血液系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结合体,它将真正的理想主义和慈善与准封建的权力结构联系在一起。最高层是社会事务部,该部通过社会保障局支付法国所有的医疗费用。接下来是卫生部,它授予160个输血中心(一个由独立、政府监管机构组成的网络)独家收集和分发血液的权利。其中七个是大型区域中心,负责根据卫生部规定的价格制造和分发凝血因子等血液制品。
最强大的区域封地(正如其名称所暗示的)是巴黎国家输血中心,一个位于城市宁静的十五区,闪闪发光的黑色钢铁和玻璃堡垒。其工厂已经满足了全国血浆和浓缩物约一半的需求,并试图做得更好。(1982年,卫生部授予CNTS进口血液制品的垄断权,并指示其减少进口并增强国家自给自足的能力。)CNTS及其研究顾问,其中包括巴黎大型公立医院的顶级血液学家,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运营体系。
CNTS 最初并不认为艾滋病是他们的问题。1981年,当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宣布首例病例时,大多数发生在同性恋男性身上;1982年1月,一名美国血友病患者首次被诊断出艾滋病,并未改变法国人认为这是一种同性恋疾病,主要传播途径是精液的看法。然而,到1983年3月,美国传来了更多令人不安的消息。在世界各地的血液学家都阅读的《输血》杂志上,美国血库联合起来宣布了八例经抗血友病因子治疗的血友病患者确诊艾滋病,并警告称,尚未知晓的致病因子可能存在于血液中。
据医生兼记者安妮-玛丽·卡斯特雷特(Anne-Marie Casteret)在5月4日的医生日报《Le Quotidien du médecin》上撰文,卫生部对这一消息的惊人反应是盲目乐观。该部显然并非唯一一个忽视警告的机构。CNTS的研究主任,血液学家让-皮埃尔·阿兰(Jean-Pierre Allain)坚持认为,“输血次数过多与艾滋病之间尚未证明存在关联”。然而,6月份,阿兰自己发表了一项对2300名法国血友病患者的研究,结果却表明并非如此:他研究的受试者中有六人表现出艾滋病的临床症状,例如淋巴结肿大和体重显著减轻。(当时还没有针对这种仍神秘的致病因子进行检测。当年2月,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吕克·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从一名患者体内分离出了一种逆转录病毒,但这种病毒是否导致艾滋病仍有待证实。)更重要的是,阿兰研究中表现出艾滋病症状的六名血友病患者中,有三人只接受过由法国献血者血液制成的凝血因子。这似乎表明法国的血液供应可能并非一尘不染。7月份,法国官方报纸《世界报》报道了第一例法国血友病患者感染艾滋病。
那年夏天,卫生部首席医疗顾问、卫生总局局长雅克·鲁(Jacques Roux)向各输血中心发了一封信,告知他们要警惕来自所有已知高危人群(现在包括静脉注射吸毒者)的献血。但盲目的漠不关心占据了主导。不久之后进行的一项部门调查显示,即使在巴黎——一个艾滋病病例比例过高的城市——大多数血库也不认为他们的献血者存在任何风险。“纯净法国血液”的神话如此普遍,以至于在1984年1月,监狱献血计划实际上得到了加强。(次年的研究表明,法国25%的受污染血液单位来自监狱。)
到1983年秋天,巴斯德研究所的蒙塔尼耶开发出一种原型测试,用于筛查血液中是否存在他认为是艾滋病病毒的抗体。该测试涉及将血滴与已知能引起抗体反应的病毒蛋白混合;颜色变化表明发生了抗体反应,并且血液可能受到感染。一项使用巴斯德测试对法国血友病患者进行的初步研究发现,133名法国血友病患者体内病毒抗体呈强阳性。这些结果由CNTS实验室主任安妮-玛丽·库鲁塞在1984年3月13日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公布,但未发表或详细说明具体数字。“纯净法国血液”的神话迅速破灭。然而,CNTS并未向卫生部透露这些发现。CNTS也未与血友病协会分享其信息,而该协会的办公室就在同一栋大楼里。
这种刻意的乐观情绪几乎是偶然被打破的。事件的发生,是在美国艾滋病研究员罗伯特·加洛于1984年4月抢了吕克·蒙塔尼耶的风头,宣布两人一直在研究的逆转录病毒——我们现在称之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确实是艾滋病病因之后不久。同年7月,一位精力充沛的法国免疫学家雅克·莱博维奇(Jacques Leibowitch)打电话给巴黎大型科钦医院血液科主任弗朗索瓦·皮农(François Pinon),请求帮助。莱博维奇的一位家人将在医院接受手术,他想派一些他自己挑选的无艾滋病献血者给皮农。皮农感到被冒犯了;他抗议说他的血液供应是完全安全的。但他对莱博维奇自己开发出筛查HIV抗体的方法印象深刻——蒙塔尼耶的巴斯德测试或任何其他测试都尚未上市。(莱博维奇的方法是将血样添加到含有HIV感染细胞的实验室培养皿中;培养皿中出现抗体反应意味着受试血液含有病毒抗体,因此献血者已被感染。)两人随后决定对皮农的库存进行研究。他们都没有意识到结果会多么可怕。
同年7月,在慕尼黑举行的国际输血学会大会上,消息传出,加热血液制品可以灭活艾滋病病毒。尽管当时还没有公布数据,但任何输血专家都不能忽视其影响。事实上,当时担任CNTS助理主任的加雷塔在慕尼黑期间就开始与奥地利公司Immuno谈判,以获得热处理技术的许可。但当时并未达成协议。
加雷塔于次年十月就任CNTS主任。他继承了一个严重依赖卫生部补贴来弥补运营亏损的机构;此外,它离实现法国血液制品自给自足的目标还很遥远。尽管9月份《柳叶刀》医学杂志发表报告称热处理可以杀死动物逆转录病毒,但加雷塔立即增加了VIII因子生产,而没有等待开发加热技术。
这是一个可怕的误判。12月12日,当莱博维奇完成对科钦血液库存的筛查时,事情变得清楚起来。皮农提供的2000份血样中有10份HIV抗体检测呈阳性。(为确保准确性,结果通过一项更费力的西方墨点法测试独立证实。)皮农惊恐地做了快速的心理计算。仅巴黎的公立医院每年就使用50万单位血液;根据每千单位血液有五单位感染(0.5%)的感染率,这意味着每年有2500例感染,或者说每天大约有七例新感染。他向科钦的医生发出了书面警告,要求将输血量降至最低,然后致电卫生部和CNTS。
对加雷塔来说,其含义是不可避免的:CNTS的每批因子VIII都是由多达5000份混合血液捐献制成的,因此任何批次免受污染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通过增加生产,加雷塔加速了疫情的蔓延。
皮农证实了CNTS至少一名高级官员,即研究主任阿兰已经怀疑的事情。阿兰曾有一段时间为他的一位年轻病人,一位他收留在家中的血友病少年,采购进口的加热浓缩物;他警告男孩销毁他未加热的CNTS库存,因为加热浓缩物更纯净。但那含糊不清的告诫并没有阻止男孩在那个12月的某个晚上,当他感到痛苦的出血危机来临时,注射了未加热的第八因子。阿兰的妻子,也是CNTS的雇员,得知发生的事情后勃然大怒。“你这个傻瓜!”她对男孩说。“你怎么能那样做?”他之前检测为血清阴性;后来变成了血清阳性。
到1985年2月,热处理血液的论证已告一段落。在《柳叶刀》杂志的两份报告中,蒙塔尼耶证实热处理能杀死艾滋病病毒,并且加热浓缩物能预防感染。未曾治疗过的(以前未接受过治疗的)法国血友病患者,如果只接受加热的第八因子,HIV检测呈阴性,而接受未加热第八因子治疗的患者则呈阳性。加雷塔匆忙与Immuno公司签订了加热技术协议。但他的工厂需要几个月才能改造完毕,在此期间只有进口加热的第八因子才能避免悲剧。但他仍然犹豫不决。如果CNTS要求卫生部承担进口费用,卫生部官员可能会想知道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发现受污染血液危机并保护血液供应。正如阿兰在一月份警告加雷塔(阿兰后来声称这是阻止灾难的最后尝试)的那样,加雷塔正在使CNTS在实现其基本任务之一方面蒙羞和失败。于是加雷塔开始掩盖他的行踪。
那年春天,一位CNTS官员说服皮农加入了一个抗艾滋病策略小组。皮农后来总结说,这是一种“并没有真正考虑我们的警报信号”的方式,而且“我的印象是这延迟了决策”。皮农和小组其他成员呼吁立即引入热处理产品,必要时从国外进口。但在五月份,当主持会议的CNTS官员将小组报告提交给卫生部时,文件中包含了一句话,建议“将召回或继续流通未加热产品的决定推迟到更高的政府部门”。
这并不是说卫生部一定会听从皮农及其同事的意见。1985年3月12日,卫生总局局长鲁克斯收到了一份来自助手关于皮农和莱博维奇最新发现的报告。两人在科钦和另一家拥有血库设施的医院找到了19名血清阳性献血者;也找到了从他们的血液中制备的第八因子受血者。所有人都呈血清阳性。报告总结道:“从巴黎献血者血浆中制备的所有血液制品现在可能都已受污染,”其中“所有”一词被划线强调。
鲁克斯无法忽视这份报告。然而,他现在说,他没有权力执行卫生政策。只有卫生部长埃尔韦才能下令销毁受污染的库存并加快献血者检测。(蒙塔尼耶的抗体检测当时仍未上市,但美国公司雅培(Abbott)生产的检测已于1985年3月2日获准在美国使用。)因此,鲁克斯将这份报告连同呼吁采取行动的信函转交给了埃尔韦的办公室。埃尔韦否认收到该报告。
直到1985年5月9日——在皮农最初的数据报告给CNTS之后的漫长五个月——加雷塔才亲自致信社会事务部,称清理血液供应是“绝对的紧急事项”。但CNTS的负责人也表示,必须在公共卫生需求和经济限制之间找到折衷方案。
据他计算,从那时起,每延迟三个月检测献血者和使用加热因子VIII,就意味着五到十名血友病患者以及他们的一些近亲的死亡。他的猜测是基于研究表明,迄今为止只有10%的HIV阳性患者发展为艾滋病。(CDC目前估计,迄今为止,29%的感染者已发展为艾滋病;其中约63%已死亡。)但他抱怨说,经济限制是巨大的:仅进口加热因子VIII就将花费4100万法郎(当时约合500万美元);销毁受污染的库存并弥补因加热过程造成的20%生产损失将花费数百万法郎。当然,卫生部和社会事务部必须承担这些费用。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些费用,加雷塔建议CNTS继续向其客户提供未加热的产品,直到7月中旬。他提议他们都接受在5月至7月期间再增加几例死亡,以维持预算。
5月10日,法国血友病协会的官员们信任地落入了他的圈套。加雷塔最近向他们承诺,CNTS很快将生产加热产品。然而,他以技术问题为由,没有给出具体日期。协会名誉会长格雷夫说,他还遗漏了一个细节:“他从未告诉我们未加热的第八因子库存已被污染。”因此,协会只要求卫生部在1985年10月1日之后禁止销售未加热的血液浓缩物——他们认为这足够加雷塔改造他的工厂。格雷夫说,他们从未想到加雷塔还需要处理掉他的库存。
与此同时,5月9日,悲剧链条上的另一个环节铸就了。那天,总理府以及卫生部、对外贸易部、社会事务部和财政部的代表会面,讨论巴斯德研究所的生产部门巴斯德诊断公司,该公司正在努力将蒙塔尼耶的测试商业化。其美国竞争对手雅培公司已于2月份申请法国政府批准其自己的测试。所有人都知道强制献血者检测早就应该进行了。但他们认为,如果雅培公司占领了法国输血中心的测试市场,那么巴斯德的产品在法国或其他地方就没有市场了。(就像法国人觉得在发现HIV方面被欺骗一样,他们现在觉得有被挤出抗体测试市场的危险。)这最终变成了在购买外国测试和拯救生命之间做出选择,或者为一家法国公司节省每年估计为9100万法郎(1100万美元)的市场。经济学再次获胜。决定雅培的许可文件将再搁置一段时间,直到巴斯德追赶上来。
5月29日,在CNTS大楼里,加雷塔与他的高级官员举行了另一次会议。他说,他们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接受我们所有的产品都被污染了?不幸的是,他补充说,召回受污染产品将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根据会议记录,一位名叫让-伊夫·穆勒的CNTS医生说:“重要的是避免污染尚未感染的血友病患者。”但没有人提出如果致命的浓缩物仍在市场上流通,如何避免污染。相反,他们决定等待“更高当局”——即卫生部——“禁止我们销售这些产品,并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后果”。实际上,他们是在要求上级阻止他们再次杀人。
6月1日,阿兰会见了输血咨询委员会,这是一个由政府官员和医生组成的卫生部监督机构。一位在场的地区中心主任回忆说,委员会“谨慎地”决定——这并未出现在在场31名医生签署的建议中——“仅仅几周,一个过渡期,你可以将未经加热的产品注射给已经血清阳性的人。”当然,他承认,“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加热产品给所有血友病患者。”这既有医疗上的考虑,也有伦理上的考虑:谁知道再次感染会对HIV阳性患者产生什么影响?(根据CDC研究人员的说法,再次感染存在被可能对艾滋病药物产生抗药性的新病毒株污染的风险,并可能加剧疾病。)
针对加雷塔的反抗零星发生。六月中旬,鲁克斯在卫生部长埃尔韦的内阁会议上摔门而去,并拒绝参加咨询委员会的会议,直到加热血液制品普遍可用。在官僚主义的愤怒中,他宣称他不再维护卫生部的政策。但这导致卫生部内部没有人反对加雷塔。
无论如何,上层没有人听。6月27日,图卢兹输血中心一位通常颇具影响力的主任让·杜科斯致信社会事务部长迪福瓦,恳求立即与她见面。一个月后,她的秘书回复说,之前的安排使得会面不可能。杜科斯也致信卫生部的埃尔韦,表示“无论如何都无法……凭良心继续向血友病患者施压,让他们接受有害产品”。埃尔韦从未回应。
与此同时,加雷塔开始计划如何出售他的受污染产品。6月26日,他致信CNTS的助手们:“非加热产品的分发仍是正常程序,只要有库存。”如果处方医生不要求安全产品,他们就得不到。他补充说,加热浓缩物“只被授权——而不是要求——用于HIV检测呈阴性的接受者”。
他的助手们强迫医生接受未加热的浓缩物。巴黎血液学家兼研究员蒂埃里·兰伯特回忆说:“你不能只说,‘这位患者血清阴性;给我们加热产品。’每次处方都必须讨论——而且讨论有时很困难。”为了防止珍贵的加热产品被共享,每位患者每月不得超过一个月的供应量。
最糟糕的是,一个可怕的悖论是,几乎没有医生能够证明他们的患者是血清阴性的——因为市场上仍然没有筛查测试。巴斯德测试的批准直到6月底才到来,当时总理洛朗·法比乌斯(Laurent Fabius)(接到卡斯特雷特和其他记者正在准备高度批评性报道的警报)宣布强制献血者检测。即便如此,这个承诺也显得空洞,因为直到7月23日,社会保障系统才同意报销检测费用。(雅培的测试在法国于第二天获得批准。)由于分发和测试人员培训方面的延误,到1985年底,法国的4000名血友病患者中,只有1670人——不到一半——接受了HIV检测。
同年7月23日,卫生部和社会事务部决定,只要有人购买,加雷塔就可以继续销售他未加热的库存。唯一的注意事项是,10月1日之后,通常报销处方费用的社会保障基金将不再支付未加热的第八因子。显然,咨询委员会在6月份同意的过渡期现在将延长到秋季。
9月6日,法国血友病协会才恍然大悟。他们的领导人在一次会议上说,同意加雷塔的计划,并非意味着允许他将笨重的产品卸载给不知情的血友病患者。他们呼吁禁止未加热的浓缩物,并提醒其成员和媒体。加雷塔随后抱怨说,他们破坏了他“现实而负责任的战略”。他被迫进口了比计划更多的加热第八因子,并且他囤积了大量未使用的法国产品。也就是那些被污染的产品。
事实上,他已经卖了很多。根据CNTS内部记录,1985年7月至10月期间,共售出160万单位的未加热第八因子。最大的销售额发生在暑假前后——面向为旅行储备或回家后补充物资的血友病患者和年幼血友病患者的父母。血友病协会的格雷夫就是其中之一。7月12日,他为他患血友病的少年儿子购买了一些未加热的第八因子。格雷夫不知道他购买的那批是否被污染,如果被污染,是否加速了他儿子死于艾滋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格雷夫绝不会明知故犯地给孩子注射可能伤害他的物质。
从1984年12月CNTS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到1985年10月其最后一批受污染产品售出,究竟有多少人被判死刑?加雷塔及其助手一直坚称,法国90%以上的血清阳性血友病患者是在1985年之前感染的,当时污染可以说成为了官方政策。然而,一项在巴黎两家医院进行的回顾性研究发现,有60名血友病患者的血清转化年份精确可知,这要归功于不到一年前抽取的参考血清。这60人中有17人——28%——在1985年发生了血清转化。
血友病患者并非唯一的受害者。在去年底的一次调查中,CNTS的库鲁塞作证说,一个简单的计算显示,从1985年4月到8月,也就是艾滋病检测普遍可用之前的几个月,每月约有200人因感染献血者的血液而受到污染。换句话说,大约有1000名受害者,还不包括受害者的配偶、恋人或新生儿。
法国司法系统通常被视为国家的一个分支,而非独立的权力机构。因此,当血友病患者于1988年首次提起诉讼时,负责该案件的调查法官以极其谨慎的速度推进,这在法国人看来不足为奇。该案将花费四年时间才开庭审理。
与此同时,在媒体中,只有卡斯特雷特认真对待了这个故事。她开始拜访前CNTS和卫生部官员,并积累了大量的官方文件——在一个从未有过信息自由的国家,这是一项壮举。然而,她回忆说,最困难的部分是“相信她所看到的一切”。她说:“我是一名医生,我无法想象一名医生会遵循经济逻辑而不是治疗逻辑。”她直到核实了自己的工作,确信无疑后才全面发表。1991年4月,她的文章开始出现在新闻周刊《星期四事件》上。
她的读者之一是埃德蒙-吕克·亨利(Edmond-Luc Henry),他是一名会计师,也是一名血友病患者,于1984年在CNTS医生治疗期间感染了HIV。亨利被卡斯特雷特的揭露激怒,对不明身份的人提出了“投毒”指控——这是一项重罪,根据法国刑法,可判处终身监禁。显然是为了阻止重罪审判,国家调查法官突然对加雷塔、阿兰、鲁克斯以及鲁克斯在卫生部的同事罗伯特·内特(Robert Netter)提出了轻罪指控。1992年3月,他们被指控“产品基本质量欺诈”,依据一项亨利律师萨宾·波加姆(Sabine Paugam)尖酸刻薄地描述为“旨在惩罚变质芥末销售商”的法律。(对鲁克斯和内特的指控被广泛认为是保护埃尔韦本人的策略。)
这四人去年夏天首次在巴黎司法宫由一个法官小组审判。1992年10月,加雷塔被判处四年监禁并处以巨额罚款。(他在宣判前潜逃到波士顿,担任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顾问,因此失去了获得宽恕的任何希望。)鲁克斯获得缓刑,内特被无罪释放,而被判处两年监禁的阿兰提出上诉并获准重审。此举非同寻常,也许是为了平息公众舆论认为判决过轻的不满,国家检察官要求对这四人全部重审。
今年五月在巴黎上诉法院开始的第二次审判旨在决定是否维持、减轻或加重原判。这仍然是一场由国家检察官进行的刑事审判。但在法国,受害者及其律师可以向法院陈述他们的案情。在上诉期间,波加姆和其他代表血友病患者的律师力促将案件移交重罪法院,以更严厉的“投毒”罪名审理。如果如此,可以追加被告。律师们还要求在高等法院对埃尔韦、迪福瓦和前总理法比乌斯提起“投毒”指控,高等法院是法国唯一可以审理前部长任职期间所犯罪行的法庭。
在等待这次最新审判结果时,亨利以一个垂死之人坚定不移的简单性总结了所涉及的法律和伦理问题:“如果你坐在办公室里数着产品盒子,你可以谈论营销,”他说。“但如果你正在治疗人类,就不能这样。如果你是医生,你不能给人们可能伤害他们的产品。”
事实上,加雷塔不只是帮助毁掉了数百条生命;他还严重损害了医患关系。皮农最近说:“我最谴责加雷塔的是,他制造了对血液系统的不信任,而血液系统完全建立在信任之上。”加雷塔在五月法庭听证会上的表现未能恢复法国公众的信心。日复一日,这位憔悴的前CNTS负责人泪流满面地重复着同样的说法:“我不可能独自做出决定。没有人说过我们应该采取不同的做法。”他说,他是一个替罪羊,为共同的缺乏远见和勇气而承担责任。
医生就应该比我们其他人更优秀吗?为什么要责怪阿兰留在了CNTS并执行加雷塔的政策呢?毕竟,正如他在审判期间接受采访时所说,“我有四个孩子,我需要谋生。”在他身后是挤满了痛苦父母的法庭,他们曾经也有自己的孩子。他们的儿子现在都死了,因为像加雷塔和阿兰这样的人——毫无疑问还有许多其他永远不会被公开点名的人——背叛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