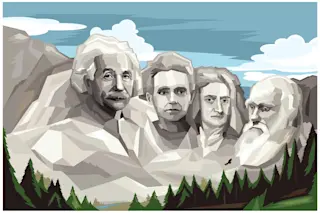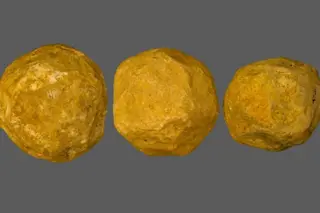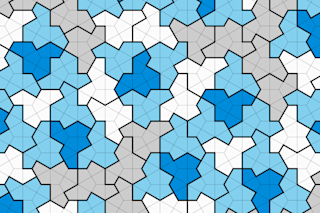杰夫·托拉克森很可能相信他注定要在此时此地。我们正乘船在大西洋上,这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倾盆大雨遮蔽了原本雄伟的亚速尔群岛火山背景,波涛汹涌的海水导致船只颠簸。恶劣的海况对托拉克森影响不大,几乎没有给他的北欧面容带来一丝血色。这对他来说是第二天性;他从小在船边长大。每个人都会同意,他过去的经历为今天的旅行做好了准备。但托拉克森和他的同事们正在调查一种更奇怪的可能性:可能不仅是他的过去,还有他的未来,将他带到今天。
托拉克森的小组正在研究时间可能倒流的观念,允许未来影响过去。推而广之,宇宙可能有一个命运,它回溯并与过去合谋,使现在显现。在宇宙尺度上,这个想法可以帮助解释生命是如何在宇宙中克服重重困难而出现的。在个人尺度上,它可能会让我们质疑命运是否在推动我们前进,以及我们是否拥有自由意志。
这次船程是作为由基础问题研究所赞助的一次会议的一部分而组织的,旨在强调物理学中最具争议的一些领域。托拉克森的想法无疑符合这一标准。然而,尽管听起来很疯狂,但这种逆因果关系的观念正在获得认可。一系列量子实验证实了它的预测——令人困惑地表明,未来进行的测量可以影响在这些测量发生之前就已经出现的结果。
当波涛汹涌时,很难决定什么更令人不安:船只持续不断的摇晃,还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时间之箭——定义我们生活基本叙事的流动——可能不仅是幻觉,而且是谎言。
托拉克森目前在加利福尼亚州橙县的查普曼大学任教,他早期就对量子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量子力学是支配亚原子世界粒子运动的理论。他跳过了高中最后一年,转而旁听了魅力非凡的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费曼在加州理工学院帕萨迪纳的物理讲座,并了解了至今仍让物理学家着迷和困扰的悖论。
这些怪异现象中最主要的是著名的不确定性原理,它指出你永远不可能同时了解粒子所有属性。例如,不可能同时测量粒子在哪里以及它移动的速度有多快;你确定一个方面越精确,测量另一个方面就越不精确。在量子尺度上,粒子还具有奇怪的分裂人格,允许它们同时存在于多个位置——直到你观察并检查它们。这种粒子可以拥有多种矛盾属性的脆弱状态称为叠加。根据量子力学的标准观点,测量粒子属性是一个剧烈的过程,会立即将粒子从叠加中分离出来,使其坍缩成单一身份。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发生,是量子力学的核心奥秘之一。
“量子力学中关于测量的教科书观点受生物学启发,”托拉克森在船上告诉我。“这类似于你不能在不影响动物系统的情况下观察它们的想法。”雨停了,船长收到无线电通知,几分钟外发现了一些海豚;很快我们就朝它们驶去。我们试图监视这些动物的行为,就好比托拉克森所说的“强测量”——量子力学中的标准类型——在动物学上的对应物,因为它们绝不是不引人注目的。船很吵;它在加速驶向目的地时激起水花。当海豚最终出现时,它们游到船边,在空中划出弧线,为观众表演。根据传统量子力学,同样不可能在不与粒子相互作用并破坏你观察之前存在的脆弱量子行为的情况下观察量子系统。
大多数物理学家都接受这些奇特的限制,将其视为理论的固有部分。托拉克森并没有那么容易满足。“我被迷住了,我知道我这辈子不可能再做其他任何事情了,”他回忆道。在费曼的建议下,这位少年搬到波士顿,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物理。但他想念大海。“在我生命中第一次,我失去了海浪的背景声,”他说。“那实际上是创伤性的。”
考虑到从事深奥的物理学工作可能不是养家糊口的最佳方式,托拉克森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同时,在一家计算初创公司工作。但如果这位年轻人不确定自己的使命,当一位名叫亚基尔·阿哈罗诺夫的物理学家访问邻近的波士顿大学时,命运很快就推了他一把。阿哈罗诺夫现在和托拉克森一起在查普曼大学任教,他以共同发现一种奇异的量子力学效应而闻名,在这种效应中,粒子会受到电磁场的影响,即使在这些场本不应到达的区域也是如此。但托拉克森最感兴趣的是阿哈罗诺夫研究的另一个领域:一种时间扭曲的量子力学解释。
“阿哈罗诺夫是第一批认真对待这样一个观点的人:如果你想了解在任何时间点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过去是相关的。未来也是如此,”托拉克森说。特别是,阿哈罗诺夫重新分析了构成量子力学支柱的非确定性。在量子力学出现之前,物理学家们相信物理定律可以用来确定宇宙及其内部每个物体的未来。按照这种想法,如果我们知道地球上每个粒子的属性,我们原则上可以计算出任何人的命运;我们甚至可以计算出他或她头脑中的所有想法。
当实验开始揭示量子力学的非确定性效应时——例如,原子放射性衰变——这种信念崩溃了。托拉克森说,问题是这样的:取两个放射性原子,它们如此相同,“即使上帝也看不出它们之间的区别。”然后等待。第一个原子可能在一分钟后衰变,但第二个可能在另一个小时后才衰变。这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实验;这在实验室中确实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解释这两个原子的不同行为,无法通过查看它们的历史来预测它们何时衰变,而且——似乎——没有明确的原因产生这些效应。这种非确定性,以及不确定性原理固有的模糊性,激怒了爱因斯坦,他怒斥上帝不与宇宙玩骰子。
这也困扰着阿哈罗诺夫。“我问,上帝通过掷骰子能得到什么?”他说。阿哈罗诺夫承认粒子的过去不足以完全预测它的命运,但他想知道,如果信息不在它的过去,那它会在哪里呢?毕竟,总有什么必须调节粒子的行为。他的回答——既令人振奋又疯狂——是我们无法感知控制粒子当前行为的信息,因为它尚不存在。
“自然正试图告诉我们,两个看似相同但命运不同的粒子之间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只能在未来找到,”他说。他认为,如果我们愿意摆脱时间只朝一个方向移动的先入为主的观念,那么完全有可能建立一个确定性的量子力学理论。
1964年,阿哈罗诺夫和他的同事彼得·伯格曼和乔尔·莱博维茨(当时都在纽约叶希瓦大学)提出了一个新的框架,称为时间对称量子力学。它可以产生与每个人都熟悉和喜爱的标准形式的量子力学相同的所有结果,并额外提供了解释未来信息如何填补当下非确定性空白的益处。但尽管阿哈罗诺夫的许多同事承认这个想法建立在优雅的数学基础上,其哲学含义却难以接受。“每次我提出一个关于时间的新想法时,人们都认为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他说。
也许是由于这个想法引起的认知失调,时间对称量子力学并未流行起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只是少数哲学家讨论的好奇心而已,”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桑杜·波佩斯库说,他与阿哈罗诺夫合作研究时间对称方法。显然,阿哈罗诺夫需要具体的实验来证明未来发生的行为会在这里和现在产生影响。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托拉克森与阿哈罗诺夫合作设计了这种颠倒的实验,其中结果由实验完成后发生的事件决定。通常,实验方案包括三个步骤:对一组粒子进行“预选”测量;一个中间测量;以及最后一个“后选”步骤,研究人员在其中选择了一部分粒子进行第三个相关的测量。为了找到逆因果关系——信息从未来流向过去——的证据,实验必须证明在中间步骤测量的效应与稍后对粒子子集进行的操作相关联。
托拉克森和阿哈罗诺夫提出分析量子特性“自旋”的变化,这大致类似于球的旋转,但有一些重要的区别。在量子世界中,粒子只能以两种方式旋转,向上或向下,每个方向都被赋予一个固定值(例如,1或-1)。首先,物理学家将在下午2点测量一组粒子的自旋,然后在下午2:30再次测量。然后在另一天,他们将重复这两次测试,但也会在下午3点对一部分粒子进行第三次测量。如果逆因果关系的预测是正确的,那么对于这最后一部分粒子,下午2:30(中间时间)进行的自旋测量将显著放大。换句话说,下午2点进行的自旋测量和下午3点进行的自旋测量加在一起,似乎会在下午2:30的中间测量中导致自旋强度出乎意料的增加。这些预测似乎荒谬,就像声称你可以在下午2点和下午3点测量大西洋沿岸海豚的位置,但如果你在下午2:30检查它的位置,你会发现它在地中海中部一样荒谬。
而且这种放大不会局限于自旋;其他量子性质也会急剧增加到离奇的高水平。其想法是,未来进行的测量所产生的涟漪可以回溯到现在,并与过去的效应相结合,就像波浪在船下方汇合并达到高峰,使其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摇晃一样。根据阿哈罗诺夫的数学,为最后一次测量选择的子样本越小,中间时间的效应就应该越显著。在传统物理学中,很难解释如此巨大的放大。
多年来,这个预测更多是哲学层面的而非物理层面的,因为它似乎无法进行所建议的实验。该团队提出的所有测试都依赖于在某个中间时间点能够对量子系统进行测量;但物理学书籍说,这样做会在最终的后选步骤执行之前破坏系统的量子特性。任何测量系统的尝试都会使其脆弱的量子态坍缩,就像乘船追逐海豚会影响它们行为一样。使用这种侵入性或强测量在中间时间检查你的系统,你还不如直接用锤子砸你的设备。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阿哈罗诺夫找到了一个出路:他可以使用所谓的弱测量来研究系统。(弱测量涉及与传统测量相同的设备和技术,但控制观察者设备功率的“旋钮”被调低,以免干扰正在进行的量子特性。)在量子物理学中,测量越弱,其精确度就越低。对一个粒子进行一次弱测量,你的结果几乎毫无用处。你可能认为你看到了所需的放大,但你同样容易将其归因于噪声或设备误差。
托拉克森意识到,获得可靠结果的方法是持之以恒,而不是强度。到2002年,意识到弱测量潜力的物理学家们正在重复他们的实验数千次,希望能建立一个数据银行,通过放大效应有力地展示逆因果关系的证据。
就在去年,物理学家约翰·豪厄尔和他的罗切斯特大学团队报告了成功。在罗切斯特的装置中,激光被测量,然后通过分束器分流。一部分光束直接穿过装置,另一部分则从一个由于连接的电机而轻微移动的镜子上反射回来。研究小组使用弱测量来检测反射激光的偏转,从而确定电动镜子移动了多少。
这是直截了当的部分。寻找逆因果关系需要观察最终测量的影响并添加时间扭曲。在罗切斯特实验中,激光束离开镜子后,它们通过两个门中的一个,在那里它们可以再次被测量——或者不被测量。如果实验者选择不进行最终测量,那么在中间阶段测量的偏转角度微小得无聊。但是如果他们执行了最终的后选步骤,结果会大不相同。当物理学家选择记录从其中一个门出来的激光时,那么单独通过该路径的光束,在中间测量步骤中偏转角度被放大了100多倍。不知何故,后来的决定似乎影响了较早进行的弱中间测量的结果。
这一惊人的结果证实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物理学家奥努尔·霍斯滕和保罗·克维亚特一年前报告的类似发现。他们在使用弱测量检测偏振光束在空气和玻璃之间移动时的位移时,实现了高达10000倍的激光放大。
对于四十年来一直在推动逆因果关系理念的阿哈罗诺夫来说,实验验证似乎是开香槟庆祝的时候,但这并非他的风格。“我并不感到惊讶;这正是我所预料的,”他说。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坦佩分校的宇宙学家保罗·戴维斯赞赏阿哈罗诺夫团队一直致力于通过实验验证其主张。“这不是空洞的哲学——这些是真实的实验,”他说。戴维斯现在已经与该团队合作,调查该框架对宇宙起源的影响(参见下文“宇宙有宿命吗?”)。
牛津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弗拉特科·韦德拉尔同意,这些实验证实了弱测量的存在和效力。但是,尽管该团队框架的数学为实验结果提供了有效的解释,韦德拉尔认为这些结果本身不足以说服大多数物理学家接受其背后的完整时间扭曲逻辑。
然而,对托拉克森来说,这些结果令人惊叹,也有点可怕。“这在哲学上令人不安,”他承认。“所有这些实验都改变了我与时间的关系,我体验自己的方式。”这些结果让他与未来已定的想法作斗争。如果宇宙有一个已写好的宿命,我们的行为真的有自由选择吗?或者我们所有的选择是否都已预先决定以适应宇宙的剧本,只给我们自由意志的幻觉?
托拉克森思索着这个哲学难题。他是否注定要成为一名物理学家?如果是这样,他的科学成就是否因为他除了在这个职业上取得成功之外别无选择而变得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如果我从21世纪穿越回托拉克森13岁时在密歇根湖畔阅读费曼著作的时候,告诉他未来我在亚速尔群岛遇到了他,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他的少年时期的自己——只是为了报复我——会不会选择离家出走加入马戏团或者成为一名水手呢?
自由意志问题是托拉克森一直在与波佩斯库用数学方法解决的问题。这个框架实际上并没有暗示人们可以穿越到过去,但它确实允许对是否可以改写历史进行具体测试。罗切斯特的实验似乎表明,未来执行的动作——在最终的后选步骤中——会时间倒流,影响并放大早期中间步骤中测量的结果。这是否意味着当中间步骤执行时,未来已经注定,实验者别无选择,只能执行后来的后选测量?似乎不是。即使在最终步骤被放弃的情况下,托拉克森发现,中间的弱测量仍然被放大,尽管现在没有任何未来的原因可以解释其大小。
我直截了当地问托拉克森:这个发现似乎在嘲弄我们迄今为止讨论的一切。
托拉克森笑了;这显然是他经历过多次的争论。他解释说,那次单一实验的结果可能相同,但请记住,弱测量的力量在于它们的重复性。任何单一测量都不能单独拿来传达关于现实状态的任何意义。它们的固有误差太大了。“你的指针仍然会读到一个放大的结果,但现在你不能将其解释为除了噪声或设备故障之外的任何原因造成的,”他说。
换句话说,你只有在进行了数百万次重复实验并将结果汇总以产生有意义的模式之后,才能看到未来对过去的影响。如果你专注于其中任何一个并试图作弊,你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结果——一个没有原因的放大——但它的意义消失了。你只能将其归因于设备中的随机错误。你收回了你的自由意志,因为如果你真的试图违抗未来,你会发现它永远无法强迫你违背你的意愿进行后选实验。托拉克森说,数学支持他的这一解释:那些没有进行所需后选的单一中间弱测量中的误差范围总是恰好足以将这个奇怪的结果视为一个错误。
托拉克森用他最喜欢的一句古犹太圣贤拉比·阿基瓦的话总结了这个令人困惑的论点:“一切都已被预见;但自由选择已被赋予。”或者用托拉克森的话来说,“我鱼和熊掌可以兼得。”他笑了。
最终,这是阿哈罗诺夫最初问题的答案:上帝通过掷骰子与宇宙玩耍能得到什么?为什么当我们试图从当下这个时间切片来看待量子世界时,它总是必须保留一定程度的模糊性?这个漏洞是必要的,这样未来才能对现在施加整体的拉力,而又不会在任何特定情况下被抓个正着。
“未来只有在可以将其影响解释为错误的情况下才能影响现在,”阿哈罗诺夫说。
这种认识是解释逆因果机制的绝妙之举,还是承认未来对过去的影响永远无法完全证明,这仍有待商榷。与豪厄尔共同设计罗切斯特激光放大实验的安德鲁·乔丹指出,甚至对于他的结果是否支持阿哈罗诺夫版本的逆因果关系,都存在根本性的争议。没有人质疑他的团队直接的实验结果,但“关于弱值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们在物理上对应什么——如果它们真的在物理上对应任何东西的话——存在很多哲学思考,”乔丹说。“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必将它们解释为未来影响现在导致的结果,而是它们向我们展示了量子力学中我们仍然有很多东西需要理解。”尽管如此,他乐于被说服改变看法:“一年后,我可能就会改变主意。”
波佩斯库认为,罗切斯特的发现至关重要,因为它为基于弱测量开辟了全新的实验室探索领域。从量子力学的传统解释出发,物理学家们并未意识到这种测量是可能的。“通过他在弱测量方面的工作,阿哈罗诺夫开始提出关于量子力学中什么可能的问题,这些问题以前没有人想过可以被阐明,”波佩斯库说。
阿哈罗诺夫依然谨慎。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他的理论得到认可。如果主流物理学注定最终会认真对待他的时间扭曲思想,那么它就会实现。
那托拉克森呢?他也与自己的命运融为一体。几个月前,他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拉古纳海滩。“我现在住的房子能再次听到海浪声——真是解脱,”他说。他觉得自己终于回到了他一直注定要去的地方。
宇宙有宿命吗?
来自未来的反馈是否正在引导生命、宇宙以及万物的发展?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坦佩分校的保罗·戴维斯和他的同事们正在调查宇宙是否有宿命——如果有,是否有办法探测其诡异的影响。
宇宙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困惑,为什么我们宇宙的条件——例如,它的膨胀速度——为星系、恒星和行星提供了理想的滋生环境。如果你掷骰子创造一个宇宙,很可能你不会得到一个像我们这样如此有利于生命的宇宙。即使你能将生命视为理所当然,也不清楚140亿年是否足以让它偶然进化。但是,如果宇宙的最终状态已经确定,并且正在时间倒流影响早期宇宙,那么它可能会放大生命出现的几率。
戴维斯与哥伦比亚安第斯大学的阿隆索·博特罗合作,利用数学模型表明,为宇宙设定特定的初始和最终状态会影响其间产生的粒子类型。“我们已经为一个简化的、一维的宇宙做了这项工作,现在我们计划将其扩展到三维,”戴维斯说。他和博特罗还在寻找宇宙最终状态可能追溯性地留在宇宙大爆炸遗迹辐射上的“印记”,这些印记可以被去年发射的普朗克卫星捕捉到。
理想情况下,戴维斯和博特罗希望找到一个单一的宇宙命运,能够解释三个主要的宇宙学谜团。第一个谜团是为什么宇宙的膨胀目前正在加速;第二个是为什么一些宇宙射线似乎具有超出正常物理学允许范围的能量;第三个是星系如何获得其磁场。“目标是查明大自然是否一直在进行她自己的‘后选择’,导致这些意想不到的效应出现,”戴维斯说。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比尔·温鲁对戴维斯的想法很感兴趣。“这可能对早期宇宙的任何样子都具有实际意义,”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