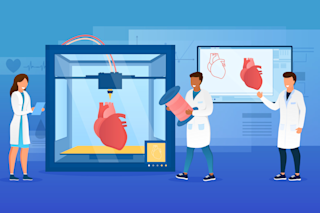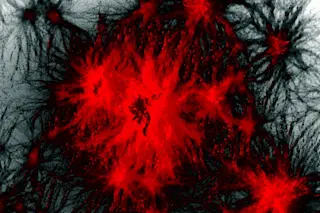莱昂·卡斯曾担任乔治·W·布什总统生物伦理委员会主席,他深谙争议,也熟悉科学与政治交汇处的险恶之地。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就干细胞研究和克隆等热门问题向总统提供建议,有时被斥为共和党右翼的工具。但尽管他的一些观点与强硬派一致,这位拥有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医生却很难被归类。“我并非来自某个学派,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他说。
他是一位老式道德主义者,持有的一些观点非常不合时宜,甚至可以说是前现代的。他仍使用“私生子”一词来形容非婚生子女,并对我们文化中“女性贞操”的丧失感到绝望。与此同时,他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影响感到担忧,并相信融合、宽容和包容。归根结底,真正让许多科学家感到恼火的是卡斯认为社会有责任监管研究,以及他经常警告某些技术可能产生的非人化影响。
生物伦理委员会的建议虽然实质内容丰富且学术性强,但总体上并未被政策制定者采纳,随着干细胞研究辩论陷入僵局,该组织的声势也逐渐减弱。卡斯于九月离开了委员会,目前是保守派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的研究员,他的办公室就在林恩·切尼(Lynne Cheney)的办公室旁边。他与《Discover》杂志坐下来,回顾了他的任期,并讨论了他的信仰、他的影响以及他对未来的担忧。
你是生物伦理委员会的主席,但你不认为自己是伦理学家。为什么?
我不认为自己拥有专业的伦理学知识,事实上,我对这种专业的存在表示怀疑。“伦理学家”这个词是最近才出现的。我更愿意说,我从事的是对各种人类经验进行道德反思,但并非通过任何道德理论或体系的视角来看待它们。我是一位老派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关心的是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不仅仅是道德方面。
你是如何形成这种观点的?
我的父母是我主要的启蒙者之一。他们都是东欧移民,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我的父亲在芝加哥南区经营一家服装店。我的母亲深夜阅读小说。那是一个讲意第绪语、世俗、偏向社会主义的家庭,和当时许多其他家庭一样,但非常强调要做正确的事情,做一个“好人”(mensch)。晚餐时会讨论道德问题。
我是越南战争的早期抗议者。我可能有点像个和平主义者。我在哈佛读研究生时,我妻子和我一起在密西西比州从事民权工作。我回来后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贫穷的黑人农民比我在哈佛的同学更有荣誉感?我当时觉得答案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
你目前正在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应对进步和技术。
我认为有很多因素阻碍我们以明智的方式应对技术进步。存在一种偏向进步的巨大文化倾向,认为创新就是好的创新。我们热爱科学家探究的自由、技术发明家的自由、企业家开发的自由以及顾客购买他们想要的东西的自由。国家就是基于这个原则运行的。我倾向于一种更经典的悲剧观,即所有美好的事物都伴随着一些坏的东西。我们为一切都要付出代价。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付出了代价,那么代价就会更高。在生物医学领域,那些为你带来新奇事物的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他们是人道主义者。他们致力于治愈疾病、减轻痛苦、延长生命。如果有人说:“在这里慢下来,”这看起来就像是将狭隘的宗教观点强加于多元化的社会,然后回应是“别用你的道德观来管我的科学”。
创新带来的商业压力呢?
我在科学界的一些老朋友非常担心生物技术公司以及它们对学术科学的侵入如何扭曲了议程。支持突破性进展的商业利益根深蒂固。没有任何经济利益支持放慢速度。在欧洲,大屠杀之后,对人类尊严的关注被体现在了法律中。总的来说,美国人挥舞着自由和平等的旗帜。我们没有(宗教形式以外的)公共语言来处理这些问题。
你认为有哪些创新应该被禁止?我支持对少数几件事进行立法禁止。因为邪恶与善良紧密相连,你不想扼杀下金蛋的鹅。但我会禁止人类克隆。并且我会将医生协助自杀和安乐死保持非法状态。
当代医学研究还让你担心什么?对我来说,我们最应该关注的领域是精神药理学以及超出明确精神疾病治疗范围的应用——整类改变情绪、令人欣快的药物,它们将满足感与通常负责获得满足感的人类活动分离开来。这并非我个人的清教徒作风。我担心的是一个人们拒绝为自己负责的社会,一个人类的愿望被截断的社会,因为实现它们太困难、太痛苦。我们将悲伤视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些经历过可怕创伤的人呢?他们不应该被允许用药物来抑制他们的坏记忆吗?我完全同情那些在世贸中心的人,或者经历过强奸想通过某种方式麻痹这些记忆来减轻创伤的人。我对此完全支持。但这也会助长消除那些耻辱性行为、那些表现得可耻的行为、那些我们应该感到内疚和懊悔并寻求原谅的行为的记忆的可能性。将自己置于记忆编辑者的位置,就像是获得了一种非我们真实生活过的生活,创造了一种与我们所经历的现实不符的身份。
你对社会的“医学化”提出了担忧。但这是否太迟了?
我去年春天教了我的第一门生物伦理课程。在几个方面,班级比我的委员会更能看到儿童精神药物使用中的危险。有几位学生曾服用利他林。他们含蓄地谈论了服用这种药物的意义,以及他们与一些坚持下来的朋友有何不同。我认为大多数年轻人希望真正快乐,而不是看起来快乐。他们希望通过药物获得击中棒球的乐趣,而不是学习如何击球吗?不。他们知道卓越与平庸的区别,并希望感受到自己成就的意义。
但你并不是完全反对使用这类药物。
我不是那种为了别人的好处而希望别人受苦的怪物。我们有时在痛苦中学习,但我并不赞成以某种方式增加世界的痛苦。
作为委员会主席,你最受关注的成就之一是报告《生育与责任》。委员会发表该报告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希望建立一些界限:除了生育孩子,不得怀孕;不得将人类胚胎出于任何原因置于动物体内;不得用动物精子使人类卵子受精,反之亦然;不得在任何阶段买卖或申请人类生命专利;除非由双方成年人的卵子和精子结合所生,不得生育。关键是,任何借助辅助生殖技术受孕的孩子,都不应被剥夺与父母双方的血缘和生物联系,这是所有“自然”出生的孩子所拥有的。任何孩子都不应说:“一个胚胎是我的父亲。”
这份报告产生了什么影响?
去年,我们的一些建议被写入了法律。措辞经过仔细斟酌,以满足支持生命者和科学家成员双方的要求。我们展示了在捍卫共同价值观的同时,如何在继续就人类胚胎的道德地位存在分歧的情况下达成一致。我们的榜样和具体建议,应该能引起任何希望克服当前国会僵局的人的兴趣。
为什么干细胞会成为主导性的生物伦理议题?干细胞研究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首要议题——上帝知道为什么。部分原因是美国堕胎裁决的产生方式以及堕胎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程度,无论是在生命末期的安乐死,还是在生命的开始时的堕胎和胚胎毁灭,杀戮和生命毁灭的问题都被视为生物伦理问题。
科学家们最近宣布,他们发现了一种将人类皮肤转化为具有胚胎干细胞全部治疗潜力的细胞的方法。这对辩论有什么影响?
这是大家一直在等待的。他们打出了全垒打。委员会最受欢迎的举措之一是建议科学能够带来救援,找到一种绕过伦理僵局的方法,来获得一种大家都会认可的获取干细胞的方式,这样我们就可以结束这个令人烦恼的政治时期了。这确实令人兴奋。
布什政府被一再指责将政治干预科学。你经历过这种情况吗?
我们从未受到任何干预。总统在前一天才收到《生育与责任》报告的副本,这是出于礼貌。
委员会的另一份影响深远的报告题为《超越治疗》。医疗治疗和医疗增强之间有什么区别?
没有明确的界限。但经典意义上的治疗是去除疾病或残疾,恢复健康和正常。增强似乎超越了自然的既有能力,无论是提高智商和记忆力,还是通过类固醇或基因改造肌肉来提高运动成绩。这会引发一系列问题。首先是,你怎么知道这种改变实际上是一种进步?没有人会质疑修复唇裂。另一方面,有一个医生为了不影响病人打高尔夫球的挥杆而切除了她的一部分乳房。在服务于病人的健康和满足病人的愿望之间存在区别。而在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灰色地带。
那么你反对整容手术吗?如果有一些非执业医师来做这类手术,我会感觉更好。将医学艺术用于满足人们的愿望——即使其中一些愿望是合理的——这是一种艺术的腐蚀。在这方面我有点老派。如果医学不受某种对完整性或治愈的承诺的指导,它就沦为一家简单的汽车修理厂,由技师受雇表演。
我们是否过于关注个人幸福?我认为有些方面是正确的。家庭更加原子化。另一方面,至少存在一种认识到我们正陷入困境。有大量的工作正在进行,内容是所谓的公民参与。
宗教机构也属于其中。你是信徒吗?我是芝加哥一家犹太教堂的成员。我不太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通常意味着不。好吧,就拿一个简单的方面来说。我认为有来世吗?我不认为我曾对这个问题有过任何期待。我对此问题持不可知论。然而,我喜欢活得好像我必须为我的所作所为负责。我感到感激。我知道对谁或什么感到感激吗?我不确定。我是否意识到有力量以我无法控制的方式推动我?是的。我是否认为有一个留着长胡子的老人在上面接听客房服务电话?不。
未来最重要的生物伦理问题是什么?其中之一是大型医疗保健系统问题。这部分是生物伦理话题。有些人用公平来衡量。有些人用获得医疗保健的权利来衡量。我更倾向于这样说:一个体面富裕的社会应该如何对待其公民的健康?长期护理的伦理危机可能是我们处理过的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影响着美国几乎所有家庭的生活。科学家们希望神奇地治愈阿尔茨海默病。我家有此病史。这令人沮丧。现在有百分之四十的人会经历长达十年的衰弱、虚弱和痴呆,然后去世。这是最常见的死亡轨迹。在生物技术领域,我认为潜在的危险与基因学有关。还有药理学:药物引起的快感或自豪感是脱离了人类活动本质的影子,而人类活动才是人类繁荣的精髓。我们想对自己感觉良好,但只有在我们做得好、成为好人的结果下。
你是否对人们会自愿选择艰难的幸福之路而不是轻松的出路感到乐观?我对改变文化有多容易不抱任何幻想,但我从未遇到过一个不怀有某种对善的渴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