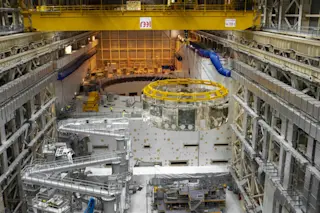请看世界上最弱的计算机网络:它坐落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一间教室里,总共连接着两个处理器,横跨一个地下走廊,传输着一个惊人的一比特信息。前提是它能工作,但它目前不能。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员杰夫·金布尔说:“我们希望它能在新千年之前投入使用。”考虑到其糟糕的规格,听到金布尔的网络被广泛认为是计算机科学中最具挑战性的项目之一,这可能有点令人惊讶。这是因为他的网络旨在传输的那个比特数据,将不是日常网络中常见的普通“1”或“0”。它将是两者的混合——即所谓的量子比特,或“qubit”。
金布尔正试图建立世界上第一个量子计算机网络。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有点超前了,因为他本人以及任何其他人都没有接近建造一台实用的量子计算机——也就是说,一台能够处理量子力学特有的那种奇特的多重现实状态数据的计算机。尽管如此,这种令人惊叹的激进的数据处理方法有望带来巨大的好处,以至于年轻的量子计算领域一直吸引着不仅来自计算机科学,还有来自物理学、数学和化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就在几年前,大多数计算机科学家还怀疑量子计算机是否能被建造出来。现在,舆论似乎正在转向,过去一两年里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尼尔·格申菲尔德已经制造出了一台简单的量子计算机。它不能做很多事情——它只能从四个名字中选出一个——但它的速度比传统计算机快。
量子计算有什么大不了的?想象一下,你身处一栋大型办公楼,需要在一栋办公楼数百个随机选取的办公室中的一个桌子上找一个公文包。就像你必须穿过大楼,一扇门一扇门地打开来寻找公文包一样,普通计算机必须或多或少地串行地遍历长串的1和0,直到找到答案。当然,你可以通过组织一个团队,协调逐层搜索,然后让他们重新聚集在一起比较结果来加快寻找公文包的速度。普通计算机也可以做这类事情,通过将一个任务分解并在多个处理器上并行运行各个部分。然而,那种额外的协调和通信会带来巨大的开销。
但如果不是独自搜索,或者组织和管理一个团队,而是你能立即创造出和你一样多的自己,就像大楼里有多少个房间一样,所有版本的你都可以同时查看所有办公室,然后——最棒的是——所有版本的你都会消失,只留下找到公文包的那一个?
这就是量子计算机工作方式的一个例子。量子计算机将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在某些条件下,原子尺度世界中的居民可以存在于多种现实中——原子和亚原子粒子可以同时在这里和那里,快和慢,向上和向下。怎么做?即使是物理学家也对此没有定论,但过去七十多年来无数的实验已经证实了这种奇异的现象。通过将这些不同的原子状态视为代表不同的数字或其他类型的数据,一组原子及其各种潜在状态的组合可以被用来同时探索一个问题的所有可能答案。通过一些巧妙的操作,代表正确答案的组合就能脱颖而出。
传统计算机芯片上的组件越来越微小,它们可能很快就会达到性能和速度的物理极限;一些研究人员希望量子计算机能够突破这些障碍。但是,尽管许多研究团队在艰苦奋斗,即使是最乐观的人也不指望在未来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做出比演示一些几乎毫无用处的简单设备更多的事情。
即使如此,量子计算的未来也并非板上钉钉。任何计算机——无论是量子计算机还是其他类型的计算机——如果不能被编程来执行实际任务,就无法发挥太大作用。许多研究人员一直在思考量子计算机是否能够解决现实世界的计算问题——或者至少比传统计算机显著更快地运行它们。
实际上,大多数应用并不适合量子计算。这是因为典型的计算机任务,如计算卫星轨道或旋转图形图像,需要串行进行的计算机逻辑,每一步都依赖于前一步的结果。量子计算无法加速这类任务。例如,如果不是在一个房间里寻找公文包,而是你需要把一个手表从散布在所有房间里的零件组装起来,那么拥有多个“你”并没有多大优势。无论是一个人还是那一千个“你”中的一个来完成这项工作,仍然需要有人走进每个房间,拿起手表的一个组件,然后按照正确的顺序,一个接一个地将其添加到正在组装的手表中。所需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完成的手表——要求每个搜索者都完成一部分工作;任何人的贡献都不能被丢弃。
相反,适合量子计算机的任务将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在众多可能的量子态组合中,只有一个能够独立地找到并代表答案。其他组合,都在朝着错误答案前进,必须按照物理学家的说法,“坍缩”到正确的答案。正是这种选择性的坍缩带来了挑战。毕竟,足够大的量子计算机总是可以被编程,使其多状态原子代表所有可能的答案。但如果无法表明众多结果中的哪个是正确的,那又有什么用呢?
物理学家们提出了一种通用的策略来筛选出所需的结果。该方法基于原子表现得像波而不是粒子的能力。就像两股相同但相反的海浪碰撞一样,处于多种状态的原子可以相互抵消或相互增强,具体取决于它们的对齐方式。
不幸的是,在已故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首次提出量子计算的可能性之后,十年间没有人能够想出一种方法将这种现象应用于实际任务。在这段时间里,物理学家们坚信量子计算机只能做一件事:进行量子力学相关的计算。这就像当初计算机芯片刚被开发出来时,其设计者宣布这些芯片只能用于了解硅的电学特性一样。
然后,在 1994 年,AT&T 研究员彼得·肖尔发现了量子计算机可能处理的第一个实际任务。数学上一个更棘手的难题是找到非常大数字的质因数。 (质数,如 1、3、5、7 等,本身无法分解成更小的整数因子。)肖尔发现这个问题可以简化为确定一个复杂的数学序列何时开始重复。肖尔意识到,识别重复序列是量子计算机可以做的事情。粗略地说,通过将序列的所有元素编码到量子比特上,代表相同——因此重复——的序列的量子比特状态可以排列起来相互加强。一段时间后,这些被强化的量子比特将压倒其他所有信息,从而提供答案。理论上,一个拥有约 5,000 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可以在大约 30 秒内解决一个传统超级计算机需要 100 亿年才能解决的质数问题。
现在,碰巧这个看似晦涩的任务有一个重要的应用。计算机数据通过打乱表示数据的代码字符来防止被窥探。解密数据的数学“密钥”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通常是 250 位长——及其质因数。这种加密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因为没有传统计算机能在合理的时间内找出如此大数字的质因数。但是,至少在理论上,量子计算机可以彻底破解这些基于质数的加密方案。因此,量子计算机黑客不仅可以轻松访问信用卡号和其他在计算机网络(包括互联网)上频繁传输的个人信息,还可以获取政府和军事机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某些政府机构——基于“最好领先而不是落后”的假设——一直在向量子计算机研究投入数百万美元。
量子计算机的成功不一定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数据都会变得不安全。即使计算机科学家能够打破所有预测并在不久的将来建造出工作设备,密码学家也会转向不基于质数的方案。其中一种方案已经存在。它涉及将数据编码为抽象的多维空间中两个秘密点之间的最短距离。目前还没有人证明量子计算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在数据安全方面,量子计算机似乎是“赐予”与“夺取”并存的。这是因为量子计算机——理论上——可以用于将数据加密成一种多状态形式,只有发送者专门准备用于读取第一台计算机数据的其他量子计算机才能正确读取。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的大卫·温兰德说:“你可能只需要大约十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就可以用于加密应用。”
量子计算机不仅不太可能摧毁互联网的完整性,而且最终也可能成为它的巨大推动力。两年前,贝尔实验室的研究员洛夫·格罗弗发现了一种将量子计算机应用于我们日常进行的任务的方法:在庞大的数据存储库中搜索隐藏的信息。在数据库中查找信息就像寻找公文包的问题一样。如果不同量子比特状态的组合能够分别查看数据库的不同小片段,那么其中一种状态组合就会找到所需的信息。
格罗弗还想出了如何让带有正确答案的量子比特状态组合脱颖而出。再次粗略地说,该方案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代表“空房间”的量子比特状态——也就是说,尚未找到所需数据的量子比特——彼此之间的相似性比与带有答案的量子比特状态更强,就像空房间比装有公文包的房间更相似一样。由于它们的相似性,错误的量子比特状态可以组合起来相互抵消。最终,代表正确答案的唯一一组量子比特状态得以保留。
由于“正确”和“错误”量子比特状态之间的差异比质数问题更微妙,因此减慢了取消过程,这种量子搜索提供的加速不会那么惊人。例如,要搜索 1 亿个地址,传统计算机在找到所需信息之前必须尝试约 5000 万次;量子计算机需要约 10,000 次尝试。但这仍然是一个显著的改进,而且随着数据库的增大,这种改进会越来越大。此外,数据库搜索是一项基本计算机任务,任何改进都可能对大量应用产生影响。互联网将如何受益?现在,搜索所有公开可用的网页以查找特定关键词需要几秒钟(假设您有良好的连接)。但请记住——网络尚处于起步阶段。十年后,它可能会增长数千倍,并且有更多的人使用它来完成更多工作。可以想象,所有这些活动将使传统计算机不堪重负。
许多理论家正在努力想出能够有用解决其他类型问题的量子软件程序策略。但对于其中许多策略来说,错误答案抵消的过程非常低效,它们只能比传统计算机提供适度的改进。“有一大类问题,量子计算机比经典计算机快两倍左右,”加州理工学院的理论家约翰·普里斯基尔指出。“但我们追求的是更令人兴奋的东西。”
普里斯基尔等人正在密切关注的一个可能性是,一个量子程序可以确定两个复杂且外观差异很大的、连接了多个点的图实际上是否等价。这样的程序可能对芯片设计者非常宝贵,例如,他们经常在不知道是否真正改变了任何东西的情况下更改组件。另一个目标是“旅行推销员”问题,它本质上是找出连接大量分散点的最短路径。这个问题有多种形式,包括航空公司在用尽可能少的飞机服务最多城市时面临的挑战。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好处是,它们都属于一大类被认为相关的数学问题,因此破解其中一个问题可能为解决所有问题指明方向。
到目前为止,很少有研究人员愿意预测量子计算是否会超越少数几个应用。尽管如此,总体趋势是令人鼓舞的。尽管许多甚至大多数物理学家最初怀疑量子力学的难以捉摸的本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发现实际量子计算的微妙、根本性障碍,但深入而广泛的理论搜索尚未发现一个。牛津大学物理学家大卫·杜奇说:“你无法预测知识的未来增长,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让我失望。”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提出的量子计算方案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该领域的火爆。
总之,急什么呢?计算的历史表明,硬件和软件的突破往往发生在它们最终解决的问题之前。也许当我们到时候需要搜索如此庞大的数据库,以至于普通计算机需要数月才能处理完时,量子计算机已经准备就绪并投入运行。
当然,那将使计算机科学家能够去寻找下一个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