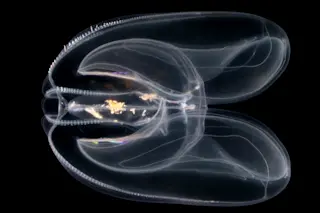修士盖伊·康索尔马尼奥(Guy Consolmagno)占据着天堂里的一小块空间。作为一名耶稣会修士和梵蒂冈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他在位于教皇夏季行宫的卡斯特尔甘多尔福(Castel Gandolfo)的天文台总部工作,那里距离罗马有45分钟的火车车程。
卡斯特尔甘多尔福位于意大利拉齐奥地区(Lazio region)的高地,俯瞰着异域风情、蓝宝石般湛蓝的阿尔巴诺火山湖。眼前的景色如梦似幻。“这里非常适合观测掩星现象,比如2004年的金星凌日,”康索尔马尼奥说,“我们观测了彗星撞击木星,因为最初的事件只有在这部分地区才能看到。”
天文台穹顶观测室下方是构成梵蒂冈天文台其余部分的办公室。其中一间书房的架子上摆满了精装期刊,一直堆到高高的天花板。康索尔马尼奥从架子上抽出一本,大声朗读道:“艾萨克·牛顿先生关于新望远镜的记述。”他给我看,然后微笑着说:“我想他前途无量。”
大楼还设有小型实验室和研究区,正在进行长达数十年的项目,例如陨石编目。虽然这里是梵蒂冈天文台的官方所在地,但一个相关机构——梵蒂冈天文台研究小组——设在亚利桑那大学的斯图尔德天文台(the Steward Observatory)。在那里,梵蒂冈可以更方便地使用高科技设备,正在对暗物质、类星体(quasars)和宇宙膨胀进行详细研究。
“宇宙值得研究,仅仅因为它是值得研究的,这是一个宗教思想,”康索尔马尼奥说,“如果你认为宇宙本质上是美好的,是美好上帝的表达,那么研究宇宙如何运作就是与造物主亲密接触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崇拜。这也是进行任何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力。”
作为一名科学家同时也是耶稣会修士,康索尔马尼奥认为科学提出了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反过来又引发了宗教探究。
“一百年前我们还不了解大爆炸,”他说,“现在我们对一个巨大、膨胀且不断变化的宇宙有了了解,我们可以提出以前不会想到的哲学问题,比如‘拥有多重宇宙(multiverses)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很棒的问题。科学无法回答它们,但科学通过告诉我们存在什么,促使我们提出这些问题。它让我们回到创世的七天——那是诗歌,美丽的诗歌,下面隐藏着一个教训——然后说,‘哦,第七天是上帝休息,以此提醒我们上帝并非包办一切。’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但赋予了你我在这个宇宙中做出选择的自由。”
从17世纪伽利略受审和被谴责(trial and condemnation of Galileo)中吸取的教训,引导了梵蒂冈内部一个科学谨慎和犹豫的时代。今天,梵蒂冈对待科学的方式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涉及教会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罗马教廷(The Roman Curia)——教会的治理机构——包括5个宗座科学院和11个宗座理事会的网络,每个机构都负责从促进基督徒合一到殉道者编目等各种任务。在不同程度上,这16个机构——当然还有独立的梵蒂冈天文台——都与科学问题相交叉,它们倾向于依靠一个学院的努力来提供澄清和咨询:宗座科学院。宗座科学院坐落在梵蒂冈城深处一座数百年历史的建筑中,它是一个令人惊讶的非宗教机构,也是梵蒂冈最不为人所理解的机构之一。
科学院内部 尽管宗座科学院在平信徒中几乎不为人知,但它却是圣座内部一个独立且极具影响力的机构。多年来,其成员名单上星光熠熠,堪称20世纪科学界的风云人物(包括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尼尔斯·玻尔和埃尔温·薛定谔等),目前拥有80多位国际院士,其中许多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并且并非所有都是天主教徒——其中包括爱开玩笑的无神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
科学院成员由现任成员选举产生。没有宗教、种族或性别标准。候选人根据其科学成就和高尚的道德标准进行挑选。在提名成员时,会咨询梵蒂冈国务秘书处,以防止任命有可疑历史的人。
“我们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群人——有许多不同的宗教和态度,”诺贝尔奖得主、激光发明者、物理学家查尔斯·哈德·汤斯(Charles Hard Townes)说,“科学家参与其中并努力帮助天主教会,就其政策提供建议至关重要。世界上许多文明并不直接受到科学技术决策的影响,但它们受到天主教会的命令和决策的影响。”

修士盖伊·康索尔马尼奥,一位天文学家,在卡斯特尔甘多尔福的梵蒂冈天文台内。| 图片由迈克尔·梅森提供
人类遗传学领域的领导者马克斯汀·辛格(Maxine Singer)在她成为会员之前就对学院的工作赞不绝口。“我参加了1980年代早期关于遗传学的一个研究周,听取了关于刚刚兴起的新生殖技术的讨论,”她说,“在梵蒂冈谈论这些事情真是引人入胜,而报纸和媒体却会让你相信梵蒂冈不会讨论它们。”
科学院的渊源几乎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1603年,植物学家费德里科·切西王子(Prince Federico Cesi)创立了“猞猁学院”(Accademia dei Lincei),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其成员——伽利略和法比奥·科隆纳等著名意大利学者——需要像猞猁一样敏锐的眼睛才能进行科学发现。
阿卡德米亚学院(Accademia)慢慢解散,直到1745年才再次重组,然后又消失并在1795年再次出现,由费利西亚诺·斯卡佩利尼神父(Padre Feliciano Scarpellini)指导,他汇集了来自教皇国(the Papal States)(意大利中部一个由教会统治的大片领土)的各种科学家。在政治动荡导致更多的组织障碍之后,1870年——意大利统一之后——该组织演变为两个独立的机构:阿卡德米亚国立猞猁学院(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和后来的梵蒂冈宗座科学院,后者于1936年形成了现在的形式。
如今,该学院的使命包括促进数学、物理和自然科学的进步,并参与相关认识论问题和议题的研究。学院召开全体会议,成员们就特定主题发表演讲。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重点介绍科学领域的最新进展。下一届会议定于十月举行。
尽管学院的使命看起来和其他科学机构一样温和,但它在梵蒂冈的存在却引发了争议。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人们对人口问题感到担忧时,该学院发布了一份报告(the academy issued a report),称“全球范围控制生育是不可避免的需要”,这一立场据说激怒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教宗比任何人都清楚宗座科学院的确切存在理由。1992年,约翰·保罗二世告诉成员们:“你们学院的宗旨,正是在科学现状及其适当的界限内,辨明并阐明什么可以被视为既定真理,或者至少具有如此高度的概率,以至于拒绝它是不明智和不合理的。”在教宗看来,学院是区分科学事实与虚构的工具。
教皇与科学院目前的合作关系表明,科学问题在教会内部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梵蒂冈最近在一系列与科学相关的问题上采取了坚定立场。2007年,梵蒂冈官员对临终关怀问题发表意见,指出即使没有康复的希望,也有道德义务维持处于植物人状态(in a vegetative state)的人的生命。这一立场与那些预先指示要求在进入这种状态时终止补水和营养的人的意愿相悖。虽然梵蒂冈支持器官移植,但2004年,其宗座生命科学院的副院长告诉路透社,克隆人类胚胎“是纳粹在集中营里所为的重演”。
天主教与争议 自1993年以来,意大利物理学家尼古拉·卡比博(Nicola Cabibbo)一直担任宗座科学院院长。尽管他并非神职人员,但他一直在经受对教会处理科学问题的无数批评。尽管如此,他对科学与宗教的看法仍然坚定不移,且出人意料地务实。
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对生命起源的科学理解需要信仰上帝时,卡比博语出惊人。“我会说不,”他告诉《国家天主教记者》(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的一名记者,但补充道,“科学无法回答关于事物为何存在以及其目的的终极问题。”卡比博的言论反映了教会不断努力调和科学与宗教,这是一个远超梵蒂冈围墙的话题。
如今,在梵蒂冈的科学项目中,与任何人交谈几乎都无法避免提及直言不讳的无神论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作品。道金斯是一位杰出的进化论理论家,他撰写了《上帝错觉》(The God Delusion)一书,该书成为国际畅销书。
“你在他的书中看到的是对我宗教的漫画式描绘,”宗座科学院姐妹组织宗座文化理事会副秘书蒙西格诺·梅尔乔·桑切斯·德·托卡(Monsignor Melchor Sánchez de Toca)说。
“他作为科学家享有盛誉,但他不是神学家,”康索尔马尼奥说。
“我们称(道金斯的立场)为科学主义,在通谕中也有提及,”罗马宗座使徒女王大学(Regina Apostolorum Pontifical University)哲学系主任拉斐尔·帕斯夸尔神父(Father Rafael Pascual)说。
道金斯后来告诉我,“科学主义是一个贬义词,有时用来指科学可以解释一切并自大地将解释一切的特权归于自身的观点。科学无法告诉你什么是对错。当涉及到真正有趣的问题时,比如‘物理定律从何而来?’或‘宇宙最初是如何产生的?’我真的不知道科学是否会回答这些深奥且目前神秘的问题;我确信如果科学无法回答它们,其他任何东西也无法回答。但也许永远没有人能回答它们。”
道金斯对教会通过哲学在科学与神学之间架设桥梁的使命表示怀疑。“根本没有桥可架,”他说,“神学完全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学科。”在我与道金斯的谈话中,曾提到梵蒂冈天文台受人尊敬的退休主任(因此也是科学院前成员)乔治·科因神父(Father George Coyne)。
“几周前我见过他,非常喜欢他,”道金斯说,“他说,完全没有理由相信上帝,所以我问他,‘你为什么相信上帝?’他说:‘很简单。我从小就是天主教徒。’当我想到优秀的科学家——有些虔诚的信教者,其中许多是天主教徒,比如耶稣会修士和神父——我总搞不清楚他们是否在进行思想上的‘隔断’。有时你逼问他们,结果发现他们相信的东西与《信经》中说的截然不同。结果他们真正相信的只是宇宙根源处存在某种深不可测的未知。”
道金斯的评论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在我采访的许多神父中,每个人都表达了一种复杂的哲学,这似乎比普通信徒心中的想法更为抽象。那么,相信宇宙中存在一个深不可测的未知根源,对于科学(such a bad thing for science)来说,即使它通过基督教概念和意象的框架来感知,又真的那么糟糕吗?
“我没有告诉理查德·道金斯没有理由相信上帝,”科因说,他视道金斯为朋友,“我说理由不足。信仰不是非理性的,它是超理性的;它超越理性。它不与理性矛盾。所以我的看法正是,对我来说,信仰是上帝的恩赐。我没有通过推理得到它,我也没有赢得它——它是通过我的家人和我的老师作为礼物赐予我的……我的科学有助于丰富上帝的这份礼物,因为我在他的创造中看到了他是一位多么奇妙和慈爱的上帝。例如,他通过使宇宙成为一个进化的宇宙——他没有把它造成一个现成的,像洗衣机或汽车一样——他把它造成一个在其中有创造力参与的宇宙。道金斯真正应该问我的问题是,‘你为什么有信仰的恩赐而我没有?’这让我很尴尬。我唯一能说的是,要么你拥有它却不知道,要么上帝以不同的方式与我们每个人合作,上帝不会拒绝任何人的这份礼物。我坚信这一点。”
我期待听到他进一步为自己的信仰辩护,于是我问科因科学对宗教,特别是对《圣经》产生了什么影响。
“《圣经》中没有科学。一点都没有,”科因说,“《圣经》是不同时代不同人写的。有些书是诗歌,有些是历史,有些是故事。”
“你的意思是《圣经》不应该受到科学的严格审查吗?”我问。
“没错,”科因说,“绝对如此。”
影响世界 宗座科学院在不断变化的文化态度中扮演的角色,也使其成为特殊利益团体的目标——并常常使其陷入争议。
2004年,美国驻圣座大使馆与科学院联合举办了一场名为“喂饱饥饿的世界:生物技术的道德 imperative”的会议。仅会议名称就在世界各地的农民和农业学家中引起轩然大波;它暗示转基因(GM)食品是解决世界饥饿的方案。然而,批评者认为,转基因食品使农业公司在经济上对小型生产者造成不公平优势,并且转基因食品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
早在2000年,学院的一份研究文件就指出:“转基因植物可以在缓解世界粮食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在教会内部,这远非一致的意见。
“关于世界饥饿问题,梵蒂冈的官方政策一直是,问题不在于生产,而在于分配,”全国天主教农村生活会议(National Catholic Rural Life Conference)前执行董事大卫·安德鲁斯修士(Brother David Andrews)说。
我问安德鲁斯,他是否觉得宗座科学院容易受到美国大使馆和大型农业企业的影响。“是的,当然,”他说,“彼得·雷文(Peter Raven)是科学院的成员,他也是密苏里植物园的负责人,该园获得了孟山都公司(Monsanto)的资助。”孟山都公司是一家拥有16,000多名员工的跨国农业公司,是基因工程种子领域的领先生产商。
虽然会议的议程偏向生物技术的支持者,但安德鲁斯告诉我,最终美国大使馆、农业综合企业和科学院本身并未成功将转基因食品定位为梵蒂冈眼中的“道德 imperative”。相反,他们承认了批评者的担忧。梵蒂冈对此问题保持谨慎和沉默。
“我认为(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争论)是学院的一个尴尬插曲,”安德鲁斯说。
尽管存在这些困难的事件,梵蒂冈仍然乐于承认科学技术在社会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以及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所带来的积极进步。困扰教会官员的是对人性的机械论观点(mechanistic view of humanity)的顽固存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和其他文化担忧,梵蒂冈转向宗座文化理事会,该理事会是梵蒂冈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某种中介。
“人类常常被视为由可剪切粘贴的部件和元素组成的集合体,而不是一个生物有机体和具有精神价值的个体,”一份理事会出版物解释道,“解决这个问题被认为是刻不容缓的。”
宗座文化理事会受命向公众解释这些不断发展的教会教义,其方式是建立科学与神学之间的哲学桥梁。该理事会位于通往圣彼得广场的宏伟的调和大道(Via della Conciliazione)旁,是梵蒂冈的多元文化外展中心。其走廊和房间里装饰着教皇本笃十六世的照片、十字架和朴素的插花。这里井然有序,一切都显得规规矩矩。
“科学周围存在着一种神话,”蒙西格诺·德·托卡说,“许多人将大写的科学(seen by many people as a religion itself)视为一种宗教。科学本身也有神话:伽利略事件、达尔文、创世论——它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问题;它们属于文化。我们对这些趋势、这些现象感兴趣——例如,创世论者与进化论者之间的斗争。”
“我认为宗教和科学都是人类存在的一部分,”德·托卡继续说,“你不必选择其中一个——你可以两者都选择……科学可以净化宗教中的迷信……而宗教可以帮助科学留在其边界之内。”
历史上,神学家有时通过改变对《圣经》的解释来回应科学知识,从字面解读转向精神解读。例如,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在接受地球是球体这一观念时经历了挣扎,但最终还是承认了科学。“当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时,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圣经》,”德·托卡解释说。当科学提出与《圣经》似乎矛盾的真理(例如,缺乏全球洪水的证据)时,《圣经》固有的弹性就会简单地包容新的发现,任何明显的矛盾都会被归入寓言的范畴(在许多天主教徒看来,诺亚方舟就属于这一范畴)。
那么,天主教徒是否有可能通过对《圣经》的这种灵活解读,找到当代问题的可靠答案呢?我请德·托卡详细阐述当今文化面临的最紧迫问题。
“伦理问题非常紧迫,因为它们直接影响人类,”德·托卡回答说,“例如,克隆(cloning)、安乐死、避孕——它们不是科学问题,而是伦理问题。”
这些问题确实是伦理问题,但伦理问题在科学领域可能非常重要。今年早些时候,本笃十六世表示,体外受精“侵犯了保护人类尊严的屏障”。其他人则不确定教会的立场是否确实保护了人类尊严。
尽管与教会教义存在分歧,普林斯顿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一个问题上与梵蒂冈立场一致:天主教药剂师拒绝出售避孕药的权利。
“我尊重那些说他们不希望提供只能用于他们认为道德上错误的目的的特定处方药的药剂师,”辛格说,“我认为他们有义务明确表明他们正在这样做。”
在美国,大多数州不提供“药剂师良心条款”(pharmacist’s conscience clause),该条款合法地允许药剂师基于道德原因拒绝出售避孕药。(至少有八个州提供,包括阿肯色州、佐治亚州、密西西比州和南达科他州。)因此,《华盛顿邮报》报道,Kmart等公司的药剂师因出于良心拒绝出售此类药物而被解雇。
在意大利,生物伦理问题被放大。尽管意大利政府已将堕胎合法化,但根据联合国的一份报告,该国近70%的医生拒绝执行该手术。2008年5月,约1000人在意大利北部举行集会,抗议教皇在一次演讲中抨击堕胎后,梵蒂冈干预公共辩论。
梵蒂冈介入意大利政治不仅仅是一项指控;只要看看它在该国的利益,就能看出其影响力。据《泰晤士报》(伦敦版)报道,在意大利,教会拥有10万处房产,在罗马则拥有250所学校、65家养老院和18家医院。据意大利报纸《共和报》(La Repubblica)报道,意大利每年通过直接捐款和免税向天主教会提供约62亿美元。反过来,意大利也受益于梵蒂冈在该国各地的人道主义项目。批评者认为,这种安排赋予了梵蒂冈过大的自由度,可以将其天主教立场强加于意大利公众。
教会、科学与学术 2003年,宗座文化理事会开始协调一项名为STOQ的重点项目,其全称为“科学、神学与本体论探究”(Science, Theology, and the Ontological Quest)。该项目追溯到约翰·保罗二世呼吁科学家、神学家和哲学家之间重新展开对话。STOQ项目的目标是促进教会内部的科学素养——这在美国尤为重要。梵蒂冈的担忧之一是其神职人员可能对进化论所涉及的科学缺乏清晰的理解。在六所专门参与STOQ项目的宗座大学的帮助下,梵蒂冈正在取得一些进展。
其中一所大学是圣十字宗座大学,其图书馆位于一条狭窄的小巷中,离鹅卵石铺成的鲜花广场(Piazza Campo de Fiori)仅一步之遥,意大利农民在那里展示他们色彩斑斓的农产品。四个世纪前,就在同一个广场上,哲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被圣座活活烧死,这距离伽利略与教会发生冲突仅仅几十年。在他的众多异端邪说中,布鲁诺曾提出宇宙是无限的,并且存在许多太阳系。如今,他那懊悔的青铜雕像高耸在熙熙攘攘的市场上方,怒视着梵蒂冈的方向。如果他今天还活着,布鲁诺可能会对宗座大学中表达的观点感到惊讶,所有这些都没有受到惩罚的威胁。
“我们认为进化是我们现在可以用来解释世界进化的科学理论,我们不觉得有必要寻找不同的理论,”圣十字大学STOQ项目主任拉斐尔·马丁内斯神父(Father Rafael Martínez)说,“我们认为智能设计因此不是一个科学命题,而且——从神学和哲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错误的答案。”
相反,克里斯托夫·舍恩伯恩枢机主教(Cardinal Christoph Schönborn)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wrote an article),其中他提出新达尔文主义思想与天主教不兼容,并隐含地支持智能设计。科因神父是自然选择理论的直言不讳的支持者,他严厉批评了舍恩伯恩的立场。
如果圣座还有罗马宗教裁判所的任何残余,那它并不明显;马丁内斯肯定没有表现出来。他轻柔的声音和神父的服装同时反映了教会对科学的接受度和对宗教传统顽固的坚守。
“我们正在努力寻找并实现这种科学、宗教和信仰之间的和谐与协调,”马丁内斯告诉我。
“这真的可能吗?”我问。
“当然,”他说,“我们并不是说科学必须解释宗教。从超验信仰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能的。我想说,科学家觉得科学并不能给他一切。科学无法解释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爱、友谊等等。”
硬科学可能无法可靠地衡量人类情感,但还有其他宗教现象确实经常受到严格的科学审查:奇迹(miracles)。
“作为一名信徒,我接受奇迹,但我并不认为奇迹是我信仰的主要原因,”马丁内斯说,“为了封圣,必须有经医生以真实的实验方式认证的医学奇迹,从科学角度来看,这已经记录了很多很多次。”
马丁内斯解释说,虽然罕见,但奇迹仍然是可能的。“我们的世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混沌和不确定性占了很大一部分……但几率是万亿分之一,”他说,“在我看来,这不是问题,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方式不会与自然法则相悖。”
罗马城的另一所宗座大学则从不同的角度处理STOQ项目指令。宗座使徒女王大学按罗马标准来说是一所超现代机构,占地宽敞,位于梵蒂冈城西南几英里处。在那里,帕斯夸尔神父负责一个关于科学与信仰的项目。他告诉我,那里的一些学生参与了Geoastrolab项目,该项目涉及天文学、天体物理学和地理学研究。
“我认为教会并没有从事科学本身,”帕斯夸尔说,“教会正在做它的工作,其使命是主赐予的,即向人们传福音,并在历史的每一个时刻呈现福音。我们需要与当今文化中的人们交谈,而这些人深受科学教义的影响。”
STOQ项目的许多倡议都涉及让文化参与关于科学的对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行动可以被视为一项精明的公关举动,为圣座提供了一个将宗教问题注入科学话语的机会。但STOQ项目的存在是否对教会本身产生了任何影响?
“我不确定,”帕斯夸尔说,“我认为它不是那么直接和即时。但从广义上讲,因为我们正在培养教会未来的领导人,它将对教会产生真正的影响。”
谈话结束后,帕斯夸尔带我参观了大学主楼,并向我展示了一个关于科学和都灵裹尸布(the Shroud of Turin)的展览。他告诉我,最近的裹尸布取样显示它与以色列植物学相关,证实了裹尸布的起源。
“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在这里进行裹尸布研究,”帕斯夸尔告诉我,我能看出他对此前景感到兴奋。
角落里矗立着一尊令人印象深刻的等身裹尸布人物雕塑;远处的墙上是同一人物的罕见全息渲染图。人物的面孔引人注目,神秘而大胆,你禁不住会想,那是否真的是耶稣的容貌。这是许多教会谜团的完美例证,而科学正试图解开它们。
仰望星空 远离教会所面临的诸多科学谜团和争议,康索尔马尼奥修士领着我上上下下卡斯特尔甘多尔福教皇宫的螺旋楼梯,他一转弯就指着通往教皇私人住所的门,然后又指着一条简陋的走廊,那里是耶稣会士们宿舍式居住的地方。他告诉我,他工作最大的福利之一就是能吃到耶稣会社区厨师做的正宗意大利美食。然后他带我简要参观了他最引以为傲的成果——著名的梵蒂冈陨石收藏,那是来自世界各地经过精心分类的样品。
卡斯特尔甘多尔福感觉距离梵蒂冈城内学院庄严的环境遥远,仿佛相隔一个太阳系。成员们目前正忙着组织他们的下一次全体会议,“对宇宙和生命进化的科学见解”,定于下个月底举行。舍恩伯恩和霍金,以及马克斯汀·辛格都将发表演讲。这次活动无疑将加剧创世论和进化论之间本已激烈的辩论。卡斯特尔甘多尔福的天文台似乎不受整个事件的影响,我突然想到这种特权是有原因的。
我向康索尔马尼奥提出,梵蒂冈可能支持天文学研究,而非其他应用研究,仅仅因为这是一个相当安全的领域。天文学不必处理胚胎干细胞、人类克隆或事后避孕药(morning-after pills)等问题。教会必须就所有这些问题表明立场,每一个问题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但很少有神父会为太阳耀斑和超新星而失眠。康索尔马尼奥补充说,其他类型的科学家确实必须应对严重的伦理问题,例如他们是否应该从事原子物理领域的工作,因为那里的研究可能导致武器的进步。答案并不容易。
“所有这些事情都有后果,有些是意想不到的,比如给艾滋病患者分发避孕套,”他说。康索尔马尼奥靠在椅子上,在充满他办公室的柔和蓝色山光中悬浮了一会儿。他将注意力转向另一个空间,一个内在的宇宙,在那里停留了一会儿,然后他的目光回到了我身上。
“我很高兴我是一名天文学家,这就是我所有要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