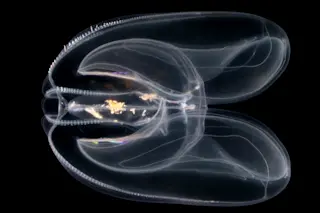重构史前人类遍布全球的事件,就像把一窝小狗放在一个篮子里一样。每次秩序似乎即将建立时,一些关键元素就会溜走。
潜在的混乱有不同的伪装。有时,一种新的实验室技术颠覆了传统观点,然后又被自身颠覆。有时,一个新的考古遗址动摇了旧的时间表,然后又无效地陷入了默默无闻。有时,来自其他学科的专家会审视这个问题,然后实际上说:抱歉打扰,但根据我们部门所知,你的解决方案不可能是正确的。
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事情都在过去十年中发生过。换个比喻,战火在各大洲熊熊燃烧。
对于旧世界的史前学家来说,过去五六年来的热度相当高。争议的焦点不是最早的人科动物是否在300万到400万年前在非洲进化:化石已经让这一点毋庸置疑。也没有人质疑这些人科动物的一个子集(以浓眉直立人的形式)在大约一百万年前离开了非洲;遍布旧世界的手斧和化石证明了他们的存在。谜团在于这些直立人种群是否繁衍了我们。也就是说,除非你问米尔福德·沃尔波夫。这没什么神秘的,密歇根大学的古人类学家高兴地说。这件事已经解决了。
他满意的背景如下。多年来,沃尔波夫一直在研究直立人,并确信——该领域许多其他人也如此——是直立人在温带地区建立了人类的滩头阵地,是直立人或多或少地繁衍了现代欧洲、中东和亚洲人口。
这种常识性的场景——欧洲直立人演变为现代欧洲人,亚洲直立人演变为现代亚洲人——在1987年受到了严重冲击。当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几位生物化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六页的论文,提出了“线粒体夏娃”现象,这篇论文突然彻底颠覆了旧世界的进化争论。由已故的艾伦·威尔逊领导的研究团队,其结论基于基因而非骨骼,并声称非洲不仅有一次,而是两次辐射。第一次确实是直立人,但那一次显然没有成功。重要的是第二次辐射——大约在20万年前;那些移民是我们的祖先。他们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取代了之前的居民,没有与他们异种交配,因此可以理所当然地声称自己是祖先。
转眼之间,“夏娃”成为了自“露西”——也就是南方古猿阿法种,我们有证据的最古老的直立人类祖先——以来最热门的新进化玩家,而直立人则沦为脚注。沃尔波夫深信化石记录不支持伯克利团队设想的古入侵,于是拿起武器,成为直立人的代言人,化石信仰的捍卫者。
伯克利生物学家们惊人的结论是基于对线粒体DNA的检查。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每个人的细胞都含有它们,每个线粒体都含有自己的DNA片段。然而,你的线粒体DNA(mtDNA)与你细胞核中的DNA在一个基本方面有所不同:你所有的mtDNA都来自你的母亲。当卵子受精时,精子的微小线粒体会被重吸收;因此,我们所有人——男性和女性——都只含有母系mtDNA。
由于线粒体DNA不发生混合,你与你的曾祖母之间的线粒体DNA差异,将是突变积累的结果。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所有生物体的线粒体DNA都以平均统计规律积累突变;这就是所谓的分子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你与你的远亲表兄弟姐妹之间的遗传距离——或者平均人类与平均黑猩猩之间的遗传距离——是衡量每对生物体多久以前共享一个共同祖先的指标。(在第一种情况下,四代;在第二种情况下,五百万年。)
伯克利小组检测了来自147名不同族裔女性的线粒体DNA,发现她们之间的变异出人意料地小——比分子钟在她们的非洲、亚洲和欧洲祖先自直立人时代以来相对隔离进化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变异要少得多。此外,看起来最古老——即广义上突变最多——的线粒体DNA来自非洲裔女性。根据对突变率的最佳估计,那个分支大约有20万年的历史。证毕:一小部分非洲人繁衍了所有现代人类。
随之而来的传统古人类学争论,伯克利研究人员积极为自己辩护,直到1992年初,似乎许多人类学家都已被说服。即使是那些明显不相信的人——比如米尔福德·沃尔波夫——也已心灰意冷。他说:“如果你在一年前问我,我会说这个争论永远无法解决。我以为它会一直是一团乱麻,我们永远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么这个人现在为什么面带笑容呢?因为他刚刚听了一场讲座,一位遗传学家——一位有能力在伯克利团队自己的学术领域与他们抗衡的实验室科学家——推翻了该团队的方法论。沃尔波夫咯咯笑着说:“在精心安排的一小时里,那家伙把夏娃假说支持者们说过的一切都彻底否定了。这个工作的影响力让我目瞪口呆。那家伙简直是颗定时炸弹。”
艾伦·坦普尔顿,华盛顿大学遗传学家,也就是那个“定时炸弹”,听起来并不像定时炸弹。他更像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科学家,尽管他给沃尔波夫及其同伴的化石研究带来了诸多慰藉,但他仍然对线粒体DNA的潜力充满热情。但他对精确的统计分析更加热情。他断言:“我认为线粒体DNA中包含大量信息,可以从中提取出许多具有生物学和统计学意义的数据。问题是,分析技术必须与数据一样优秀。”
在他看来,揭示夏娃的分析技术并非如此。首先,伯克利小组在使用计算机程序创建其遗传树的方式上存在问题。坦普尔顿说,根据数据引入的顺序,它可以生成数百万棵同样看似合理的树。程序的说明告诉你用随机顺序引入数据进行多次运行。威尔逊只运行了一次;或者正如沃尔波夫咆哮的那样,坦普尔顿只是阅读了他们程序随附的用户手册。当你正确运行时,就没有支持夏娃的证据。
还有更多。坦普尔顿天生比沃尔波夫谨慎,他煞费苦心地澄清,用于研究进化问题的统计学和数学本身正在不断发展,而他批评中使用的那些在“夏娃”首次亮相时尚未开发。然而,现在的底线是,这两种假说——非洲起源或不留俘虏的入侵——都不一定得到线粒体DNA的支持。
坦普尔顿认为,这些日期存在比伯克利科学家们所希望的更大的模糊性:事实上,差了一个数量级。他估计,我们有一个线粒体祖先,但她生活在十万到一百万年前的某个时期。他说:“伯克利小组一直承认存在误差范围。我只是找到了一个数学方法来确定这个范围有多大。”(沃尔波夫的说法一如既往地更直白:所以你有一个时钟,它能告诉你现在是凌晨4点还是中午。那有什么用?)
坦普尔顿所设想的既不涉及晚期从非洲爆发的辐射,也不涉及严格的局部进化,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人类可能确实从非洲迁移到旧世界的其他地方,并且在那里进化,但各大洲之间始终存在足够的接触来混淆线粒体。当然,这种接触是有限的。坦普尔顿强调说:“我并不是说欧洲人和亚洲人随机交配。但是,”他指出,“即使是一点点涓涓细流也能起到作用。看看大峡谷——只要时间足够,水就能侵蚀岩石。就人类世代而言,我们这里谈论的是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坦普尔顿并没有完全否定夏娃。我只是说我们不知道她住在哪里,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这在进化意义上并不那么相关。所有人类群体都作为一个单一实体进化,追溯到线粒体存在的时期。我们的基因是一个地理马赛克:即使我们的线粒体源自非洲,我们的血红蛋白基因[包含在核DNA中]可能来自亚洲祖先,或者我们的Y染色体来自欧洲。
为了进一步混淆祖先血统并挑战“夏娃”理论,去年六月,另一个研究小组公布了其对1989年和1990年在中国发现的两具头骨的研究结果。这些头骨显示出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的特征混合,这可能表明向现代人类的过渡在亚洲与非洲同时发生,从而为沃尔波夫阵营提供了支持。
正当旧世界的喧嚣争论持续不断时,在北美洲,另一只“小狗”正试图从篮子里挣脱出来。这与新的实验室技术无关。在北美洲,这位试图“逃跑”的,是一位语言学家,一位语言专家,他礼貌而坚定地表示,目前关于人类迁徙到北美洲的时间表是错误的:它短得令人绝望,短得不可能。
那个时间表是考古学中比较持久的现象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初放射性碳测年成为现实以来,它一直保持不变,反映了普遍的共识:现代人类在大约12,000年前通过现已淹没的白令陆桥进入新世界。这些西伯利亚移民及其后代被称为古印第安人,是几乎所有美洲原住民的祖先。
它通常被称为克洛维斯年代学,因为新墨西哥州的一个遗址首次发现了这些先驱者的石器。像20世纪50年代的许多现象一样,它正步入一个相当疲惫的中年。它不再令人兴奋,但也没有更好的东西来取代它。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最初令人兴奋的克洛维斯前期的主张都曾出现过,但最终都以壮观的方式失败了。例如,育空地区的一件骨器曾声称有27,000年的历史;当该工具重新测定年代时,却缩减到可怜的1,350年。加利福尼亚州的石头,曾被路易斯·利基赋予旧石器时代的认可,因为它们类似于古代非洲的砍砸工具;现在它们被认为是生态制品——自然断裂的石头。
尽管如此,新的竞争者仍在不断涌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竞赛中的遗址包括至少三个南美洲遗址,几个美国遗址,以及另一个育空地区遗址。最古老的声称年代是32,000年,位于巴西东北部的一个遗址,由法巴联合团队发掘。如果得到证实,在佩德拉富拉达岩石庇护所中发现的古老炉灶将使智人在新世界的存在时间几乎增加两倍。然而,一些考古学家质疑,那些得出年代的区域是否真的是炉灶,而不仅仅是自然烧焦的区域。
无论如何,考虑到克洛维斯周围略显陈旧的气氛,1986年,当体质人类学、遗传学和语言学三驾马车为旧的假说注入一剂急需的强心剂时,人们感到相当欣慰。体质人类学——对美洲印第安人、亚洲人和太平洋岛民的牙齿研究——指向了晚期殖民,可能分为三波。遗传学——对三组血型抗体类型的比较——证实了这一点。但吸引考古学家的,是三人组中的第三个成员——语言学。
语言学家一直对美洲原住民语言的非凡多样性感到困惑。例如,仅加利福尼亚沿海地区的土著语言就包含了十多种语言家族的代表(大致六倍长的北地中海沿岸,仅包含两种)。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描述了大约1000种不同的美洲原住民语言,自欧洲殖民以来,可能还有同样多的语言已经失传。
任何形式的复杂性都需要时间积累,语言复杂性也不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会演变为现代版本,或者像拉丁语一样,分支成几种不同的语言。北美语言难题的关键始终是:所有这些语言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发展起来,特别是如果它们像大多数专家认为的那样,至多只是远亲关系?
回答这个问题的克洛维斯友好型语言分类是由约瑟夫·格林伯格(一位来自斯坦福大学的非正统学者,他对非洲语言体系的排序曾获得普遍赞誉)提出的。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他说,所有这些语言都相关。格林伯格提出,第一批古印第安人,在12000年前穿越陆桥时,都说着一种共同的原始语言。
格林伯格使用他称之为“大规模比较”的技术,在尽可能多的已记录土著语言中寻找词汇类别(例如,水类别可能包括湖泊、池塘和沼泽)的相似之处。他在专家们没有找到的地方找到了它们,并在此基础上定义了北美洲的三大语言群体。(更传统的统计约为140个。)其中两个并不引人注目,一个包含9种语言,另一个包含34种语言,但第三个,称为“美洲印第安语”(Amerind),既庞大又具争议性。它包含了所有其他语言。
三大语系,三次殖民,12000年——所有碎片都吻合。140个不同的语系,140次不同的殖民——正如格林伯格本人所说,“那白令海峡就得有个交通管制员了。”
格林伯格的经济解决方案让大多数历史语言学家喘不过气来。他们认为,推断存在一个12000年前的共同祖先是可疑的。正统历史语言学家研究独立的语言,并比较构成各种语法类别(如格和时态)的各个组成部分。即使进行这种细致的研究,他们也无法重建8000年以前的原始语言。在那个时间深度,比较方法——一位语言学家称之为我们“闪烁的照亮过去的电筒”——无法区分因亲缘关系而产生的相似之处和因借用或偶然而产生的相似之处。
伯克利语言学家乔安娜·尼科尔斯登场。她不声称基于语言进化的年表能提供精确的数字——但如果她是对的,她说,克洛维斯年表完全错了。
尼科尔斯的方法既不同于大规模词汇比较,也不同于传统的历史方法。为了确定一组语言有多古老,她着眼于那些不随时间迅速变化或传播的整体语法类别——例如是否存在独立的主格和宾格,或者动词是放在句末还是句首。她坚持认为,这些相似性集合比词汇相似性更能衡量时间,因为它们不太可能被整体借用,或仅凭偶然在两组语言中达到相同的频率。根据这个标准,格林伯格的北美图景似乎不太可能。每一种可以想象的语言类型都得到了体现,这表明在12000年前存在亲缘关系的可能性很小。
然而,尼科尔斯最引人入胜的问题不是“多少?”,而是“多久?”语言能告诉我们美洲人类的古老程度吗?在她1990年发表的一篇让语言学界为之震惊的论文中,尼科尔斯认为语言演化出子语言的速度具有大致的时钟般的规律性。她将这一主张建立在语言史上:具体来说,是基于她对北半球现存和已灭绝的语言、语系以及重建的原始语言如何演变的调查。尼科尔斯观察到两件事:大多数语系会产生一到三种独立的子语言(平均语言出生率为每语系1.6种),而且它们大约每6000年发生一次。有了这两个数据点,尼科尔斯设计了一种方法,可以从北美语言大杂烩中提取出时间线。她实际上创建了一个“语言时钟”。
它的机制看似简单。尼科尔斯只是将140个不同的北美群体除以1.6;她说,这让她回溯了一个语言世代,即6000年,大约回到了88个祖先群体。再除一次,她就回到了12000年前,也就是克洛维斯年表的门槛,那里有55个不同的语系。她认为,这个日期是不合理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在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都没有证据表明语言家族数量所暗示的人口规模和社会复杂性。
另一方面,如果所有美洲原住民语言都源自一次单一迁徙带到美洲大陆的一种语言,那么“语言时钟”显示这一定发生在5万年前。尼科尔斯愉快地承认这个数字“不着边际”。她认为,更现实的观点是,在过去3万年左右的时间里,发生了多次(也许是十次)语言上独立的殖民。
然而,困惑依然存在。如果人类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而且数量相当可观,足以维持一种语言的生命,为什么早期的考古遗址却如此稀少且模棱两可?尼科尔斯坦白地说,她对此感到困惑。这非常——她徒劳地寻找最贴切的词——奇怪。语言证据非常清楚地指向一个漫长的历史深度,而公认的考古学却不支持这一点。她振作起来补充道:“我想,总有希望能够找到令人信服的考古证据。”
正如夏洛克·福尔摩斯曾说,当你排除了所有不可能的,那么剩下的,无论多么不可思议,就是真相。尼科尔斯深知她的结果令人不安,但她坚守自己的语法立场。她说:“确切的日期有问题,但语言学在大致范围上是绝对明确的。新世界已经有人居住了数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