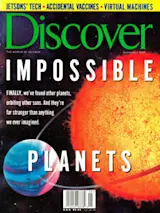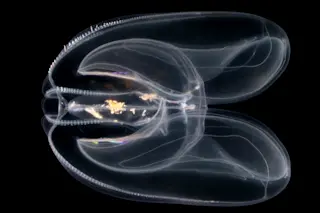爪哇岛是澳大利亚西北部一个人口稠密的巨大热带岛屿。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它只是咖啡的另一个代名词,但对于研究人类起源的科学家来说,爪哇岛更具丰富的启发性,因为它是19世纪90年代首次发现古代人类化石的地方。最近,其中一些布满灰尘的化石被从博物馆的架子上取下,一个多世纪后,再次成为头条新闻。测定化石年代的新技术表明,其中一些爪哇岛的遗骸比我们原先认为的要古老得多,而另一些则要年轻得多。这些新日期对我们所有关于人类进化的宏大理论都构成了挑战——尽管对某些理论而言,消息比其他理论更糟。
爪哇岛在古人类学中的故事可以追溯到1891年,当时一位名叫欧仁·杜波依斯(Eugène Dubois)的年轻荷兰军医在特里尼尔镇附近的一条爪哇河岸上发现了一块看起来像猿猴头骨的顶部。起初他以为自己发现了一只黑猩猩的化石。像黑猩猩一样,特里尼尔生物的脑壳很低,额头陡峭倾斜,眼眶上方有巨大的骨脊。但脑壳有点太大了,额头也有点太突出,不属于猿猴。
第二年,杜波依斯在他发现头盖骨的地方几码外挖出了一根看起来像人类的大腿骨。他将这两个标本放在一起,并宣布他发现了猿猴和人类之间缺失的环节:一种具有像我们一样长腿和直立步态,但大脑只比大猩猩大50%左右的灵长类动物。杜波依斯将他的生物命名为直立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意思是直立的猿人。
1931年,其他荷兰科学家回到该地区,在特里尼尔下游的昂东镇附近的一个遗址又发现了11个头骨。昂东头骨比特里尼尔头盖骨年轻,看起来也稍微不那么原始。尽管它们也有厚骨、大眉骨和后倾的额头,但它们的脑壳比特里尼尔大21%,平均约为1100立方厘米——这在今天正常人类的范围之内处于低端。
多年来,更多的直立猿人化石陆续出现。我们现在有十几具或多或少的残缺头骨,几块下颌骨,以及一些更小的碎片和松散的牙齿。它们出土的沉积物被测定为距今一百多万年前到大约七十万年前——大约在更新世中期(距今一百六十万年前到一万年前)。直立猿人头骨贯穿整个序列。它们多年来变化不大,尽管平均而言,更古老的头骨脑容量略小。
如今,人类学家认为直立猿人是我们自己属,即人属的一个物种。我们是智人,而直立猿人现在是直立人。专家们争论昂东头骨属于哪个物种;他们甚至更激烈地争论这两个物种之间的确切关系。从杜波依斯时代至今,许多科学家都将直立人视为我们的直系祖先。另一些人则将其斥为仅仅是一个发育迟缓的表亲,并寻找更古老、脑容量更大的人类,将其置于人类家谱的底部。
现如今,关于人类起源的基本事实已基本达成共识。大约250万年前在非洲,人属从脑容量较小、两足行走的猿人(被称为南方古猿)中进化而来。非洲也在大约同一时期首次出现了石器,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两个事件之间存在关联。早期人属可能有两个物种——鲁道夫人和能人。前者比南方古猿脑容量更大;后者臼齿较小。这些先进的特征表明,一个或两个早期人属物种正在制造那些工具,因为工具制造需要大脑,而使用工具可以减轻牙齿的一些负担。
到190万年前,这两种物种在非洲又增加了一个:我们的老朋友爪哇直立人。这个新来的物种具有完全人类的体型,相对长的腿和短臂使其看起来比以前的人科动物更不像猿。直立人的脑容量也更大——大约900立方厘米,而早期人属的脑容量为600到700立方厘米。但它的头骨却出奇地粗野,脑壳壁增厚,眉脊巨大,并有强壮颈部肌肉的证据。总而言之,直立人符合没有下巴、头颅厚实、眉毛粗重、脖子粗壮的穴居人的熟悉刻板印象。对于早期的类人猿来说,它一定是一个可怕的竞争者,这些类人猿在直立人出现后约30万年就消失了。
在竞争者灭绝之后,非洲直立人取得了两个重要突破。一个是一种新型的石器技术。早期的工具制造者只是将几块鹅卵石敲击在一起,得到一个短而粗糙的边缘。而新工具的制作更加经济和巧妙,通过从大石头上剥离出大的扁平石片,然后对分离出的石片进行再加工,从而获得一个四周锋利的边缘。
另一个突破是走出非洲。到一百万年前,直立人已抵达中国和亚洲格鲁吉亚。到五十万年前,类直立人种群遍布旧世界,从德国到远东,一直延伸到非洲。这些生物是原始直立人的改进版,拥有扩大的1200立方厘米的脑容量,但额头依然低平,头骨依然厚重。一些人称这种新的改进模型为古智人。另一些人则称之为先进直立人,还有一些人将其归为一个独立的物种——海德堡人。在欧洲,这种中间类型似乎进化成了独具特色、脑容量更大的尼安德特人。我们自己的现代智人,拥有合适的额头和突出的下巴,最早的化石出现在中东,大约在9万年前。
所有专家都同意这个故事的基本内容。但他们对这一切的意义却存在分歧。对化石最简单的解释是,从非洲到爪哇的所有直立人种群作为一个整体共同进化成了现代智人。根据这种所谓的区域连续性解释,智人和直立人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而海德堡人只是这个进化过程中间种群的一个模糊标签。
另一种主要的解释是“走出非洲”理论,它将人类进化视为一系列从非洲发出的两到三波进步浪潮。在这种观点下,直立人种群被海德堡人种群取代,其中包括他们在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分支。所有这些又依次被一波完全现代的智人所取代——旧的原住民和新移民之间没有杂交。
“走出非洲”理论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能可靠地区分所有这些所谓的物种——直立人、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和智人。有许多化石介于它们之间,没有两位专家能就一个物种在哪里结束、另一个物种在哪里开始达成一致。但该理论也有其有利的事实。几条证据链表明,今天人类种群之间的遗传差异可以追溯到不超过20万年前。许多遗传学家认为,他们的数据不符合直立人在整个旧世界逐渐进化为智人,长达百万年的图景。对这些研究人员来说,遗传事实表明,现代人口(或至少是现代基因)是最近从一个单一中心传播开来的,正如“走出非洲”模型所描述的那样。
关于“走出非洲”理论的一个古生物学证据是,一些古人类种群似乎在更现代的人类出现后依然存在了一段时间——这意味着这两种类型没有杂交,因此必然属于不同的物种。这又把我们带回到爪哇的新测年结果。
确定爪哇化石的年代一直是个问题。早期的大部分发现都是由当地工人挖掘出来的,他们每发现一块化石都会得到报酬,因此有经济动机隐瞒他们找到“金矿”的确切地点。结果,早期发现的化石都无法精确地放置在当地的地层学中。即使知道爪哇化石的确切来源,也不能保证其年代。当河流穿过古老的沉积物时,从河岸剥蚀出的化石会沿着斜坡滚落,掉入河中,然后重新埋藏在新沉积物中。如果你根据这些新鲜沉积物测定它们的年代,你就会低估它们的年代。所有爪哇化石都来自河岸沉积物,其中许多看起来像是被流动河流冲刷了一段时间。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它们最初可能被埋藏和石化在比发现它们的沉积物更古老的沉积物中。
1971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加尼斯·柯蒂斯(Garniss Curtis)对爪哇岛最古老的直立猿人化石之一,即来自莫佐克尔托遗址的一名儿童头骨周围发现的一些火山矿物进行了测年。他分析了岩石中的钾随时间转化为氩的情况,得出了一个惊人的古老年代——大约190万年前。1992年,柯蒂斯和他的同事卡尔·斯威舍(Carl Swisher)采用了一种更复杂的技术,对头骨内部的矿物进行测年,得出的年代为180万年前。
这些年代比大多数专家预期的要早近一百万年。如果新年代是正确的,那么直立人出现在爪哇的化石记录中,大约与它首次出现在非洲的时间相同。这很难与我们关于早期人类进化的任何理论相符。如果直立人在非洲进化,为什么它在爪哇出现之前没有在非洲出现?如果直立人在非洲和爪哇之间的某个地方进化,并从那里传播到非洲和爪哇,都在190万年前,那么为什么在非洲以外没有发现任何更早的原始人类化石?
投下莫佐克尔托重磅炸弹后,柯蒂斯和斯威舍回到爪哇化石记录的另一端,即那些较晚但仍具原始特征的昂东头骨。(昂东沉积物不含氩测年所需的火山矿物,因此研究人员使用了其他技术。埋藏的牙齿会从地下水中吸收铀盐,通过测量牙釉质中铀与其裂变产物的比例,可以估算出牙齿被埋藏了多久。)他们对这些化石获得的年代估计范围从5.6万年前到仅2.1万年前。
这些日期令人震惊地晚。到两万年前,尼安德特人早已消失,世界各地的人类基本上与今天的人们没有什么区别。到一万年前,中东和东南亚的人们已经开始尝试农业。但如果昂东的新日期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孤独幸存的落后、斜额生物群体(大多数专家称之为直立人)在爪哇岛,在最后的大陆冰川融化、其他所有人都抬起额头并在洞穴墙壁上作画很久之后,仍然过着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生活。像爪哇岛的其他日期一样,这些新日期也受到各种质疑;但如果柯蒂斯和斯威舍是正确的,这对区域连续性理论是一个打击。
这个打击不一定是毁灭性的。更新世爪哇岛可能是一个被时间遗忘的土地:一个原始的孤立区域,早期被殖民,然后被切断了所有持续将其他直立人转变为现代智人的基因流。认为爪哇岛可能是一个特殊偏僻地区的原因之一是,直立人沉积物中几乎没有石器。在世界其他地方,我们发现人属化石的地方,伴随它们的石器数量远超化石。但与爪哇直立人一起发现的唯一工具是一些可疑的石片和锤石。一些科学家认为,直立人在爪哇不需要石器,因为他们可以用竹子的燧石茎制作他们需要的所有刀、矛和刮刀。但他们用什么来切割竹子呢?
为什么人类学家对这些问题如此兴奋?我们为什么要关心我们是晚期幸存的古人类的后代,还是生活在更早、其他地方的同样原始类型?围绕这些问题的吸引力部分来自于科学自我的冲突,部分来自于对遥远年代和遥远地方故事的纯粹迷恋。但它也源于科学种族主义漫长而肮脏的历史。
对人类进化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了种族政治的污染。19世纪末,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欧洲人似乎很清楚,白人之所以能主宰世界,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优秀。自然而然地,达尔文主义者将此视为适者生存。许多科学家将殖民非洲、澳大利亚和新世界的原住民视为活化石:人类进化早期阶段的遗存,注定要像塔斯马尼亚狼和塔斯马尼亚土著一样,在自然界残酷的竞争法则下走向灭绝。
这种种族主义思想很容易反过来应用于化石。如果塔斯马尼亚原住民因为过于低级和原始而无法竞争而被灭绝,那么像直立猿人这样更低级、更原始的已灭绝形式也一定是因为无法竞争而被消灭。而消灭他们的人一定是现代人类的祖先。因此,我们不可能是直立猿人的后代。没有人如此赤裸裸地阐述这个论点,但很多专家都有类似的想法。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关于人类进化的主要教科书几乎都将更新世的所有人类化石描绘成注定灭绝的、偏离主流(白人欧洲)人类谱系的死胡同分支。一些人将人类进化树描绘成杉树状,一个粗壮的中央树干通向欧洲人,然后是许多大多已灭绝的侧枝:首先是直立猿人(灭绝了),然后是尼安德特人(灭绝了),然后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和非洲人,他们尚未灭绝——但还没有。
二战结束后,在纳粹恐怖的余波中,人类学家们急于抛弃所有关于种族等级的观念。欧洲在非洲和亚洲的帝国瓦解也帮助治愈了白人科学家将自己视为主导种族的旧习惯。到1960年,没有一位有声望的人类学家还在谈论进化地位上的种族差异。
对化石记录的旧等级解释——以及其中隐含的史前大屠杀——也被抛弃了。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将任何化石人类排除在我们的祖先之外被视为带有一丝种族主义色彩。所有的分类之门都敞开了。南方古猿加入了人类家族,直立人被纳入人属,而尼安德特人则被认为是现代智人的一种极端种族变体。如果低眉的尼安德特人是今天欧洲人的祖先和同等地位者,那么将非洲、澳大利亚或美洲的高眉现代原住民划分为较低地位的想法就显得荒谬了。科学种族主义似乎已成为过去。
并非如此。在1962年出版的《种族起源》一书中,美国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Carleton Coon)突然出现,将所有这些蓬勃发展的平等主义颠覆了。库恩接受了区域连续性理论,并同意所有直立人化石都是我们的祖先。但他通过篡改日期和分类法,认为从直立人到智人的转变在不同种族身上发生在不同的时间。不出所料,他认为白人首先实现了智人化,然后是东方人(可能通过欧洲的基因流),最后是非洲人和位于欧亚大陆边缘的澳大利亚人,他们是最后完全成为人类的群体。库恩暗示,与白人和亚洲人相比,这些深色皮肤的后来者仍然有些迟钝。他的书收录了并列的照片,一张是小头颅的澳大利亚土著妇女,另一张是圆顶的中国圣贤,配文是“智人的阿尔法和欧米伽”。
库恩的书引起了激烈的争议。许多人类学家对他的模型中隐含的种族等级制度感到沮丧,将其视为理论上的不可能。他们坚持认为,一个单一的杂交种群不能在一端属于一个物种,而在另一端属于另一个物种。(事实上,在一些鸟类、蝾螈和其他动物物种中,已经描述了这种安排的几个例子,尽管科学家们对这些描述的真实性存在争议。)关于库恩著作争议的结果是,一些人类学家开始将整个人类起源的区域连续性模型视为一种受种族主义玷污的理论。
出于这个原因,一些化石专家将“走出非洲”理论的每一条证据都视为现代人类平等的进一步证明。(如果我们都起源于10万年前的非洲夏娃,那么我们彼此之间就不会有太大差异,不是吗?)另一些人则将区域连续性模型,以及其长达数百万年的人类种群之间基因流动的模式,视为反对种族类型学的堡垒。我们中的一些人,在六十年代接受训练,脑子里还存着那些旧的种族分化树状图,仍然有一种模糊的感觉,真正的平等主义者不应该歧视尼安德特人。(如果尼安德特人是完全的人类,那么现代种族之间的差异就微不足道,不值得在意,不是吗?)这场辩论可能比它需要的更激烈,因为双方的拥护者都认为自己在捍卫人类大家庭的团结和平等,抵御对立阵营的攻击。
关于爪哇岛的那些年代,科学界仍在争论不休。但在我们等待新证据的同时,我们最好记住,今天人类的平等并非真正危在旦夕。我们就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我们的祖先。如果我的祖母是A型血,这并不意味着我也有A型血,甚至不意味着我携带了A血型的基因。即使我3万年前的曾曾……祖父是尼安德特人,那也不会改变我额头倾斜度一丝一毫,也不会暗示我携带着尼安德特人血液的某种污点。种族平等主义的真相取决于活人的事实。他们的谱系无关紧要。
理解这些简单的真相或许有助于缓解许多人对人类进化所感到的不安。这种不安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错误的观念,即在所有文化表象之下,我们骨子里仍然是我们的祖先——如果我们是猿猴的后代,我们就一定以某种方式是猿猴,并且可以在我们愿意的时候像猿猴一样行事。我们不是,我们也没有。知道我们从何而来并不能告诉我们现在身在何处。如果我们都能接受这个原则,它可能会有助于使未来关于人类起源的辩论减少激烈,增加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