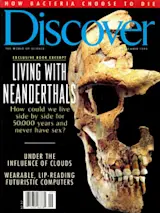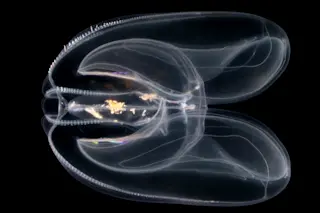我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遇到了我的第一个尼安德特人,就在儒西约地铁站对面。那是一个潮湿的五月下午,我背靠着窗户坐在卡座上。咖啡馆烟雾缭绕,毫无情调。靠近入口处,两个学生正在玩一台名为“创世纪”的弹珠游戏,每次得分都会发出提示音。店内挤满了人——外国学生、教授、年轻的专业人士、法国工人、阿拉伯人、非洲人,甚至还有几对日本游客,他们都被这场雨聚集到了一起。咖啡刚送上来,我发现当我端起杯子时,如果把肘部收紧,就不会碰到旁边桌子上一位正争论得不亦乐乎的胡子男人的肋骨。
在弹珠游戏的喧嚣声和窃窃私语声的上方,一位名叫让-雅克·胡布林的法国人类学家正在向我讲述人类的解剖学统一性。是他带来了那个尼安德特人。当我们走进咖啡馆时,他把一个用软布包裹的物体放在桌上,然后就再也没管过它。像任何被小心翼翼忽视的东西一样,它开始吸引我的全部注意力。
“也许你会对这个感兴趣,”他终于说道,迅速地拿走了布。在那里,在浓缩咖啡杯和空糖包装纸的杂乱之中,是一个巨大的人类下颌骨。牙齿磨损,因岁月而泛黄,都还在原位。我感觉周围的咖啡馆都集体挑起了眉毛。谈话声明显沉寂下来。旁边的胡子男停下了话语,看了看下颌骨,看了看胡布林,然后继续了他的争论。胡布林轻轻地将化石推到桌子中央,然后靠了回去。
“这是什么?”我问。
“这是来自西班牙南部一个叫扎法拉亚的遗址的尼安德特人,”他说。“我们只有这块下颌骨和一个单独的股骨。但正如你所见,下颌骨几乎是完整的。我们还不确定,但这块化石可能只有三万年的历史。”
三万年或许听起来是一种奇怪的时间表达方式,但对于一位古人类学家来说,这就像说一个职业篮球运动员只有六英尺四英寸高。人类——我们人类家族树的成员——至少已经存在于地球上四百万年了。与我们谱系的最早成员相比,桌上这块矿化骨头就像一个哇哇大哭的新生儿。即使与同类相比,这块下颌骨也年轻得惊人。尼安德特人本应在这个个体出生前五千年就已完全消失,而我来法国就是为了弄清楚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尼安德特人是我们所有人类祖先中最广为人知却又最少被理解的。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名字立刻会让人联想到一个笨拙的野蛮人的形象,粗暴地抓住他伴侣的头发拖着走。这种刻板印象,几乎在我们上个世纪中期在德国一个洞穴里发现第一具骨骼时就已形成,在漫画书、小说和电影中被反复添油加醋,以至于它已经从陈词滥调变成了普通话语。但真正让一个尼安德特人成为尼安德特人的,并不是他的体型、力量或智力水平,而是一系列极其独特的外形特征,其中大部分位于面部和颅骨。例如,与所有尼安德特人下颌骨一样,桌上的这个缺少下颌骨边缘的骨性突起,被称为“精神隆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下巴。下颌骨外侧用于附着咀嚼肌的区域异常增大,表明咬合力非常强劲。在最后两颗臼齿和下颌骨后部向上翘起的部分之间,胡布林指出了近四分之一英寸的间隙,这是一个精巧的结构,将咀嚼功能移到了更靠前的位置。
在这个以及其他几个特征上,这个下颌骨是独一无二、典型的尼安德特人;没有其他任何人类家族成员,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表现出相同的模式。经过一点指导,即使是我这样的外行人也能认出尼安德特人的模式。但与胡布林不同,他的专业知识让他能平静地坐着喝咖啡,而一个三万岁的男人的下颌骨就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我却觉得应该弯下腰表示敬意。
几年前,根据从现代人类细胞线粒体中发现的 DNA 进行的比较,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个生物化学家团队得出结论,地球上所有人类都可以追溯到大约二十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位女性。人类家族树的每一片活着的枝叶都从这位线粒体夏娃那里萌发,像葛藤一样蔓延到全球,将所有人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对我来说,夏娃的假说听起来好得不真实。如果所有现存人类都可以追溯到仅仅二十万年前的一个共同祖先,那么尽管文化和种族有令人困惑的装饰,地球上整个人口实际上就是一家人。因此,在一个五月的巴黎下午,一家咖啡馆可以接待来自三大洲或四大洲的顾客,但这个场景仍然相当于一次临时性的家庭聚会。
但夏娃也带来了更黑暗的消息。伯克利的研究表明,在大约十万到五万年前的某个时候,来自非洲的人们开始分散到欧洲和亚洲,最终也定居了美洲。这些人,也只有他们,成为了所有未来人类世代的祖先。然而,当他们到达欧亚大陆时,那里已经生活着数千,甚至数百万的其他人类——包括尼安德特人。他们都怎么样了?夏娃的答案是残酷而明确的:尼安德特人——包括桌上那块下颌骨所代表的扎法拉亚人口——被新来的南方移民挤到一边,被竞争淘汰,或者以其他方式灭绝了。
尼安德特人的命运让我着迷,在于他们那似乎注定的希望所产生的悖论。尼安德特人大约在十五万年前首次出现在欧洲,他们在日益寒冷的冰河时代茁壮成长;到七万年前,他们已经遍布欧洲和西亚。至于尼安德特人的外貌,肌肉发达的恶棍的刻板印象并非完全错误。体格健壮、胸部宽阔的健康成年尼安德特男性可以将一名普通的NFL线卫扛起扔过球门。但是,尽管尼安德特人以愚蠢而闻名,他们的大脑除了平均体积略大于现代人类外,并没有什么明显区别。我们无从得知那些大脑所思考的思想,因此也不知道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像我们自己的。但是一个大脑袋是昂贵的适应性装备。如果你不用它,你也不会进化出它。结合巨大的体力和显而易见的智力,尼安德特人似乎已经装备好应对环境能施加的任何障碍。他们不可能输!
然后,不知何故,他们输了。就在尼安德特人达到最先进的阶段时,他们突然消失了。他们的灭亡离奇地与一种新型人类的到来同时发生:更高、更瘦、更现代。这两个人类种群的碰撞——我们和另一个,注定的暴发户和大陆注定的看守者——是人类故事中和之后发生的任何事情一样强有力而奇妙的一部分。
我面前桌子上的半块下颌骨本身就有自己的故事。胡布林说它可能年轻到只有三万年。几个月前,一位名叫詹姆斯·比肖夫的美国考古学家和他的同事也公布了西班牙洞穴中一些文物的惊人年代。在应用一种新技术对一些现代人类风格的文物进行测年后,他们宣布这些文物的年代为四万年前。这比现代人类本应出现在欧洲的时间早了六千年。如果比肖夫和胡布林的年代都对,那就意味着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在西班牙共享这片土地长达一万年。我无法理解。
“如果年代是三万年,”我问胡布林,“这块下颌骨会不会是已知最晚的尼安德特人?”
“如果我们的年代是正确的,是的,”他说。“但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才能确定这块下颌骨的确切年龄。”
“但比肖夫说现代人类在一万年前就已在西班牙,”我坚持道。“我能理解一个拥有先进技术的族群进入一个地区,并迅速统治那里不那么先进的人群。但在演化意义上,一万年听起来一点也不快。两种人类怎么可能在那么长时间内并存而不分享他们的文化?不分享他们的基因?”
胡布林以经典的、神秘的法国式耸肩回应,意思是“答案显而易见”或者“我怎么知道?”
在人类演化的所有事件和转变中,现代人类的起源直到最近才最容易解释。大约三万五千年前,欧洲出现了一种新的、极具活力的文化,标志着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开始。这包括由骨头、鹿角和石头制成的各种高度复杂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制造这些工具的人——通常被称为克罗马农人,这个名字来源于1868年在法国南部发现他们的骨骼的一个极小的岩石庇护所——已经发现了象征性的存在层面,这从他们华丽的洞穴壁画、雕刻的动物雕像以及装饰他们身体的珠子和坠饰中可以看出。数万年前就居住在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从未制造出任何与之相提并论的复杂物品。伴随这种文化爆炸出现的是区分现代人类的解剖学特征的早期迹象:清晰的下巴;垂直的前额,没有明显的眉脊;圆顶的脑壳;以及细长、轻巧的体格,以及其他更深奥的特征。
克罗马农人洞穴中的骨骼,被认为有三万两千到三万年的历史,提供了文化和解剖学共同出现的精美微观模型。发现了五具骨骼,包括一具婴儿的,它们被埋在一个集体墓穴中,并且都表现出现代人类的解剖学特征。散落在墓穴里的有数百颗人工穿孔的贝壳和动物牙齿,显然是项链、手镯和其他身体装饰品的遗迹。现代文化和现代解剖学的几乎同时出现,为人类旅程的最后一步提供了现成的解释。由于它们同时发生,所以推断显而易见,一种必然导致了另一种。这一切都符合达尔文主义的逻辑。一种更高效的技术出现,取代了以前由蛮力提供的生存角色,从而减轻了对尼安德特人强健体魄和强大咀嚼器官的需求。瞧。突然之间,出现了聪明、瘦削的克罗马农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居然是欧洲本土的,这进一步加强了演化叙事:现代人类恰好出现在欧洲——根据欧洲人的说法——后来文化达到顶峰的地区。史前预示着历史。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克罗马农人是从别处来的,还是尼安德特人演变成了他们。
后者自然假设现代人类和尼安德特人没有共存,至少没有共存很长一段时间。但扎法拉亚的下颌骨挑战了这种简洁的假设。中东地区一些奇怪的发现更是具有破坏性。那里的最新发现也表明,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可能在同一片土地上,在同一时间,并且比在西班牙的时间长得多,长得多。
在以色列,尼安德特人分布区的南缘,一片林木茂盛的石灰岩地从海法下方地中海 abruptly 升起,形成起伏的山丘。这就是《所罗门之歌》中的迦密山,以利亚在那里击败了巴力的假祭司,黛博拉在那里击溃了迦南人。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军队、部落和整个文化穿越了它的岩石通道和肥沃的山坡,带来了赫梯人、波斯人、犹太人、罗马人、蒙古人、穆斯林、十字军、土耳其人,以及现代欧洲人的干预——一个民族被下一个民族屠杀或吞噬,但又不知何故再次崛起,并获得足够的力量去屠杀或吞噬他人。
我在这里的兴趣在于更古老的冲突。迦密山位于黎凡特,是海洋和沙漠之间一片狭小的宜居区域,连接着非洲和欧亚两大洲。一百万年前,大量的哺乳动物从非洲向北迁徙,穿过黎凡特进入温带地区。这些哺乳动物中包括一些早期人类。时间流逝。人类演化,多样化。生活在欧洲的那些人与留在非洲的、现在已遥远的亲戚变得截然不同。欧洲人变成了尼安德特人。然后,甚至在历史用围攻和屠杀开始侵蚀黎凡特之前很久,一些来自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和来自非洲的其他人类就 wandered 到这片连接他们故乡的通道,将他们的骨骼留在了迦密山上。他们相遇时发生了什么?两种人类如何回应对方?
前往以色列的石器时代很简单;我只需在特拉维夫租一辆车,沿着沿海公路开两个小时。我的目的地是凯巴拉洞穴,一个坐落在香蕉种植园上方、位于山脉风化西坡的考古发掘地。
走进洞穴,现代中东地区及其所有政治复杂性都消失了——这里只有一种凉爽、遮蔽的空旷,被数十年的考古勘探大大扩展了。散落在发掘地的是十几名科学家和学生;同样数量的人在入口处桌子旁工作。气氛是一种肃穆的、近乎僧侣般的专注,如同宏伟图书馆的阅览室。
凯巴拉的发掘始于十年前,接续了希伯来大学的 Moshe Stekelis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期的工作。Stekelis 揭示了一系列旧石器时代的沉积物,并在他突然去世前,发现了一具尼安德特婴儿的骨骼。1983 年,一个更大的宝藏出现了。在 Stekelis 去世后,发掘地的陡峭垂直剖面在几代年轻人和各种其他缓慢的侵蚀下崩塌了。一位名叫 Lynne Schepartz 的研究生被分配了清理恶化暴露区域的任务,就是将它们挖得更深一点。一天下午,她注意到一块似乎是人类脚趾骨的物体从一块粘合的沉积物中探出头来。第二天早上,她的扫帚露出了一排珍珠般的人类牙齿:一具成年尼安德特人骨骼的下颌骨。Stekelis 的团队只差了二英寸。
Lynne Schepartz 已不再是研究生,但她仍然在夏天去凯巴拉。我找到了她,问她发现化石是什么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她说。“我跳上跳下地尖叫。”
她有理由发出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反应。她的发现不仅仅是一具普通的尼安德特人,而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骨骼:第一具完整的尼安德特人脊柱,第一具完整的尼安德特人胸腔,以及已知最早的古人类的第一个完整骨盆。她给我看了化石的石膏模型——它被亲切地称为 Moshe——放在旁边的桌子上。骨骼按照发现时的原样摆放。Moshe 仰卧着,右臂叠放在胸前,左手放在腹部,呈经典的埋葬姿势。唯一缺失的部分是右腿、左腿的末端,以及除了下颌骨之外的头骨。
Schepartz 带领我通过梯子下到 Moshe 的埋葬地点,那是发掘地中心附近的一个深邃的长方形坑。在这个七月的早晨,这个尼安德特人的墓穴里住着一个名叫 Ofer Bar-Yosef 的现代人,他透过厚厚的眼镜看着我,让我感觉自己打扰了一位洞居霍比特人的快乐劳作。他似乎已经进化到适合这项任务,敏捷而矮小,更能适应狭窄的空间。
Bar-Yosef 告诉我,他 11 岁时就指导了他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在耶路撒冷附近的街区召集了一群朋友,帮助他挖掘拜占庭时期的水利系统。从那时起,他就没停止过挖掘。凯巴拉是他在任的第三次重大发掘。“我的女儿自从还是胎儿时就来这里了,”他告诉我。“她以前就在那里搭了一个游戏围栏。”
在 Bar-Yosef 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在挖掘以解答两个个人痴迷的问题:新石器时代农业社会的起源——这是我们痴迷的交汇点——以及现代人类起源的复杂难题。
黎凡特的故事从未真正说得通。在过去,当每个人都知道现代人类首先出现在欧洲时,那个真正现代的人们至今仍居住在那里,你可以通过他们留下的工具来辨认一个古人类。笨重的尼安德特人制造笨重的石片,而苗条的克罗马农人制造纤细的石刃。事实上,狭窄是石刃的定义,在古人类学中,它仅仅指一块长度是宽度两倍的石器。在欧洲,一种新的、高效的从燧石核上生产石刃的方法,作为文化爆炸的一部分出现,这与克罗马农人的出现同时发生。然而,在这个地区,解剖学上现代人类的到来并没有伴随什么新奇的工具,更不用说彩绘的洞穴、珠串项链或其他克罗马农人服饰爆炸的证据了。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古人类身体上的现代程度,并不能说明他行为上的现代程度。
从凯巴拉洞穴沿着海岸公路搭乘几站巴士就到了塔布恩洞穴,那里有超过 80 英尺的沉积物,跨越了超过 10 万年的古人类活动。塔布恩洞穴的宝藏,就像凯巴拉洞穴一样,都是尼安德特人。在塔布恩洞穴旁边拐个弯,是另一个叫做斯赫尔的洞穴,那里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发现了一些相当现代的人类。在凯巴拉洞穴几英里以外的加利利低地的一个小山丘上,是卡夫泽赫,1965 年,一位名叫 Bernard Vandermeersch 的年轻法国人类学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真正的中更新世现代人类墓地。但尽管这些洞穴中的骨骼既有尼安德特人,也有现代人类,但与骨骼一起发现的工具却几乎完全相同。
1982 年,亚利桑那大学的 Arthur Jelinek 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尝试,试图解释迦密山的困扰性悖论。他认为,就像后来欧洲一样,工具随着制造它们的人的身体而变薄。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变薄是从前到后,而不是从边到边。
他指出,最厚的石片来自塔布恩洞穴底部附近的一层,那里发现了一具尼安德特女性的部分骨骼;如果石片厚度确实是衡量时间的一个真实指标,那么她就是这群人中最年长的。其次年长的将是 Stekelis 在凯巴拉发现的尼安德特婴儿。斯赫尔的现代人类遗留了更扁平的石片工具。而最扁平的是卡夫泽赫洞穴的现代人类。尽管在身体上现代的斯赫尔-卡夫泽赫人可能还没有达到完全的、以石刃为基础的人类水平,但正如 Jelinek 所写,他们似乎“正处于突破的边缘”。
“我们目前从塔布恩洞穴获得的证据表明,在黎凡特南部,工业有序而连续地发展,”他继续说道。“这伴随着从尼安德特人到现代人的形态演变。根据这个情景,尼安德特人只是演变成了现代人类。没有民族或文化的冲突;两种人类从未相遇,因为实际上只有一种,随着时间而改变。”
如果 Jelinek 基于工具形态变薄的传统年代学是正确的,那么在卡夫泽赫发现的化石可能是克罗马农人的前身,是连接尼安德特人过去和克罗马农人未来——以及至现在——的演化环节。但 Jelinek 使用的测年方法是相对的,仅仅根据骨骼在整体年代顺序中的位置来推断其年龄。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时间测量方法,最好是一种绝对测年技术,能够以实际日历年标记迦密山的古人类。
最著名的绝对测年方法是放射性碳定年法,它通过放射性碳原子恒定、稳定的衰减来测量时间。放射性碳定年法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一直是最准确的地点定年方法之一,只要该地点比大约 4 万年前年轻。在更老的材料中,剩余未衰变的放射性碳的量非常少,以至于任何轻微的污染都会导致高度不准确的结果。另一种技术,依赖于放射性钾的衰变而不是碳,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来一直用于测定半百万年前的火山沉积物。放射性钾是测定著名的东非早期人类(如露西)以及 1994 年宣布的新根人类——普罗孔齿龙——的首选方法。然而,直到最近,这两种技术范围之间的所有生物——包括卡夫泽赫的现代人以及凯巴拉的尼安德特人——都陷入了年代学的黑洞。
然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法国考古学家 Hélène Valladas 使用一种名为热释光(TL)的新技术,对凯巴拉和卡夫泽赫洞穴的燧石进行了测年。这项技术之所以适用于这些燧石,是因为矿物质在加热到约 900 度时会发出光芒。它还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过去的や当代人类有时是粗心的。在中更新世,一些燧石工具偶然被粗心的脚踢到了火中,为绝对测年打开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当一块燧石工具被火充分加热时,它会释放出其热释光能量。经过数千年,该能量会再次缓慢积累。因此,原则上,对火烧工具进行测年很简单:今天加热时一块燧石发出的光越亮,它上次被使用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就越长。
到 1987 年,Valladas 和她的物理学家父亲 Georges 从凯巴拉 Moshe 附近发现的火烧工具中提取出了 6 万年的年代。这个数字让所有人都满意,因为它与通过相对测年方法得出的时间表一致。令人震惊的是,第二年 Valladas 和她的同事们公布了他们在卡夫泽赫的研究结果:那些现代人的骨骼有九万两千年的历史,误差几千。
此后,又有几处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遗址用 TL 技术进行了测年,而卡夫泽赫遗址至今仍是最轰动且最确凿的。黎凡特地区的一些关键遗址也通过一种姐妹技术——电子自旋共振(ESR)——进行了测年。在卡夫泽赫骨骼附近发现的大型哺乳动物牙齿的 ESR 年代甚至比 Valladas 的热释光测年结果还要早。这些骨骼至少有 10 万年,可能高达 11.5 万年。“人们说 TL 存在太多不确定性,” Bernard Vandermeersch 告诉我。“所以我们给了他们 ESR。现在很难争辩说,黎凡特地区最早的现代人类在 10 万年前就已在此居住。”
显然,如果现代人类早在尼安德特人之前 4 万年就已居住在黎凡特,那么他们就不可能从尼安德特人演化而来。如果这些年代确实是正确的,那么很难看到除了彻底抛弃我们对尼安德特祖先的崇敬信仰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解释。
案件是否已经了结?恰恰相反,这些年代只会让迦密山的谜团更加扑朔迷离。假设现代人并非仅仅在 10 万年前来此拜访然后礼貌地离开,那么当 4 万年后尼安德特人(如果尼安德特人也并非一开始就在那里的话)到达时,他们就一定在那里了——对塔布恩尼安德特女性的最新 ESR 年代将其置于 11 万年前。无论如何,两种不同的人类显然被挤压在一个面积不过相当于新泽西州大小的区域里,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至少 2.5 万年,甚至可能 5 万年或更长。
新的测年技术并没有解决这个悖论,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它的谜团。如果两种人类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以同样的方式行事,我们怎么能称它们为不同呢?如果现代人类并非起源于尼安德特人,而是取而代之,那么他们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完成这项任务?
在凯巴拉,我带着这个悖论来到外面,在一个宁静的夏日午后,地平线上勾勒出一艘远海油轮的轮廓,象征着当下。如果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这两个名字具有有意义的区别,如果它们具有与地平线上那艘油轮相同的现实性,那么它们就无法混合,就像海水和天空无法混合一样。但如果它们仅仅是边缘呢?在法国和西班牙,这些边缘可能具有坚实的内容,但在那里,在这个过去,却不是如此;这些边缘的内容如此大量地溢出和渗透,以至于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边缘?
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了。黎凡特悖论就是一个笨拙的结;从两端轻轻拉扯,它就会自行解开。将绳子的一端视为文化。每一个物种都有其独特的生态位,其对当地栖息地的独特适应。竞争排斥原则表明,两个物种无法挤进同一个生态位:适应性稍强的物种最终会驱逐另一个。传统上,人类的生态位是由文化定义的,因此两种人类不可能使用相同的石器,争夺相同的动植物资源。一种会迫使另一种灭绝,或者从不允许它立足。
“竞争排斥原则将阻止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类在同一小区域内共存 4 万或 5 万年,除非它们有不同的适应性,”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 Geoffrey Clark 说。“但据我们所知,凯巴拉和卡夫泽赫的适应性是相同的。” Clark 将使用符号——或缺乏使用——也列入了共同适应性的清单。“也许尼安德特人缺乏复杂的社会符号,如珠子、艺术品和复杂的葬礼。但他认为,住在不远处的苗条的卡夫泽赫人也是如此。如果两者都没有在景观中留下某种新心智能力的痕迹,我们凭什么权利偏爱苗条的、拥有光明未来的那个,而将另一个判处愚蠢的灭绝?”
这导致了绳子的形态端。如果两种人类类型在工具上无法区分,那么区分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宣称一个看起来像尼安德特人,而另一个则不是。如果你将所有相关的化石排成一列,你能真正将它们分成两组互斥的群体,没有重叠吗?一个替代主义者可能会这么认为,但一个连续性信徒,如 Geoffrey Clark,坚持认为你不能。他认为,将这些化石更好地描述为一个广泛变化的种群,涵盖了从最尼安德特人到最现代人的一切。早期塔布恩和斯赫尔的挖掘者将那里的化石视为原始智人和现代智人之间的中间等级。“也许他们是对的,”Clark 认为,“骨骼材料远非清晰的‘尼安德特人’和清晰的‘现代人’,无论这些术语最初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它们并不多。”
这种观点保留了连续性的传统观念,但放弃了过程:人类之间不存在从一种类型到另一种类型的演化——从尼安德特人到现代人——因为实际上不存在“另一种”。但尽管它很有吸引力,这种“单一性”解决方案在黎凡特悖论上存在根本缺陷。没有人会否认两种人类的工具包几乎完全相同。但这并不逻辑地意味着工具制造者也必须相同。中更新世的工具包与尼安德特人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是中更新世最广为人知的古人类。但如果具有现代解剖学特征的人在那时也存在,为什么他们不使用与尼安德特人相同的文化呢?
“如果你问我,忘了石器,” Ofer Bar-Yosef 告诉我。“它们什么也说不了,零。最多能说明他们是如何准备食物的。但厨房里做的事情就是你生活的全部吗?当然不是。作为积极的人,我们不愿意承认,一些缺失的证据可能正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证据。”
无论工具暗示什么,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的骨骼看起来不同,并且它们的差异模式太一致,不能被忽视。正如人类学家 Erik Trinkaus(新墨西哥大学)所展示的那样,这些骨骼差异清楚地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尽管考古遗迹可能相似。此外,这两种身体类型并非相互推导,也不是在短暂的瞬间相遇,然后一种占优势而另一种消退。它们只是并肩前行,但从不混合。在他的骨骼行为学方法中,Trinkaus 故意忽略了那些可能最能区分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在基因上差异的特征。根据定义,这些特征是生活方式对骨骼影响的糟糕指标,因为它们的形状和大小是由遗传决定,而不是使用决定。但人类生活中有一个方面,行为和遗传在此汇合:使人类世系得以延续的行为本身。
人类喜欢交配。他们随时随地交配,无论白天黑夜,无论女性生殖周期的哪个阶段。有机会的话,全世界的人类都会与其他任何人交配。种族和文化之间的障碍,在其他方面如此残酷地明显,但在性方面却融化了。科尔特斯开始了对阿兹特克人的系统性灭绝——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娶一位阿兹特克公主为妻。自被强迫奴役以来,黑人在美国一直受到白人的蔑视,但大约 20% 的典型非裔美国人基因是白色的。想想 18 世纪詹姆斯·库克在太平洋的航行。“库克船员来到某个遥远的土地,岸边站满了那些长着长长的下巴、粗大的眉脊,长相非常奇怪的人类,”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考古学家 Clive Gamble 告诉我。“上帝,那一定让他们觉得多么奇怪。但这并没有阻止库克船员们生下许多小小的‘库克仔’。”
将这种普遍的人类行为投射到更新世中期。当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在黎凡特接触时,无论他们最初看起来多么奇怪,他们都会杂交。如果他们的共存持续了数万年,化石应该会随着时间推移,向单一的形态模式收敛,或者至少出现一些性状的相互交换。
但证据并不存在,如果 TL 和 ESR 的年代是正确的话。相反,尼安德特人坚持自我。事实上,根据一些最近的 ESR 年代,他们中最不尼安德特人的是最年长的。完整的尼安德特模式在凯巴拉洞穴被深深地雕刻下来,大约在 6 万年前。与此同时,现代人在卡夫泽赫和斯赫尔很早就到来,并且从未失去他们的现代外观。当然,有可能随时会有新的化石被发现,确凿地证明了“尼安德特-现代”谱系的出现。然而,根据现有的证据,最可能的结论是,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在黎凡特并没有杂交。
当然,要杂交,你首先需要相遇。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在迦密山坡上数万年的共存仅仅是由于考古记录不完善而造成的幻觉。如果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在地理上相互隔离,那么他们未能杂交就没什么神秘的。最明显的隔离形式是地理隔离。但想象一下时间上的隔离。黎凡特的气候在中更新世波动——有时温暖干燥,有时寒冷潮湿。也许现代人类在温暖时期从非洲迁移到该地区,因为那里的气候更适合他们更轻、更高、更适应温暖体格。另一方面,尼安德特人可能只在冰川推进使他们的欧洲栖息地比他们适应寒冷的体格所能承受的还要冷时才来到黎凡特。那么,这两种人与其说是共存,不如说是共享同一片陆地,同时又在他们各自的大陆范围内。
虽然这个解决方案很有趣,但存在问题。古人类是适应能力极强的生物。即使是古代的直立人——缺乏大脑、有柄矛尖和其他文化装备——也设法在各种地区和各种气候条件下生存。而且,虽然古人类适应迅速,但冰川移动非常非常缓慢,来来往往。即使一种或另一种人类在气候极端时期独占了黎凡特,但那些既不最热也不最冷的千年时光呢?一定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长达整个有记录的人类历史——黎凡特的气候都非常适合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这些“中间时期”在这个时间共享情景中扮演什么角色?让一个人类种群在另一个搬进来之前就礼貌地撤离迦密山,这说不通。
如果这些人既没有在空间上也没有在时间上被隔离,而是真正同时存在,那么他们到底为什么没有交配呢?解决这个谜团的唯一办法还剩下一种。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在黎凡特没有杂交,是因为他们不能。他们是生殖不相容的,是独立的物种——可能同样是人类,但生物学上是不同的。两个独立的物种,恰好同时,在同一地点,都是人类。
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黎凡特地区的共存引发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可能性。它迫使你想象两个同样有天赋、足智多谋、情感丰富的人类实体,在同一片风景织锦中穿梭——但彼此之间却如此不同,以至于当今人类的种族多样性与之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如果消除了性桥梁,你就会得到两个完全有感知能力的人类物种被挤压在一个地方,彼此之间就像你后院里共享同一个喂食器里的两种鸟一样漠不关心。
当古人类学家争论尼安德特人的解剖结构是否足够独特,足以证明尼安德特人是与我们不同的物种时,他们使用的是物种的形态学定义。这对于古人类学家来说是一种有用的借口,因为他们首先只能依靠骨骼的形状来工作。但他们承认,在真实、充满活力的混乱的自然界中,骨骼形态是区分一个物种的开始和另一个物种的结束的糟糕指标。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进化生物学家 Ian Tattersall 指出,如果你剥去 20 种新大陆猴子的皮肤和肌肉,它们的骨骼将几乎无法区分。许多其他物种,即使带着皮肤,看起来也一样。
生物学物种的最常见定义,与古人类学家不得不处理的形态学上的“假装”相反,是已故的进化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的一句简洁的话:“物种是actually 或potentially interbreeding 的自然种群,它们在生殖上与其他此类种群隔离。”关键短语是“生殖上隔离”:一个物种就是它不与任何其他物种交配的东西。阻止物种随意杂交并产生一种有机汤的进化障碍被称为“隔离机制”。这些可能是任何阻止密切相关的物种杂交产生可育后代的障碍。障碍可能是解剖学的。东非的两种蹄兔共享同一个睡眠洞,使用公共厕所,并在集体玩耍群中抚养幼崽。但它们无法杂交,至少部分原因在于雄性阴茎的形状截然不同。隔离机制不必如此显眼。两个密切相关的物种可能有不同的发情周期。或者,障碍可能在交配后发挥作用:染色体不兼容,或者可能重组成一个无法繁殖的后代,一个不育的杂交后代,就像骡子一样。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古人类学家在试图将迈尔的生物学物种概念应用于古代古人类时会感到绝望。识别生物物种所需的特征——隔离机制——通常不会以化石的形式出现。发情周期如何保存?一个不育的杂交后代,只剩下骨骼的几块碎片,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染色体差异如何变成石头?
但还有另一种看待物种的方式,可能会带来希望。生物物种概念是一个奇怪的消极概念:一个物种之所以是一个物种,是因为它不与其他物种交配。几年前,南非生物学家休·帕特森森(Hugh Patterson)将生物物种概念颠倒过来,提出了一个基于与谁交配而不是与谁不交配的物种观。根据帕特森森的说法,物种是自然界中共享共同受精机制的群体。
以生殖为核心,帕特森森的概念与迈尔的概念一样具有生物学意义。但他将焦点从阻止杂交的障碍转移开,并突出了确保精子与卵子成功结合的适应性。显然,性行为和受孕是受精机制,就像父母双方染色体的基因兼容性一样。但早在精子靠近可接受的卵子之前,两性就必须有办法相互识别为潜在的配偶。或许,这其中就蕴藏着解决迦密山之谜的办法。
自然界中的每一次交配都始于一个信号。它可能是化学信号:例如,泡叶藻(Ascophyllum nodosum)的卵子会释放出一种吸引泡叶藻精子的化学物质,而不会吸引其他任何东西。它可能是一种气味。正如任何养狗人士都知道的那样,一只发情的母狗会从邻近地区吸引公狗。请注意,气味不会吸引松鼠、公猫或青少年。许多鸟类使用声音信号来吸引和识别异性,但只针对自己的物种。“一个物种的雌性可能会听到另一个雄性的歌声,”帕特森森在威特沃特斯兰大学的同事 Judith Masters 解释道,“但她不会做出任何反应。没必要谈论是什么阻止她与那个雄性交配。她就是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动静。”
一个物种的求偶识别系统与对当地栖息地的适应性相比,是极其稳定的。一只喙稍微短一点的麻雀可能能够比一只喙大小适中的麻雀更好地喂养它的幼崽,也可能不能。但是一只唱着陌生歌曲的麻雀将无法吸引配偶,也无法繁衍后代。它将被下一代的基因库淘汰,留下它特异性歌声的任何演化痕迹。当然,任何未能回应潜在配偶唱着正确曲调的母麻雀也是如此。有了这种偏离的代价,每个人都是保守派。“只有当发生真正戏剧性的事情时,一个物种的求偶识别系统才会改变,”Masters 说。
为了戏剧性的展开,一个种群必须在地理上与其母种群隔离。如果种群足够小,而且栖息地与其以前的栖息地截然不同,即使是强大的求偶识别系统的演化惯性也可能被克服。这种繁殖的变化可能伴随着对环境的新适应。或者不伴随。无论如何,标志着一个新物种诞生的唯一变化是影响求偶识别的变化。一旦越过了识别阈值,就无法回头了。即使新种群和旧种群的个体再次生活在同一地区——比如在一个连接它们两个大陆分布区的、人来人往的肥沃土地走廊里——它们将不再将彼此视为潜在的配偶。
人类的求偶识别系统压倒性地是视觉的。叶芝写道:“爱从眼睛进入”,而人类身体中最吸引眼球的部位就是面部——这是我们的物种与其他许多灵长类动物共有的特征。“这是旧大陆猿猴普遍使用的策略,”Masters 说。猴子有各种眼睑闪烁的技巧。森林长尾猴有鲜艳的脸部,带有物种特有的图案,它们在森林的阴暗中像旗帜一样挥舞。“进化这只老顽固,不断在同一个主题上玩出新花样。”
面部是极其富有表现力的工具。在我们面部皮肤之下,是一张由肌肉组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络,尤其集中在眼睛和嘴巴周围,纯粹是为了社交沟通而进化——表达兴趣、恐惧、怀疑、喜悦、满足、疑惑、惊讶,以及无数其他情感。每种情感都可以通过抬眉或轻微的面颊肌肉抽搐进一步修饰,以表达,例如,适度的惊讶、极度的惊讶、失望的惊讶、伪装的惊讶等等。据估计,面部两侧的 22 块表情肌可以产生 10,000 种不同的面部动作或表情。
在这套社交信号的武器库中,有一些刻板的、正式的对潜在配偶的邀请。我们称之为“调情”的求偶展示,在一位新几内亚部落妇女和一位巴黎咖啡馆的年轻女学生脸上表现相同:害羞地将目光向一侧向下移,然后偷偷瞥一眼对方的脸,并羞怯地移开视线。许多其他性信号也通过面部传递——下巴下垂、瞥一眼肩膀、嘴唇微微张开。面部作为吸引力的重要性,体现在人类在各种文化中为美化已有的东西所付出的努力。但潜在的信息是由面部本身的解剖结构传达的。亚历山大·蒲柏写道:“我们称之为美的不是嘴唇或眼睛,而是所有元素的联合力量和完整结果。”正是这种联合力量——历经几代——使我们的物种如此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这让我们回到了黎凡特:两个人类物种在狭小的空间里,长期共存。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现代人在解剖学上最显著的差异所在,也是即使最顽固的连续性倡导者也能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划清界限的地方,当然是面部。尼安德特人经典的脸部模式——中面部前突,被巨大的鼻子向前推,颧骨隆起,长下巴且没有下巴,大而圆的眼窝,以及比眉毛厚一倍的眉脊,像双层遮阳篷一样遮盖着它——通常被解释为与寒冷气候相关的复杂适应,或作为支撑前牙强大咀嚼力的结构。无论哪种情况,都被认为是环境适应。但如果这些面部适应性功能不是它们最初进化的原因呢?如果这些独特性是为了支撑一个完全独立、纯粹的尼安德特人求偶识别系统而进化的呢?
虽然这仅仅是猜测,但这个想法符合一些事实,并解决了一些问题。当然,尼安德特人的祖先在地理上与其他种群隔绝,足以允许出现新的求偶识别系统。在冰川时期,通过亚洲的联系被极地冰川和广阔的、不宜居住的苔原阻断。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山地冰川几乎完成了向南的屏障。“尼安德特人是获得独立物种的经典案例,”考古学家 John Shea 告诉我。“将它们隔离一万年,然后融化冰川,让它们出来。”
如果求偶识别是物种层面差异的根源,那么黎凡特悖论就可以最终得到解答。它们与现代人的共存不再需要解释。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能够共存数千年,做着同样人性化的事情,但却没有杂交,仅仅是因为这个问题从未真正出现。
这个想法似乎难以置信。连续性信徒无法相信两种人类类型在性隔离中并存。替代性倡导者无法想象如此长时间的共存却没有竞争,如果没有公然的暴力对抗。他们宁愿看到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相互争夺黎凡特,在一场漫长的斗争中最终由我们自己的祖先获胜。当然,如果尼安德特人是一个生物学上的独立物种,那么必然发生了某种事情导致了他们的灭绝。毕竟,我们还在,而他们却不在了。
他们为何消逝而我们得以生存,这是另一个故事,也有其自身的震惊和惊喜。但迦密山上发生的事情可能更为非凡。这是一些当今人们无法理解的事情,尤其是在黎凡特这样的地方。两种人类物种,彼此之间的共同点远少于当今地球上的任何两个种族或族群,可能在 5 万年里共享了一小块肥沃的土地,并且一直以来都以稳定、平静、无烦恼的冷漠态度对待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