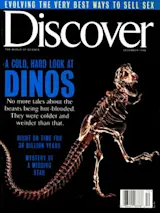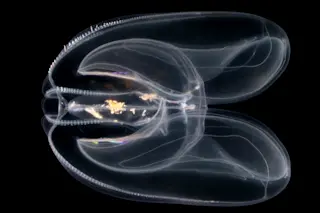我们不会在“骨坑”上多费笔墨。
去过那里的人对它有很多话要说:25万年前,人类把几十具其他人类的尸体拖进一个洞穴,然后——谁知道为什么?——把它们扔进了46英尺深的竖井。尸体一定伴随着沉闷的“砰”声着陆,因为竖井底部是一个泥泞的斜坡;它们像布娃娃一样手舞足蹈地翻滚,最终落入了一个低矮的、没有出口的洞室,那是坑底真正的底部。后来,寻找冬眠场所的熊误闯入竖井,其中一些在坠落后存活下来,啃食了人类遗骸。狐狸也曾跌落,还有一两只狮子。数个世纪以来,一层厚厚的动物遗骸堆积在杂乱的人类遗骸之上——然后洞穴的原始入口不知何故关闭了,使得所有骨头在数千年里未受干扰。潮湿的粘土完美地保存了它们。直到中世纪,从洞穴中的涂鸦来看,这个坑才被山下麦田对面伊比利亚斯德胡阿罗斯村的年轻人重新发现。
伊比利亚斯和这座山——一片名为阿塔普埃尔卡山脉的低矮山脊——位于西班牙中北部,布尔戈斯以东几英里处。它们离潘普洛纳不远,至今仍有年轻人选择在那里被愤怒的公牛追逐穿过街道。在伊比利亚斯,街道上更多的是羊,而那里的男孩们在某个时候开始通过冒险进入“骨坑”——Sima de los Huesos——来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他们的目的是为女孩们取回熊牙。毕竟,获取熊牙并不容易。在原始入口关闭的情况下,要到达那个46英尺深的竖井,你必须钻过1600多英尺的洞穴,其中几百英尺需要手膝并用,几十英尺需要腹部着地。尤达尔德·卡博内尔·伊·鲁拉、何塞·玛丽亚·贝穆德斯·德·卡斯特罗·里苏埃尼奥和胡安·路易斯·阿苏阿加·费雷拉斯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这段旅程——但他们不是为了爱情,或者至少不是为了普通的那种。卡博内尔是塔拉戈纳的考古学家;贝穆德斯和阿苏阿加是马德里的古人类学家。1976年,一名研究生曾下降到Sima,并带出了熊牙,是的,但也带出了一块非常古老的人类下颌骨。那块颌骨就是这一切的开端。
然而,现在,只有阿苏阿加和他的康普顿斯大学团队在Sima采矿。卡博内尔和贝穆德斯更喜欢在户外工作。卡博内尔对他在坑中的几个季节记忆犹新。他和同事们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背出四个世纪以来熊牙猎人搅起的四吨泥土。他说,那太可怕了。那是非常、非常、非常艰难的。我记得:那是非常、非常、非常艰难的。有一天在Sima,他发现自己打起了瞌睡——不是因为在狭窄空间里挖了好几个小时无法站立的疲劳,也不是因为无聊,而是因为缺氧。他试了试打火机;打不着。他的同伴们也打着瞌睡。他把他们摇醒,大家爬到外面,大口喘气。卡博内尔继续说,很多次,那些无法忍受狭小空间访客不得不被从Sima拉出来,通过一个狭窄到不足两英尺的通道。有一次,一位电视制片人在洞穴里心脏病发作。
但是我们不会在“骨坑”上多费笔墨。
尽管它提供了对深远过去的无与伦比的视角——其中的骨头属于尼安德特人的祖先——但最近,这个坑被几百码外的一个第二个遗址抢了风头。在一个充满沉积物的洞穴里,叫做大洞穴(Gran Dolina),这是一个你需要挖掘而不是爬进去的洞穴,卡博内尔和他的同事发现了比Sima中的骨头早三倍的骨头——它们有80万年的历史,是欧洲最古老的人类遗骸。它们的解剖结构被证明是独特的。牙齿,尤其是前臼齿,类似于来自非洲的更古老的牙齿。下颌骨类似于Sima人和他们的尼安德特后代。但面部——从大洞穴的粘土中浮现出的面部——是最令人惊讶的。阿苏阿加说,它如此令人惊讶,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人类进化以适应这张脸。大洞穴的面部有80万年的历史,但却具有我们独特的特征。它几乎是一个现代人类的面孔。
西班牙研究人员认为,它属于一个以前未知的人类物种,该物种与我们和尼安德特人的最后一个共同祖先非常接近。他们称该物种为“先驱人”(Homo antecessor)——意为“先锋人”或“侦察人”。他们说,大约一百万年前,“先驱人”走出非洲,穿过近东,横跨南欧抵达西班牙。在那里,它找到了通往阿塔普埃尔卡的路,那一定是一个宜人的居留之地。
在七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一早上8点45分,尤达尔德·卡博内尔那辆老旧的路虎车沿着从布尔戈斯出发的国道向东轰鸣着,前方和左侧,群山如绿色大象般从薄雾中浮现。右侧短暂地出现了一片联排别墅开发区。卡博内尔比载着他团队的货车早了几分钟,他的团队有60多位年轻科学家和学生,他们在大洞穴进行挖掘。当他离开伊比利亚斯的柏油路时,他把车开进了名为“洛斯克拉维莱斯”的旅馆停车场。他走到吧台前,咕咚咕咚地喝下一杯 chico chica——两种烈酒的混合,其中一种清澈而辛辣。他解释说,农民们就是这样开始一天的。在这里,在阿塔普埃尔卡山脉的山脚下,在阿兰松河谷的温柔怀抱中,人们已经耕作了6000年。卡博内尔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从塔拉戈纳的罗维拉·伊·维尔吉利大学来到这里。女服务员把饮料记在他的账上。
路虎现在沿着一条土路向北颠簸,穿过被风吹拂的金色麦浪,其中散发出几乎是潜意识的红色罂粟花的光芒。群山就在正前方。它们当然比农田还要古老得多——基岩是白垩纪石灰岩,形成于一片曾经将西班牙与欧洲隔开的浅海中。后来,在形成比利牛斯山脉的巨大构造挤压中,石灰岩被抬升;很久以后,地下水侵蚀出穿过它的隧道;再后来,阿兰松河切开山谷,从而将地下水从群山中引出。这些隧道变成了空洞的洞穴。在更新世时期,大约160万年前开始,它们慢慢被通过入口吹入或冲入的沉积物填满。在大部分同一时期,它们被人类和其他动物用作庇护所。堆积的沉积物层,每一层都曾是洞穴地面,现在都布满了遗骸。
洞穴和卡博内尔的缘分由来已久。他在东比利牛斯山脉的加泰罗尼亚长大,五岁时在那里发现了他的第一块化石。十二岁时,他在一个洞穴入口组织了他的第一次考古发掘——他发现了一些青铜时代的陶瓷和一些罗马硬币,这些至今仍在博物馆展出。这个洞穴附近有一所准法西斯天主教寄宿学校,卡博内内尔在那里学习成绩不佳,却表现出许多野性,这正是他母亲最初把他送到那里的原因。洞穴是卡博内尔的避难所——尽管有一次他和几个受他影响的男孩差点在一个突然的雷雨中被淹死,当时他们正在爬行的一个狭窄通道被水填满。他现在笑着说,那是年轻时的故事,但有时生活回顾起来才说得通;有些人似乎生来就注定要扮演自己的角色。在大洞穴,工人们戴着彩色安全帽以防落石;但卡博内尔——高大、留着胡子、帅气而强壮,44岁,即使在西班牙这种注重体魄和外向的文化中,他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从不吝惜拍打后背或拥抱肩膀,一个在人群中高声唱歌的人——卡博内尔不戴塑料安全帽。他爬上脚手架去挖掘时,戴着他的软木帽。
“先驱人”首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出现的地方,位于一个峡谷的墙壁上,这个峡谷实际上是一条废弃的铁路线壕沟,名为“Trinchera del Ferrocaril”。本世纪初,一家英国矿业公司在阿塔普埃尔卡山脉的西南坡开凿了这条壕沟;铁路将铁矿石从东南30英里外拉德曼达山脉的矿山运到布尔戈斯附近的一个交汇点。时代照片显示,当Trinchera刚建成时,它是地貌上的一个污点。但现在,在某些地方——那些你看不见卡博内尔脚手架的地方——它看起来几乎是有机的,甚至很美:峡谷壁已经风化,灌木和野花重新占据了地面,圣栎树从边缘倾泻而下。当你从伊比利亚斯上来,向下望着壕沟弯曲消失的地方,那景象会久久萦绕在你心头。它看起来像一个“时间之路”的图标:点击此处进入过去。
自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对于尤达尔德·卡博内尔来说,直到最近才开始有所进展。但现在和他一起站在脚手架上,面对着那片七乘十英尺的层层沉积物切口,你可以想象它曾经的样子。脚手架无声地坍塌,特林切拉在你下方被填满,洞穴的石灰岩墙壁和屋顶重新组合,你面前的沉积物融化消失,直到最终你站在80万年前的大洞穴中。穿透薄雾照亮特林切拉的晨光现在消失了,唯一的光线是从你身后40英尺高的平缓碎石斜坡上的小洞口渗透下来的。在你前方几英尺处,一小群人类正用粗糙的石器工具忙碌地从骨头上剥肉。他们正在敲碎骨头以获取骨髓。是捕食者的恐惧让他们如此深入黑暗吗?是羞耻吗?他们的感受已对我们无从考证,它们不会化石化,只有他们正在屠宰的骨头会,而这些骨头属于屠宰者自己的同类——一个11岁的男孩或女孩;几个三四岁的幼儿。但这些稍后再说。
从壕沟底部,你可以看到洞穴的横截面:白色石灰岩的墙壁和起伏的顶部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红色泥球,它填满了整个洞穴。有些地方,动物骨头从泥中突出。早在卡博内尔1978年抵达现场,在古人类学家埃米利亚诺·阿吉雷的监督下工作之前,其他人就已经注意到了它们。Sima中发现的人类下颌骨吸引了阿吉雷和卡博内尔来到阿塔普埃尔卡,但他们首先开始在大洞穴挖掘。当时这似乎更直接一些。
项目开始几年后,1982年,贝穆德斯前来参观。他和卡博内尔在洛斯克拉维莱斯酒吧喝酒,从此成为一生的朋友。贝穆德斯是一位年轻的古人类学家,他一直想研究人类起源,但他有一个问题:西班牙几乎没有人科化石。他的博士导师让他转而研究加那利群岛人的起源——关于一千年前谁定居这些岛屿的问题——贝穆德斯通过分析博物馆藏品中的牙齿完成了这项研究。他对牙齿的专业知识后来派上了用场,但从博物馆抽屉里取出牙齿并非贝穆德斯设想的职业生涯。他在大洞穴的第一个野外季节更像他所设想的。他回忆道,那是非常强大的考古学,笑容在他和蔼、略显丰满的脸上蔓延开来。他想不起英文单词“电镐”,于是他做了个手势。我的印象是,“哇,这太棒了!”
然而,卡博内尔已经挖掘了五年,电动工具的吸引力正在逐渐减弱。他说,那些年对发掘来说非常艰难。资源匮乏——团队很小。多年来,我们只是从铁路切割口中捡拾东西。问题在于如何处理这个遗址——它太大了,我们不知道从何下手。唯一合理的地方,实际上,是从顶部开始;正确地给骨骼和文物定年并重新构建其原始背景的唯一方法是逐层发掘。这就是为什么卡博内尔和贝穆德斯在1983年夏天站在大洞穴顶部,用电镐穿透石灰岩屋顶进入第一层沉积物(大约15万年前),用电镐和镐头在灰尘和卡斯蒂利亚的阳光下像公牛一样挥汗如雨——却没什么发现。即使那时,卡博内尔也从壕沟壁上看到的(他甚至发现了一些燧石工具)怀疑,沉积物堆中间更古老的沉积物才是富含文物的。但从顶部到达那里需要更多的资金和更大的团队。
另一方面,在“骨坑”(Sima de los Huesos)里,即使你有一个更大的团队也无法容纳——这个坑最多只能容纳五六个活人。而且尽管那里的工作异常艰苦,但几乎肯定会找到人类化石。所以卡博内尔和贝穆德斯暂时放慢了“大洞穴”(Gran Dolina)的发掘速度,并在八十年代中期与阿苏阿加一起攻克Sima。1989年,阿苏阿加终于越过熊骨层,到达了一个几乎只发现人类骨头的新层位。接着在1992年,他与同事们从Sima中发现了有史以来最完整的人类头骨,而且它并非现代智人——比许多尼安德特人头骨都要完整,而且比大多数尼安德特人头骨早20万年。Sima头骨很快登上了著名的英国期刊《自然》的封面。阿塔普埃尔卡的工作终于进展顺利了。卡博内尔在那里挖掘了15年,贝穆德斯和阿苏阿加也挖掘了10年。
现在他们开始获得资源——卡斯蒂利亚-莱昂地方政府增加了支持——以妥善地挖掘大洞穴。卡博内尔安排了一个团队在一个小型的试掘点工作,就是在壕沟墙上的那个七乘十英尺的凹槽,计划从洞穴顶部开始,一直挖到最底部百万年前的沉积物。到1993年野外季节结束时,团队几乎挖到了他们认为有50万年历史的层位。他们进展缓慢但稳定。然后他们受到了竞争对手的一点刺激。
1994年6月初,也就是下一轮挖掘开始前一个月,卡博内尔从邮箱里取出他的《自然》杂志,这次封面上,他在一张人类胫骨图片下方看到了大字写着“第一个欧洲人?”。这块胫骨是在英格兰南部的博克斯格罗夫发现的,年代约为50万年前。这使其与1907年在德国海德堡附近出土的一块著名下颌骨——毛尔下颌骨——年代相同。尽管一块下颌骨很难与一块胫骨联系起来,但博克斯格罗夫的研究人员或多或少地默认将这两项发现归为同一物种——海德堡人。近一个世纪以来,欧洲没有发现其他同龄的人类骨骼,当然也没有更古老的。一篇与文章同时发表的评论强烈暗示,永远不会发现更古老的骨骼。尽管有明确证据表明早期人类物种直立人最迟在一百万年前就已走出非洲,但欧洲似乎直到50万年前仍是一个未被殖民的偏僻地区。《自然》杂志的评论员想知道:我们如何解释这一点?
这让卡博内尔热血沸腾。他亲身感觉到在大洞穴有更古老的欧洲人——他从壕沟中捡到了他们的一些石器工具。他打电话给贝穆德斯和阿苏阿加。他们三人,自1991年以来一直共同负责阿塔普埃尔卡的所有发掘工作,同意立即派出一支特别小组加快挖掘速度。否则,他们可能要经历一个令人沮丧的野外季节,却未能达到博克斯格罗夫工人已经达到的历史深度。当卡博内尔在7月1日照常时间到达大洞穴时,先遣人员已经快速挖了六英尺多的沉积物。接下来的一周铭刻在他的记忆中。
7月2日,挖掘人员发现了牙齿——水田鼠Mimomys savini的牙齿。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Mimomys在欧洲各地的遗址中都有发现,它在大约50万年前灭绝。它的臼齿有牙根,这将其与继它之后出现的田鼠Arvicola terrestris的无根臼齿区分开来。博克斯格罗夫的胫骨是通过田鼠时钟来测年的:它来自Mimomys向Arvicola过渡之后。此前,在欧洲任何地方,从未发现过与Mimomys相关的任何人造物品或遗骸。直到现在?“现在我们知道那里有这种啮齿动物了,”卡博内尔说。“我们仍然需要找到工具和人科动物。”
工具在这一周内陆续出现。接着,7月8日,一名名叫奥罗拉·马丁·纳赫拉的挖掘者从泥土中又提取出三颗牙齿,这些牙齿并非来自田鼠。马丁,恰如其分地,是团队中的资深成员,在大洞穴摸索了14个季节——几乎和卡博内尔本人一样多。或许你必须经历过漫长而大多徒劳的努力,才能理解几颗牙齿所能激发的纯粹喜悦。无论如何,马丁克制住了自己。她知道它们是什么,但牙齿专家贝穆德斯被召来确认。他确认了。它们确实是人类牙齿,而且——它们是非常古老的人类牙齿。
其中一颗是前臼齿,这种牙齿位于口腔后部臼齿和前角犬齿之间。站在挖掘点旁边的脚手架上,贝穆德斯手里翻看着这颗前臼齿,他立刻看出它有一个复杂的牙根,有三个牙髓管——牙髓管内含有神经和血液,维持牙齿的生命。在一个牙齿中发现牙髓管,在这样的时刻似乎是个微不足道的细节,更不用说将其作为构建人类进化宏伟论断的依据了。但事实就是如此:此前在欧洲发现的所有前臼齿,从与毛尔下颌骨相关的牙齿到现代人类的牙齿,都只有一个牙根,而不是三个。大洞穴的前臼齿看起来古老且明显带有非洲特征:贝穆德斯想,这是直立人。
同一沉积层中发现的Mimomys牙齿表明,这些人类牙齿的年代早于50万年——当然也早于博克斯格罗夫胫骨——但究竟早多少,尚不清楚。然而,在考古学家们进行挖掘(并总共发现了36块人类骨骼碎片,包括大部分额骨、上下颌骨碎片,以及牙齿、手指和脚趾)的同时,来自密歇根大学的约瑟夫·帕雷斯和康普顿斯大学的阿尔弗雷多·佩雷斯-冈萨雷斯两位地质学家,正在从大洞穴的所有沉积层中采集小样本。他们正在寻找第二个时间标记:下更新世和中更新世之间的界限。这个界限被定义为地球磁场最后一次反转方向的时间,大约在78万年前。在此之前,磁场呈负极性:它指向南方而不是北方。早期的地质学家团队曾将这次反转定位于大洞穴沉积层堆的最底部,远低于卡博内尔团队正在挖掘的深度。但帕雷斯和佩雷斯有理由相信那项研究做得不够仔细。
野外季节结束几个月后,卡博内尔在塔拉戈纳接到了一个电话。帕雷斯说,“听着,我们在你的人科动物周围发现了负极性,”卡博内尔回忆道。
我说,“你什么意思?”
“我说的就是那个意思。我相信你的人科动物处于负极性。这意味着这些人科动物的年代超过78万年。”
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对他说的话。“听着,这不是开玩笑。如果你不确定,你可以下去把整个团队都带走。因为这是一个强烈的声明。这将是欧洲首次在下更新世发现人科动物。你要负全责。”
他说,“是的,是的,好的,我会负责的。”他重复了分析。毫无疑问,我们确定是78万年前。
有时,人类进化的研究似乎与其研究对象以相同的速度前进。争论持续数十年,常常枯燥乏味。在发现第一批尼安德特人化石,即古人类学诞生事件140年后,关于尼安德特人是谁,仍没有共识——他们是我们的祖先,还是另一种完全消失无踪的人类物种?最近的证据似乎倾向于后一种假设;例如,就在今年,从一块原始尼安德特人骨骼中提取的DNA被发现与现代人类DNA截然不同。但这并不会结束争论。古人类学具有不可避免的主观性,部分原因在于化石稀少,这使得争论悬而未决——而这种稀少在试图追溯到尼安德特人之前的中更新世和下更新世时尤为突出。在10万年前的经典尼安德特人化石与非洲最早的智人化石之间,存在约150万年的空白,其中只有少数骨骼散落其间。
在过去的十年里,关于尼安德特人的争论已成为一个更广泛论战的一部分。那些相信尼安德特人进化为欧洲现代人类的人,也相信同样的过程发生在其他地方;他们说,现代人类是从直立人种群在非洲扩散后,在世界几个区域同时进化的。另一方面,那些相信尼安德特人被现代人类取代后在欧洲灭绝的人,也相信同样的过程发生在其他地方;他们说,世界各地的前现代人类都被现代智人取代了,而现代智人只在非洲进化,然后在大约10万年前从该大陆传播开来——这是第二次迁徙。这一“走出非洲二号”理论最著名的倡导者是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克里斯·斯特林格(Stringer)。(斯特林格碰巧也是分析博克斯格罗夫胫骨并将其命名为海德堡人的人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大洞穴的研究人员与斯特林格的立场一致——但他们的发现并不能解决争论。
另一方面,从奥罗拉·马丁从阿塔普埃尔卡的泥土中取出人类牙齿的那一刻起,另一场争论就基本结束了。那是关于人类何时抵达欧洲的争论。许多人,像《自然》杂志的评论员一样,认为欧洲的定居是在50万年前才开始的。这种观点已被证明是错误的。那是古人类学中一种不寻常的轻率假设,很容易被证伪。奥罗拉层,现在在壕沟壁上用红色大头针标示,位于下更新世内部约三英尺处——也就是说,在磁场开始指向北方的沉积层之下,即78万年前。这三英尺的沉积物可能在2万年或20万年内积累起来;无法确定。但是,1994年从奥罗拉层中取出的骨骼表明,人类至少在80万年前就已经存在于阿塔普埃尔卡了。
然而,它们并未揭示这些人是谁。1994年野外季节结束后,贝穆德斯和他的同事们并不确定。这些牙齿是早期人属的,不仅仅是前磨牙的牙根;蜿蜒、多皱的牙冠也很古老。但在马德里国家自然科学博物馆仔细思考之后,贝穆德斯认为,这些复杂的牙根更具体地说,是原始的。之前在人属中从未有过如此描述。直立人没有它们,至少亚洲的直立人化石没有。贝穆德斯在超过160万年前的非洲化石中找到了最接近的相似之处,其中包括被称为“图尔卡纳男孩”的化石。这具壮观的骨架是理查德·利基团队于1984年在肯尼亚北部图尔卡纳湖发现的,它要么是早期直立人,要么是另一个更原始的物种——能人(Homo ergaster)——这是另一个悬而未决的争论。西班牙研究人员称之为能人,他们说它的牙齿与大洞穴人科动物的牙齿相似。
从奥罗拉地层中出土的眉脊也很原始。当然,所有的眉脊在我们看来都显得原始,但在它们的鼎盛时期,它们有不同的风格,就像太阳镜一样。亚洲的直立人有一个单一的、几乎水平的眉架——这大概是在他们离开非洲后进化的——它保护着双眼。更原始的图尔卡纳男孩则有更优雅的双弓眉脊——大洞穴化石也是如此,有趣的是,西马德洛斯韦索斯头骨也是如此,尼安德特人也是如此。早在1994年,一条线索似乎正在浮现,一条概念上的线索,从图尔卡纳湖穿过大洞穴延伸到西马,再延伸到尼安德河谷。安东尼奥·罗萨斯,阿塔普埃尔卡团队的下颌骨专家和贝穆德斯在国家博物馆的同事,也能追溯到同样的轨迹。在大洞穴发现的下颌骨碎片比图尔卡纳男孩的更细长——更纤细——但不如他研究过的西马化石那样纤细。甚至其内表面的细节也显得介于两者之间。
这样的标本该如何称呼?这些开拓性的欧洲人究竟是谁?罗萨斯说,当时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还在定义我们的生物。因此,在他们关于这项发现的第一份报告的结尾,阿塔普埃尔卡团队做了斯特林格在博克斯格罗夫做过的事情,将他们的生物归入了海德堡人——一个包罗万象的容器,其中几乎包含了非洲和欧洲所有中更新世的化石,包括来自西马德洛斯韦索斯的化石。西班牙研究人员提出,80万年前的大洞穴人可能是原始的海德堡人。但是,在挖穿六英尺的沉积物到达奥罗拉地层之后,他们花了三个7月,从1994年到1996年,慢慢筛查了十英寸厚的红棕色泥土。
当“先驱人”于1995年在大洞穴展现其面容时,其情感冲击不如一年前。仅仅牙齿就确立了欧洲早期定居者的原则,而这张脸看起来并没有那么有前景。当挖掘者将其取出时,它仍然被泥岩覆盖。胡安·路易斯·阿苏阿加记得当时认为,在移除岩石后,完整的骨骼所剩无几。但他随后说,它被国家博物馆的技术人员清理了。他们创造了一个奇迹。清理工作耗时一年多。对阿苏阿加而言,发现的时刻不是面部从大洞穴中出土,而是去年12月在马德里,当他第一次看到它的真面目时。
那只是一个局部面部,覆盖了眼睛下方到上排牙齿的区域。其中几颗牙齿仍在原位,这使得贝穆德斯能够确定这是一个人科少年的面部,大约11岁——与图尔卡纳男孩的年龄大致相同。在去年五月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论文中,西班牙研究人员试图用技术术语来传达这张脸的影响;他们谈到了眶下骨表面的凹陷、上颌骨的明显弯曲、颧牙槽嵴的水平度。但阿苏阿加第一次看到化石时的印象更简单:那是新奇的冲击。他说,我们期待一些大的、巨大的、膨胀的东西——你知道,一些原始的东西。我们对一个80万年前的男孩的期望是像图尔卡纳男孩那样的。而我们发现的是一张完全现代的脸。
现代人脸,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尽管有个体差异,但它是一张小巧精致的脸。现代人的大脑,我们都自豪地知道,是一个大而凸出的器官。这就是人类进化的故事,用几句话来说:大脑的扩张,面部的缩小,阿苏阿加解释道。工作从身体的一部分转移到另一部分。随着大脑足够大,足以构思巧妙的工具,我们不再需要巨大而有力的颌骨和牙齿来处理食物。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为这些大脑腾出空间。因此,它们向前向上生长,形成了高耸的额头,覆盖在我们的面部特征上方,并将它们挤压到我们头骨的前部下方。与我们的非洲祖先相比,我们的脸是萎缩的、扁平的、瘪的。我们眼睛下方的骨头——眶下骨表面——不再向前突出,而是向下向后倾斜,形成一个凹陷,使得我们所有人,不仅仅是超模,都有凹陷的脸颊。(它们有时被肉所掩盖。)为了将这些脸颊与我们细长突出的鼻子连接起来,上颌骨——上颌——必须明显地向内弯曲。别管颧牙槽嵴了;它不那么重要。
在大洞穴发现之前,最古老的现代人脸来自以色列一个12万年前的头骨。大洞穴人脸具有所有正确的特征,而且有80万年的历史。它比任何海德堡人化石都要古老得多,但却有一张更现代的脸。如何才能将其理解为原始的海德堡人呢?这个人科动物有一张智人的脸,下颌骨接近海德堡人,前臼齿则像能人。如何称呼这样的人?阿苏阿加说,如果你说它不是海德堡人,那么它就必须是一个新物种。如果你不给它命名,别人就会。西班牙研究人员正值40多岁的年纪,在学校里被强制学习过拉丁语,于是他们查阅了拉丁语词典。“先驱人”(Homo antecessor)似乎捕捉到了第一批无畏的非洲人侦察欧洲的精髓。
一个新物种在某种意义上使人类进化的故事复杂化,但它也能整理清楚一些事情。当然,阿苏阿加和他的同事们所设想的场景——对斯特林格“走出非洲”理论的补充——是足够简洁的。在这个场景中,全人类的祖先是能人(Homo ergaster),生活在150万到200万年前的东非。在这段时间的某个时候,能人迁移到亚洲,途中变成了直立人(Homo erectus)。一些仍有争议的日期将直立人置于爪哇岛,早至180万年前;更具争议的日期则将其置于中国,200万年前。这些日期很混乱,但概念很简单:直立人本质上是一个亚洲物种。与长期以来的信念相反,我们并非其后代。
当那些后来成为直立人的人离开非洲时,能人种群的其余部分留了下来。又经过大约50万年的进化,他们产生了先驱人。大约一百万年前,也许更早一点,先驱人也离开了,追随直立人的脚步。但在近东,它左转进入欧洲,经过数万年最终到达西班牙。它为什么不横渡直布罗陀海峡呢?贝穆德斯说,因为没有桥梁。横渡直布罗陀海峡很困难——海流非常危险。今天,摩洛哥人试图乘小船横渡海峡进入欧洲,几个月前就有40人丧生。他和他的同事们很难想象下更新世的人科动物会以足够多的数量进行横渡,以在欧洲建立一个成功的滩头阵地。
在他们看来,这确实是成功的:欧洲的先驱人种群产生了海德堡人,后者蔓延到整个欧洲,甚至到达英国的博克斯格罗夫。大约30万年前,是海德堡人部落将尸体扔进了骨坑。大约10万年后,海德堡人,在与非洲祖先完全隔离的情况下,进化成了尼安德特人——他们的巨大而完全独特的面孔从头骨前方突出,他们的大脑潜力不明,从头骨后方突出。与此同时,在非洲,从未离开的先驱人种群则踏上了截然不同的进化道路——这条道路最终导致了现代智人的出现。
之后的故事便是“走出非洲”的直线发展。现代人类在10万多年前离开了非洲大陆,并殖民了欧洲和亚洲,逐渐取代了尼安德特人和直立人。这个过程耗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根据去年报道的证据,远至2.5万或3万年前,地球上可能仍然存在三种人类物种,直立人仍盘踞在爪哇岛,尼安德特人则在西班牙南部。但这些年代仍然备受争议。
就像“先驱人”情景无疑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受到质疑一样。到目前为止,它尚未被许多西班牙研究人员的同行所接受。例如,克里斯·斯特林格仍然认为大洞穴儿童更可能是早期的海德堡人。他认为,该物种展现出的解剖学特征表明它是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的真正共同祖先;两者之间的进化分歧——在西班牙情景中,这将始于大约80万年前,在先驱人离开非洲之后——实际上只有不到40万年,这是发现的最年轻的海德堡人化石的年代。斯特林格说,我只是保持谨慎。给每一个新发现都命名一个物种是有风险的。我自己也被指责这样做过——很多人不相信海德堡人是一个独立的物种。
令斯特林格和其他古人类学家对“先驱人”情景最感困扰的是,它过于依赖一个儿童的面孔。众所周知,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变化很大。斯特林格说,或许那个凹陷的面孔纯粹是幼年特征,并不能将先驱人与后来的海德堡人区分开来;或许相同年龄的海德堡儿童——目前尚未发现——也会有同样的面孔。阿苏阿加承认他和他的同事们可能对先驱人的核心进化作用判断有误。他说,对此过于狂热是个大错误。但他不认为那个儿童的面孔是他故事的弱点。对他来说,那是最好的部分。
他解释说,我们相信,现代人脸代表着一个“幼态延续”的例子。这个想法并非全新。在20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路易斯·博尔克的荷兰解剖学家认为,幼态延续——即一个物种的成年个体保留其祖先的幼年特征——可以解释几乎所有的人体解剖结构。博尔克认为我们本质上是被滞后的猿类,由于进化过程中发生的简单荷尔蒙变化,我们的发育受到了阻碍。20年前,史蒂芬·杰·古尔德试图从这种天真的夸大中挽救博尔克思想的核心——认为幼态延续可以是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机制,即使它不是主要的。阿苏阿加认为,大洞穴儿童的面孔表明古尔德是对的。
阿苏阿加解释说,我们的脸,我们成年人的脸,与我们祖先的脸相比,非常小巧精致。我们的祖先有一张大脸,经过漫长的生长才达到。但我们的脸并非全新——自然选择并非如此运作。如果你想缩小面部骨骼,你可以继续让它生长,直到达到我们祖先的成年形态,然后再缩小。但还有另一种更明智的方式。那就是在面部仍处于缩小状态时就停止生长。
尼安德特人发生了什么?尼安德特人以另一种方式制造了一张脸。他们的脸与之前制造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他们必须制造一张新脸——就像我们制造头骨一样;我们的头骨是一种新设计——因为他们需要的脸并不存在。所以他们通过在生长过程中增加新的步骤来制造了一张新脸。但对我们来说,这更容易,效率更高,更安全,只需停止面部生长并保留幼年形态。这样我们就获得了一张精致小巧的脸——那是我们祖先孩子的脸。那是先驱人孩子的脸。
对我来说,这才是最引人入胜的——这些是能让你震撼的东西。发现这种完全出乎意料的事物。不是发现化石;发现化石也很出乎意料,而且没关系。但最引人入胜的事情是,在过去发现了你以为属于现在的东西。这就像在大洞穴里发现了一台——一台录音机。那会非常令人惊讶。我们不期望在下更新世发现磁带和录音机。80万年前发现一张现代人的脸——道理是一样的。当我们看到它时,我们非常惊讶。
阿苏阿加当然喜欢发现人类化石。但这对他来说已经有点例行公事了。在阿塔普埃尔卡团队的三位领导人中,阿苏阿加是最瘦小的,所以他每天七月都钻进西马是合适的。他说,我并不是特别喜欢洞穴。我只是穿过它去遗址。每天,他和他的同事们都会带着几十块人类骨头钻出来。这些骨头不全是头骨和面部——通常是指尖或脚趾尖,甚至是内耳的锤骨和砧骨。正是这些微小的骨头——通常即使在中世纪骨架中也无法保存的骨头——让阿苏阿加和他的团队在1980年代的“付费”岁月里坚持挖掘。他们认为,如果这些碎片存在,他们最终会找到那些能让同行关注阿塔普埃尔卡的头骨和下颌骨。任何对更新世人科动物感兴趣的人现在都必须关注。在10万到150万年前的这段时期发现的所有人类遗骸中,超过四分之三是在西马发现的。如果你只以手骨为例,中国有一块碎片,法国南部有一块——而西马则有300多块。这就像一个古人类学糖果店,尽管这家店有点难进去。
阿苏阿加和他的同事们仍然不确定30万年前在西马发生了什么。他们相信尸体坠入坑中时已经死亡,因为一些骨骼显示出致命疾病的证据。但他们没有发现文物,这让他们怀疑他们所见的并非葬礼仪式遗迹。也许这些尸体——至少32具,可能更多——是被某种灾难的幸存者出于卫生原因扔进坑中的。阿苏阿加说,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有其循环。有些年份很好,动物繁衍;有些年份很糟糕,动物大量死亡。我相信这就是发生了生态灾难,比如干旱之类的。西马德洛斯韦索斯的骨头可能都来自同一个屠杀季节,而且可能不超过两三年。
这意味着他们来自同一个族群:这些人彼此认识。他们都是年轻人和青少年,这加深了他们死亡的谜团。其中一人,拥有最完整头骨的主人,显然死于牙齿断裂引发的骨感染,这可能非常痛苦。另一人,从堵塞耳道的赘生物来看,听力不佳。他们大多数人的眼眶里都有微小的孔洞——这种状况被称为“眶上筛状体”(cribra orbitalia),表明他们童年时营养不良。大多数人还有关节炎性颌关节,可能来自磨牙,而且他们都习惯剔牙,以至于牙齿上磨出了凹槽。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男性和女性的身材差异不比今天更大——这与传统观点相悖,即更新世的男性猎人为了带回野牛,必须比留守家中的妻子大得多。阿苏阿加说,这就像我们是探险家,遇到一个新的人类部落,一种新的文化。我们可以直接了解他们的生与死,我们可以像研究现代人群一样研究他们。大约一年前,他请一位艺术家根据所有解剖信息,描绘了一幅西马人的画像,他们在更快乐的日子里,站在树下,仿佛在参加家庭聚会。
而对于生活在——或者更可能是在——50万年前的大洞穴的人们,目前还无法做到这一点。卡博内尔和他的考古团队分析了奥罗拉地层中与先驱人骨骼一起发现的约200件工具。即使在那个时代,这些工具也显得古老。早在150万年前,在先驱人据称前往欧洲之前,非洲的人科动物就已经在制造所谓的阿舍利工具:对称的手斧,两面经过精细加工,形成锋利而规则的切削刃。先驱人,由于不明原因,仍然停留在更早的奥尔德沃文化传统中。他们从阿兰松河中捡拾石英岩卵石,带回洞穴用作锤子;有时,他们会匆忙地从卵石或燧石上敲下大片石片,将石片用作简单的刀具,而石核则作为一次性砍刀来敲碎手头的骨头。
他们敲碎了许多骨头。他们吃鹿肉、野牛,可能还有一点大象和犀牛肉——也吃人肉。约兰达·费尔南德斯-哈尔沃(Yolanda Fernandez-Jalvo),一位说话轻柔的年轻女性,现在在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她将史前屠宰作为她的专业之一,她用显微镜检查了1994年至1996年在大洞穴发现的所有86块人类骨骼。她说,其中一半,包括该遗址发现的所有六个个体遗骸,都显示出人造痕迹——例如,只有石器才能造成的锐利切口,而不是食肉动物的牙齿或爪子。诚然,最近的人类曾为了祭祀目的屠杀其他人,而不食用其肉。但费尔南德斯说,在大洞穴,人类骨骼与以相同方式切割的动物骨骼混杂在一起——被肢解并剥去所有可食用的部分。一个四岁儿童的锁骨就是这样处理的。费尔南德斯说,如果你对这个人有任何尊重,那么如此用力地敲碎骨头,剥离它们——那是在寻找骨髓,那是身体中蛋白质最丰富的部分。所有椎骨都是这样断裂的。他们喜欢椎骨。
在大洞穴,似乎没有一块骨头来自曾在那里扎营的人科动物;所有骨头都来自在那里被食用的原始人。进行捕食的人随后离开了,没有死在洞穴里——至少没有死在已经挖掘的部分。这些捕食者可能是一个敌对的先驱人部落,在战斗中获胜;他们也可能是同一家族的成员,食用已经饿死的亲属。卡博内尔的假设,在阿塔普埃尔卡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因为证据仍然很少,那就是这根本不是同类相食。在意大利切普拉诺,1994年,就在大洞穴化石发现之前,发现了一个单独的脑颅,其年代可能与那些化石一样古老,其发现者称之为直立人。(这存在争议。)卡博内尔认为,如果直立人存在于切普拉诺,那么它也可能存在于阿塔普埃尔卡,食用先驱人。他说,我的大胆假设是当时欧洲存在几种人类。总是所有东西都在非洲,欧洲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这不合逻辑。
那个产出“先驱人”的小型试掘坑,现在已经到达壕沟墙壁的一半以下。但卡博内尔和贝穆德斯再次从洞穴顶部开始,这次挖掘的面积更大,大约800平方英尺,环绕着最初的挖掘点。到去年7月底,二三十名挖掘者已经完成了洞穴顶部相对贫瘠的沉积层。明年7月,他们应该会穿透来自30万年前“西马人”时代的沉积物。卡博内尔希望能找到他们的营地:他们的工具,包括用于将兽皮制成衣服的刮刀,一个火炉,甚至可能是一件艺术品——简而言之,就是证明“西马人”过着像我们一样复杂生活的证据。卡博内尔说,我们挖掘是为了找到了解我们自己的基本事物。这项研究的全部意义在于:自我认知。
再次深入奥罗拉层,也许能找到食用先驱人的人——如果这就是我们所需的自我认知——那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卡博内尔估计需要十一年。阿苏阿加说,我等不及了。我们不会等到退休。也许六年。一位实际参与挖掘的人说,二十年。无论何时——卡博内尔已经在规划下一次挖掘了。他说,在某些时候,阿塔普埃尔卡山脉有很多人。我认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大的沉积层。壕沟是零散的。在大的洞穴里,我们会找到连续的居住序列,我们会展示出山脉的吸引力。埃布罗河和杜埃罗河是连接西班牙北部两大流域——而阿塔普埃尔卡就在它们的中间。
其中一个大洞穴距离大洞穴几英里,位于山脉的南端,靠近山顶。它宽阔的洞口,像一个半开的蛤壳,通向一个凉爽宽敞的庇护所。前方有一个露台,阳光普照,覆盖着高高的草和野花,可以俯瞰阿兰松河谷,远眺德曼达山脉。现在,河谷里有布尔戈斯公路和一个军事基地,但在80万年前——当时气候与现在相似——那里一定点缀着橡树和橄榄树,有野牛、鹿和大象在此放牧。即使像先驱人这样的游牧民族,人们想象,也会有在此停留一段时间的意识。卡博内尔和他的同事们对这个洞穴的挖掘寄予厚望。他们称之为Cueva Mirador——粗略翻译过来,意思是“有风景的洞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