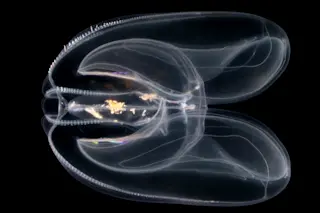四年前,考古学家艾莉森·布鲁克斯(Alison Brooks)和约翰·耶伦(John Yellen)发现了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人类文化痕迹。唯一的问题是,没有人相信他们。有时他们自己也难以置信。
他们的发现是在扎伊尔靠近乌干达边境的一个偏远角落,一个阳光普照的山坡上,名叫卡坦达(Katanda)。三十码下方,塞姆利基河(Semliki River)清澈凉爽,水下河马看起来像巨大的玉石块。但在发掘现场,高温足以让人怀疑自己的眼睛。
卡坦达离冰河时代的欧洲平原很远,考古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那里是真正现代文化首次出现的地点:新工具技术、艺术和身体装饰的繁荣,被称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始于大约4万年前。几年来,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考古学家布鲁克斯一直在追求一个异端假说:非洲的人类甚至更早地发明了复杂的技术,而他们的欧洲同伴仍然使用着他们已经使用了几十万年的同类工具。如果确凿的证据没有出现,那只是因为没有人真正费心去寻找它。
布鲁克斯说,仅法国就有大约三百个我们称为中石器时代的发掘良好遗址。而在整个非洲,只有不到二十几个。
那二十几个遗址中有一个就是卡坦达。1988年一个下午,约翰·耶伦——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考古项目主任,也是布鲁克斯的丈夫——正在挖掘一堆密密麻麻的巨型鲶鱼骨头、河石和中石器时代石器工具。他从碎石中取出了一个制作精美的化石骨鱼叉头。最终又发现了两个完整的鱼叉头和五个其他碎片的鱼叉头,所有这些都带有精细的倒钩并经过抛光。几英尺外,科学家们发现了几件同样制作精良的匕首状工具。在设计和工艺上,这些鱼叉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期(大约14000年前)的鱼叉并无二致。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布鲁克斯和耶伦认为约翰所站的沉积物至少是那个时期的五倍古老。为了理解这一点,想象一下在列奥纳多·达·芬奇的阁楼里发现一辆原型庞蒂亚克轿车。
布鲁克斯说:“如果这个遗址像我们认为的那么古老,它就可以证明现代人类是在非洲进化的。”
自从发现以来,这对夫妇一直致力于削弱那个顽固的小词“如果”。面对同事根深蒂固的怀疑,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他们确实有一些优势。在卡坦达发现第一个鱼叉的四年里,一项突破重振了现代人类起源的问题。这项突破不是从地下挖出的新骨架。也不是遗传学家提出的、广受关注的夏娃假说,该假说认为地球上所有现代人类都共享一个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女性共同祖先。真正的进步,在夏娃吸引众人目光的同时悄然存在,仅仅是一种新的测定时间的方法。
准确地说,这是一系列新的测定时间的方法。最近,它们都汇集到了同一个令人振奋、令人羞愧的发现:我们自以为对我们物种起源所知甚少,却错得离谱。从非洲到中东再到澳大利亚,新的测年方法以一种傲慢不羁的方式颠覆着传统观念,让人类学界在 collapsed 的确定性废墟中目瞪口呆。正是在这种震惊的气氛下,艾莉森·布鲁克斯在达芬奇阁楼里的“庞蒂亚克”才有可能得到听证。
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考古学家迈克尔·梅尔曼说:“十年前,我会说这些鱼叉不可能这么古老。现在我持保留意见。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手持刚出土的头骨、石器或骨骼庞蒂亚克的考古学家可以通过两种普遍方法来确定其年代。第一种是相对年代测定法。本质上,考古学家将发现物置于周围地质沉积物的背景中。如果新发现物是在一层棕色沉积物中,而这层沉积物又位于一层黄色沙子下方,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就比黄色沙层或任何更高处的沉积物更古老。在物体附近发现的灭绝动物化石遗骸也提供了生物地层记录,可以为新发现物的相对年代提供线索。(如果在一个石器工具旁边发现了一种已灭绝的马类,那么很有可能这个工具是在这种马仍然存在的时期制作的。)有时,工具本身也可以作为参考,如果它们的特征和风格与其他已知遗址的工具相匹配。像这样的相对年代测定方法可以告诉你一个发现物比另一个发现物更古老还是更年轻,但它们无法以日历年为单位确定物体的年代。
最著名的考古年代绝对测定法——放射性碳定年法,是在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植物从大气中吸收碳来构建组织,其他生物又以植物为食,因此碳最终存在于从木材到土拨鼠的一切事物中。大多数碳以稳定的碳12形式存在。但有些是由不稳定的放射性碳14形式组成。当一个生物体死亡时,它含有与大气中碳12和碳14大致相同的比例。死亡后,放射性碳14原子开始衰变,变成稳定的氮原子。然而,碳12的量保持不变。科学家可以查看碳12的量,并根据比例推断出最初存在多少碳14。由于碳14的衰变率是恒定稳定的(每5730年就有一半消失),因此,一块烧焦的木头或骨头中最初的碳14含量与现在存在的碳14含量之间的差异,可以作为确定物体年龄的时钟。
传统的放射性碳测年法在4万年以内非常准确。这是迄今为止测定发现物的最佳方法——只要它比这个截止点年轻。(在更古老的材料中,尚未衰变的碳14含量极少,即使实验过程中最微量的污染也会导致高度不准确的结果。)另一种测年技术,依赖于放射性钾而非碳的衰变,可用于测定超过50万年的火山沉积物。当它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被发现时,放射性钾测年法为人类家族的早期成员——南方古猿(如著名的露西)及其更先进的后代——能人(Homo habilis)和直立人(Homo erectus)的出现打开了一扇窗。然而,直到现在,50万年至4万年之间的时间段——恰好包含了智人起源的时间段——通过绝对测年技术几乎是无法得知的。就好像一道地质年代学帷幕遮蔽了我们物种诞生的奥秘。在那道帷幕之后,人科谱系经历了惊人的蜕变,进入了无年代、黑暗的几个世纪,最初是一种略显早熟的两足猿,最终以我们称之为现代人类的文化辉煌、口若悬河的存在,进入了放射性碳测年法的范围。
十五年前,关于这种变化如何发生有一些普遍的共识。首先,大约35000年前,具有当今人类的圆颅、垂直额头和轻巧骨骼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出现在欧洲。其次,伴随着这些最早的现代人类,也就是俗称的克罗马农人,出现了复杂人类行为的最初迹象,包括骨制、鹿角制以及石制工具,以及艺术、象征、社会地位、族群认同,可能还有真正的人类语言。最后,在任何一个地区,现代人类的出现与经典尼安德特人等古人类的消失在时间上没有重叠,这支持了一个群体从另一个群体进化而来的观点。
“多亏了新测年法的努力,”北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家弗雷德·史密斯说,“我们现在知道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
对传统观念造成最大冲击的技术被称为热释光,简称TL。(读者请注意:地质年代学领域充满了足够长的术语,可以绑在两棵树之间绊倒,所以缩写是必须的。)与对有机物起作用的放射性碳测年法不同,TL从石头中提取时间。
如果你从地上捡起一块普通的石头,并试图描述它的基本石性,那么像“狂热地活跃”这样的词语可能不会立刻浮现在脑海中。但事实上,矿物处于不断地内部骚动状态。岩石本身以及周围的土壤和大气中微量的放射性元素不断轰击着它的原子,将电子从它们的正常轨道中击出。所有这些都是完全正常的岩石行为,在晃荡了一百分之一秒或两秒之后,大多数电子都会尽职地回到它们的正常位置。然而,少数电子在途中被困住——物理上被捕获在晶体杂质或矿物结构本身的电子异常中。这些微小的“监狱”会 удержи住它们的电子,直到矿物被加热,此时陷阱打开,电子返回到它们更稳定的位置。当它们逃逸时,它们以光的形式释放能量——每个回家的电子都会释放一个光子。
热释光现象早在1663年就被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罗伯特·玻意耳观察到。一天晚上,玻意耳带着一颗借来的钻石上床,原因至今不明。当钻石放在我赤裸身体的温暖部位时,玻意耳注意到它很快发出温暖的光芒。他对这颗会“响应”的宝石如此着迷,以至于第二天他在皇家学会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并指出他对这种光芒感到惊讶,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体质并不是最热的。
三百年后,另一位英国人,牛津大学的马丁·艾特肯,发展了将热释光转化为地球物理计时器的方法。这个时钟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轰击矿物的放射性相当恒定,所以电子以稳定的速度在这些晶体监狱中积累。如果你将要测年的矿物碾碎,并将几粒加热到足够高的温度——大约900度,这比罗伯特·玻意耳的体质所能产生的体温高得多——所有的电子陷阱都会立即释放它们的俘获电子,产生一道耀眼的光束。在实验室中,这种发光爆发的强度可以用一种叫做光电倍增管的装置轻松测量。光峰越高,样品中积累的被俘获电子越多,因此自上次暴露于热量以来经过的时间就越长。一旦矿物被加热,所有电子都返回原位,时钟就会归零。
如今,我们人类祖先已经制造燧石工具数十万年了,在那漫长的史前时期,我们也开始使用火。不可避免地,我们一些不太细心的祖先会将废弃的工具踢入燃烧的火炉中,从而使它们的电子钟归零,为现在热释光计时员提供了一个成熟的机会。火熄灭后,那些燧石躺在地下,受到放射性的冲击,每个被困的电子都像时钟的另一个滴答声。通过实验室加热释放,电子会闪烁出光子,揭示流逝的时间。
20世纪80年代末,巴黎附近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低辐射中心考古学家埃莱娜·瓦拉达斯(Hélène Valladas)及其父亲、物理学家乔治·瓦拉达斯(Georges Valladas)通过对以色列两处考古遗址出土的烧焦燧石进行热释光测年,震惊了人类学界。第一个遗址是名为凯巴拉(Kebara)的洞穴,该洞穴已出土一具保存惊人完整的尼安德特人骨架。瓦拉达斯测定尼安德特人所在地层的燧石年代为距今6万年。
这本身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个年代完全在尼安德特人在地球上已知的时间范围内。真正的震惊发生在一年后,当时她使用相同的技术,对附近一个名为卡夫泽(Qafzeh)的洞穴中的燧石进行了测年,该洞穴含有早期现代人类的埋藏遗骸。这一次,发光峰值转化为大约92000年的年代。换句话说,更先进的人类类型比他们理应演变而来的尼安德特人早了整整3万年。
如果瓦拉达斯的热释光测年结果准确,它们将彻底颠覆现代人类以任何整洁有序的方式从尼安德特人进化的观念。相反,这两种人类,在文化上同样富有,但在外貌上截然不同,可能在中东的同一小块地方共享了数万年。对一些人来说,这简直说不通。
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的考古学家安东尼·马克斯担心:“如果这些年代是对的,那我们所知的其他一切,比如地层学、化石人类、考古学,都会发生什么?一切都乱套了。这并不是说年代一定是错的。但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它们的信息。”
马克斯的怀疑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尽管理论简单,但在实践中,TL 必须克服一些棘手的并发症。(科罗拉多大学地质年代学家吉福德·米勒说:“如果这些新技术很容易,我们很久以前就想到了。”)要将燧石加热时发出的光脉冲转换为日历年,必须知道该特定燧石对辐射的敏感性以及自被火归零以来每年接收的放射线剂量。可以通过在实验室中用人工辐射轰击样品来确定其敏感性。而每年从样品本身内部接收的辐射剂量可以通过测量样品中含有多少铀或其他放射性元素来相当容易地计算出来。但是,确定从样品周围环境——周围土壤中的放射性以及大气中的宇宙射线——接收到的年度剂量则是一个更不确定的命题。在某些地点,这种环境剂量在数千年间的波动可以将从 TL 得出的绝对年代变成一场绝对的噩梦。
幸运的是,对于瓦拉达斯和她的同事来说,Qafzeh燧石的大部分辐射剂量来自燧石本身。因此,那里现代人类骨骼的92000年日期不仅是迄今为止热释光测年法产生的最耸人听闻的数字,它也是最确凿的数字之一。
瓦拉达斯说:“卡夫泽的可靠测年结果只是运气好。只是碰巧内部剂量高而环境剂量低。”
最近,瓦拉达斯和她的同事诺伯特·梅西耶将他们的热释光技术应用于法国圣塞泽尔遗址。去年夏天,他们证实圣塞泽尔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只有36000年的历史。这个新日期,加上西班牙北部一些克罗马农人遗址的约40000年的新放射性碳测年结果,强烈表明这两种人类在冰川从北方推进时,在欧洲的同一个角落共存了数千年。
当瓦拉达斯忙于欧洲和中东的工作时,其他热释光测年专家为澳大利亚首次人类居住地提供了一些惊人的新日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澳大利亚大约在五千年前才被殖民。其推理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既然第一批白人定居者到来时,澳大利亚原住民仍然使用石器,他们一定只是最近才发展出能够从印度尼西亚进行艰难海路穿越的能力。十年后,考古学家不情愿地承认,首次进入的日期可能更接近全新世时期开始的1万年前。20世纪70年代,人类居住地的放射性碳测年将日期再次推回,远至3.2万年前。而现在,澳大利亚北部两处遗址的热释光研究将人类在这片大陆上迈出的第一步——以及在此之前的海上航行——一直推回到距今6万年前。如果这些日期成立,那么这些曾经被诋毁的现代原住民祖先在欧洲出现复杂文化的最初迹象之前约2万年,就已经在建造适于海洋航行的船只了。
“发光技术彻底改变了我所从事的整个时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考古学家里斯·琼斯说,他是负责新热释光测年团队的成员,“实际上,我们拥有了一台新机器——一台新的时间机器。”
然而,由于事关重大,没有人将热释光——或任何其他新的时间机器——视为地质年代学上的万能药。过去,一些测年方法言过其实,使得许多声誉受损。20世纪70年代,一项名为氨基酸消旋化技术的热潮让许多研究人员相信,另一个大陆——北美——早在7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对同一美国遗址的进一步测试证明,这种神奇的新方法完全偏离了十万八千里。这些遗址的真实年代接近7000年。
英国考古学家保罗·梅拉尔斯今年早些时候在伦敦皇家学会展示新测年技术的会议开幕时,不祥地警告说:“用错误的年代来工作是我们不能承受的奢侈品。错误的年代不仅会阻碍研究,甚至可能使其倒退。”
正是对这种灾难的恐惧——更不用说她自己的声誉可能会化为泡影的风险——使得艾莉森·布鲁克斯没有直接宣称她在扎伊尔发现了制作精美的骨制鱼叉,其年代比这类创作应有的年代早了4万多年。到目前为止,她论点的主要支持是她对另一个遗址,名为伊尚戈(Ishango)的重新测年,该遗址位于卡坦达遗址下游四英里处的塞姆利基河。在20世纪50年代,比利时地质学家让·德·海因泽林在伊尚戈发掘了一个富含鱼叉的水生文明,他认为其年代为8000年。布鲁克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该遗址的放射性碳测年将其年代推回至25000年。通过追踪伊尚戈和卡坦达之间共享的沉积层,布鲁克斯和她的同事确信卡坦达在地层学上更深——是伊尚戈的两倍甚至更古老。但是,尽管布鲁克斯和耶伦在会议上自由地谈论他们的鱼叉,他们尚未在学术期刊这个不容置疑的论坛上发表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
“正是因为没有人相信我们,所以我们想在发表之前把我们的论点做得滴水不漏,”布鲁克斯说,“我们想要年代确认年代再确认年代。”
鱼叉发现后不久,团队就开始了热释光(TL)工作。不幸的是,该遗址没有发现烧焦的燧石。然而,尽管TL对篝火等极端高温完全归零的材料效果最好,但即使是强烈的阳光也能释放一些电子陷阱。因此,即使是考古发现周围的普通沉积物也可能隐藏一个可读的时钟:它们在地表时被阳光漂白,一旦被自然过程掩埋,它们的TL计时器就开始计时。布鲁克斯和耶伦已从卡坦达采集了土壤样本进行TL测试,到目前为止结果令人兴奋——但也仅此而已。
“目前我们认为这个遗址相当古老,”马里兰大学地球物理学家艾伦·富兰克林说,他正与马里兰大学的同事比尔·霍尼亚克一起进行这项工作。“但我们不想给它定一个具体数字。”
正如富兰克林所解释的,用热释光(TL)对沉积物进行测年的问题在于,虽然一些电子陷阱可能很快被阳光漂白,但另一些则更顽固地 удержи着它们的电子。当样品随后在传统TL设备中加热时,这些顽固的陷阱会释放出可能在沉积物最后一次暴露在阳光下之前数百万年就被捕获的电子——用一个虚假古老的年龄来迷惑对年代渴望的考古学家。
布鲁克斯还有其他测年方法在进行中。最有前景的叫做电子自旋共振——或简称ESR。与热释光(TL)类似,电子自旋共振也是利用稳定积累在陷阱中的电子来制作时钟。但TL通过陷阱打开时发出的光的强度来测量这种积累,而ESR则是在俘获电子仍在陷阱中 undisturbed 时,字面意义上直接计数它们。
所有电子都以两种相反方向中的一种旋转——物理学家称之为“向上”和“向下”。(这里必须使用比喻,因为这种旋转的本质是量子力学的,只能用巨大的数学方程精确描述。)每个电子的自旋都会产生一个指向一个方向的微小磁力,有点像指南针的指针。在正常情况下,电子是成对的,因此它们的相反自旋和磁力相互抵消。但被捕获的电子是不成对的。通过操纵围绕待测样品施加的外部磁场,可以诱导被捕获的电子发生共振——即翻转并以另一种方式旋转。当它们翻转时,每个电子都会从同样施加到样品上的微波场中吸收有限的能量。这种微波能量的损失可以用探测器测量,它是捕获在陷阱中的电子数量的直接计数。
ESR在牙釉质上效果特别好,有效范围从一千年到两百万年。对布鲁克斯和耶伦来说幸运的是,卡坦达的鱼叉所在层也出土了一些肥美的河马牙齿。为了测定这些牙齿的年代,他们请来了安大略省麦克马斯特大学的亨利·施瓦兹,一位无处不在的资深地质年代学家。在过去的十年里,施瓦兹走遍了欧洲、非洲和西亚的约50个遗址,只要他的宝贵而深奥的服务被需要。
施瓦兹也出席了皇家学会会议,他在会上解释了ESR方法的优点和问题。优点在于牙齿是坚硬的遗骸,几乎在世界上每个考古遗址都能发现;而且ESR可以反复测试微小的样本——而发光技术则是一次性的。ESR还可以针对某些类型的电子陷阱,相对于将所有陷阱混为一谈的TL,提供了一些改进。
从负面来看,ESR与TL一样,都存在关于样品每年从环境中接收到的辐射量的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即使牙齿内部的辐射也不能保证随着时间推移保持恒定。牙釉质有一个令人讨厌的习惯,即在埋在地下时会从周围环境中吸收铀。牙齿含有的铀越多,被轰击出正常位置的电子就越多,电子陷阱填充的速度就越快。记住:你无法通过计算填充的陷阱数量来知道物体的年龄,除非你知道陷阱每年填充的速度。如果牙齿在5万年内含有少量内部铀,但在1万年前突然吸收了大量高放射性物质,那么基于牙齿当前高铀含量的计算会表明电子陷阱填充的速度比实际快得多。施瓦兹说:“最大的问题是,铀是什么时候进入那里的?牙齿是在三天内全部吸收的,还是铀随着时间逐渐积累的?”
混淆这个大问题的一个因素是样品在埋藏的数百年间周围存在的湿度:湿润的牙齿会更快地吸收铀。因此,最好的ESR遗址是那些条件最干燥的遗址。中东和非洲的沙漠是不错的选择。就现代人类起源而言,这项技术已经对以色列一个名为Skhul的洞穴中一些人类化石的年代定为大约10万年,这恰好支持了几英里外Qafzeh洞穴的92000年热释光测年结果。如果Skhul附近的一个尼安德特人洞穴的新ESR测年结果是正确的,那么尼安德特人也大约在同一时间存在于中东。同时,在南非,Border Cave遗址发现的一块人类下颌骨——正如一位研究人员所说,现代得令人难以置信——现在已被ESR测定为6万年,几乎是欧洲任何类似化石的两倍古老。
但是,现代人类行为的文化变化——例如卡坦达鱼叉所体现的复杂技术发展——又如何呢?施瓦兹在卡坦达的测年工作尚未完成,考虑到事关重大,他同样可以理解地不愿讨论。他谨慎地说,这个遗址具有很好的ESR潜力。我们这样说吧:如果最初的结果表明这些鱼叉根本没有那么古老,我们就会对它们说“那又怎样?”然后放弃。嗯,我们还没有放弃。
还有其他正在开发的测年技术,未来可能会为非洲现代性的主张增添更多确定性。其中一种叫做铀系测年法,它测量铀在碳酸盐(例如石灰岩和洞穴钟乳石)形成的任何物质中稳定衰变为各种子元素的量。其原理与放射性碳测年非常相似——例如,钟乳石中子元素的量表明该钟乳石存在了多久——优点是铀系测年可以追溯到50万年前。即使是被唾弃了15年的氨基酸消旋化法也正在卷土重来,这得益于一项发现:该技术在应用于多孔骨骼时不可靠,但在用于坚硬的鸵鸟蛋壳时却相当准确。
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一个考古遗址将提供机会,可以同时应用其中两种或更多的测年技术,以便它们可以相互验证。当被要求描述理想的遗址时,施瓦兹脸上露出梦幻般的表情。“我看到一个漂亮的人类头骨夹在两层非常纯净的流石之间,”他说,想象着铀系测年将那些洞穴石灰岩变成了时间标尺。“旁边躺着几颗大而厚实的河马牙齿,不远处还有一堆烧焦的燧石。”
即使没有施瓦兹的梦想之地,单独使用的测年方法也指向一个共同的主题:现代人类事件在不应该发生的地方出现了惊人的古老性。布鲁克斯不仅在卡坦达,而且在非洲大陆各地,早在距今10万年前,就看到了暗示复杂的痕迹。一种被称为石叶的经典石器类型,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标志,在一些南非遗址中大量出现,比旧石器时代晚期早了4万到5万年。非洲大陆甚至可能蕴藏着艺术和人类社会象征方面的最早线索:具有风格意义的工具;色彩斑斓、闪闪发光的矿物,除了其美丽之外别无价值,却在数百英里之外发现。克罗马农人越来越像是最后出现的现代人类并开始像人一样行动,而不是最早的。
“这对于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来说并非易事,”芝加哥大学的古人类学家理查德·克莱因说,“艾莉森的那些鱼叉不可能那么古老,这不符合我们的模式。”然后他耸了耸肩。“当然,如果她是正确的,那她确实做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时间会证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