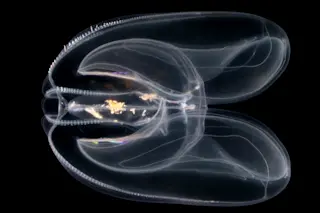马丁·诺瓦克看着一页页新的计算结果从打印机里涌出。他在他林肯市马萨诸塞州家中的小天堂里工作,那是一个有大窗户的房间,他可以看着鹿啃树,鸟儿在喂食器旁飞来飞去。他的16岁儿子菲利普走进这个圣地,拿起其中一页。上面有一张图表,看起来像一堆色彩鲜艳的丝带搭在桌子上,然后从边缘垂下。
“这是什么?”菲利普问。
“这是生命的起源,”诺瓦克回答说,他是一位生物学家和数学家,也是哈佛大学进化动力学项目的负责人。
男孩眯着眼睛看着那张纸。“是生命的真正起源,还是只是一种理论?”
“我的一生都只是一种理论吗?”诺瓦克假装绝望地呻吟着。诺瓦克在他的剑桥办公室里讲述了这个故事——那是另一个圣地,可以俯瞰哈佛广场,行人车辆在六层楼下的街道上形成复杂、不断变化的图案。他的意思很清楚:他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想法。他也非常认真地对待他的宁静。房间阳光明媚,他的书桌整洁。一幅罗马尼亚圣母像从房间的另一端平静地凝视着。
但最近,诺瓦克的严肃性严重干扰了他的宁静。2010年,他向进化生物学的心脏投下了一颗燃烧弹,挑战了内含适应性理论,这项长达数十年的理论认为,烈士可以通过保护亲属的基因在生存斗争中获胜。冲击波仍在回荡。
进化生物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借助内含适应性来解释“真社会性”物种,即那些生活在高度关联的结构中,同时有许多世代的物种。蚂蚁的蚁群主要由照顾母亲后代的无菌雌性组成,它们是真社会性的;白蚁也是。人类,凭借我们复杂的社会和各种各样的乐于助人者,在某些方面也像真社会性物种:年长的兄弟姐妹照顾年幼的;我们甚至与世界各地的邻居共享一个跨国空间站。我们说诸如“我愿为你而死”之类的话。
这种行为甚至让查尔斯·达尔文也感到困惑:如果自然选择是为了个体在生存斗争中相互竞争,那么合作和其他无私行为是如何产生的呢?牛津大学生物学家比尔·汉密尔顿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所有这些友善行为的解释。他使用一个计算协作可能性的数学公式,声称已证明合作行为——定义为“即使会让我付出代价,我也为你做某事”——在个体为挽救亲属基因而牺牲时出现。即使他们死了,受益者也是家族血统及其集体DNA——包括他们自己的。于是,内含适应性理论诞生了。
在汉密尔顿提出他的理论近50年来,数百名科学家通过观察白蚁丘和蚁穴中的亲缘关系程度而获得了职业生涯。但诺瓦克坚称所有这些工作都微不足道。他与他的数学家同事科丽娜·塔尔尼塔和传奇社会生物学家E.O.威尔逊在两年前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抨击该领域精英的文章中指出,内含适应性的数学过于笨拙而无用。相反,诺瓦克称之为“超合作”的特质可以用基本的进化理论,特别是自然选择,更好地解释,因为它有自己的数学框架。
在诺瓦克对达尔文理论的重新解读中,利他主义的出现仅仅是因为它在生存斗争中给予了一些个体优势。幸存者将有益的、利他主义的基因传给他们的后代,如此循环往复,直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幸存者群体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可防御的巢穴。任何一个生物的动机可能都是自私的,但极端的合作是令人欣喜的结果。当个体被迫进入同一空间(例如,由于食物来源的邻近)时,大量合作个体的共同努力为每个人提供了更好的生存机会。亲缘关系和内含适应性远不如以前认为的那么重要。
没有亲缘关系作为支点,合作可以在更广泛的背景下被审视,影响整个进化过程。在诺瓦克的新计算中,合作不仅仅是进化的产物,而是一个引擎,与突变和自然选择本身一起推动着这个过程。“合作是进化的基本原则,”诺瓦克今天说,“没有它,你就无法在生命中获得建构或复杂性。每当你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比如多细胞生物或人类语言的进化,都涉及到合作。”
然而,合作很棘手。它可能是复杂性进化中的一种积极力量,但对于面临艰难选择的个体或群体来说,它往往是危险的。当朋友请你帮忙重新设计简历以争取你们都想要的工作时,你的帮助可能会促进牢固的友谊,但也可能让你失去工作。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协议可能有助于地球,但选择退出的国家可能会获利。
尽管如此,对于流氓叛逃者来说,优势是短期的,尤其是在更高级的物种中。“智慧生命伴随着破坏力,并以这种方式变得脆弱,”诺瓦克说。他设想,智慧生物可能在宇宙漫长的历史中多次进化,但由于缺乏合作基因而自我毁灭。唯一能够幸存的,是那些像我们一样,渴望和平相处的生物。如果他是对的,那么超合作的驱动力不仅仅是进化故事中一个有趣的旁枝末节。它位于我们为何存在的核心——那种他的儿子菲利普能够理解的真实答案。
诺瓦克对一项神圣进化理论的彻底否定激怒了进化生物学界。他的2010年论文发表后不久,137位科学家联名致信《自然》杂志,表达他们的愤怒。他们中的许多人谴责该杂志给诺瓦克发声的机会,并暗示这篇论文之所以发表,仅仅因为其作者来自哈佛大学。
“我觉得这种反应很有趣,”诺瓦克今天用他浓重的德语口音英语说,听起来惊人地像阿诺德·施瓦辛格。“为什么要去坚持一个毫无作用的理论呢?”他耸耸肩,仿佛在暗示这场风波并没有给他带来过多的焦虑。毕竟,他已经发展他的想法几十年了,他最近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他2011年出版的《超级合作者:利他主义、进化以及我们为何需要彼此才能成功》一书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诺瓦克从小就被父母培养成一个激烈的竞争者。作为在奥地利长大的独生子,他喜欢解决象棋和数学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这种热情得到了他父亲的鼓励。到1983年上大学时,他认为数学没有用,并宣布打算成为一名生物化学家,以便了解生命的基石。但后来诺瓦克在物理课上重新接触了数学。“教授提出关于自然的问题,我们必须通过计算来回答,”他说。“我发现这很吸引人——理解某事物意味着计算它——并意识到我想做理论工作。”
在维也纳大学,诺瓦克开始与理论化学家彼得·舒斯特合作,专注于RNA复制的数学。舒斯特喜欢每年带着他最优秀的学生去山区旅行,他们会滑雪一整天,然后回到小屋听讲座, communal 准备晚餐,晚上还有更多的讲座。在其中一次度假中,诺瓦克被维也纳大学的数学家卡尔·西格蒙德所吸引。炉火熊熊燃烧,西格蒙德向他们介绍了1950年设计的博弈论模型——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关注合作与自私之间的选择。表面上看很简单:你和另一个人因涉嫌犯罪活动被警方逮捕,并被关押在不同的牢房里。检察官分别拜访你们每个人,并提供一个交易。如果你坦白并指控你的同伙,而他或她保持沉默,你将被判轻罪,只服刑一年,而你的同伙将服刑四年。用游戏术语来说,你“背叛”了你的友谊。
如果你和你的同伙都拒绝交易并互相忠诚——在游戏的术语中保持“合作者”——你们都将被判轻罪并服刑两年,因为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你们任何一人犯更严重的罪行。如果你们都互相作证——也就是说,如果你们都互相背叛——那么警方将以重罪判处你们两人,但只给你们三年刑期,因为你们提供了部分证据。
显然,作为个体,你最好的选择是背叛。如果你告发你的同伙而他没有告发你,你只需服刑一年。即使你们都互相告发,刑罚也只有三年,而不是最高刑期。只有那些不背叛而同伙背叛的傻瓜才会在监狱里呆上四年,这是最高刑期。另一方面,当两个囚犯互相背叛时,他们的处境比他们都保持沉默时更糟。
诺瓦克对囚徒困境着迷,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数学方法来研究人类行为,更广泛地说,是合作的进化成本和收益。游戏的每一轮都会产生数字(监狱的年数可以被视为分数),不同的策略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所有这些都可以转化为计算。西格蒙德说,有了囚徒困境,人们可以用数学来审视我们社会生活中最棘手的难题:如何权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
在阿尔卑斯山度周末的剩余时间以及返回维也纳的整个过程中,诺瓦克一直与西格蒙德讨论这个游戏。第二天,他拜访了西格蒙德在维也纳数学研究所的办公室,该办公室与一个神学院共用一栋大楼,神父在一楼,数学家在二楼。“那里一片宁静,”诺瓦克说,他是一名罗马天主教徒,坚守自己的信仰。“在生物化学领域,我们总是搞破坏,而且有难闻的气味。但这里只有空荡荡的走廊,偶尔有人深思熟虑地走过。我惊讶于有人可以通过思考来谋生。”
1987年,诺瓦克决定与西格蒙德一起攻读关于进化数学的博士学位。他们的重点是囚徒困境及其无尽的迭代,现在用计算机和数学进行分析。
其他人已经使用囚徒困境研究了合作,其中最著名的是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他在1970年代举办了虚拟锦标赛。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向阿克塞尔罗德发送了“囚犯”的策略——关于何时合作何时背叛的指示——在电脑化的一轮又一轮比赛中运用。每一轮,策略都会获得分数;刑期越短,分数越高。
在数百轮的电脑模拟中,获胜的策略被称为“以牙还牙”:你在上一轮游戏中做了什么,我将在这一轮中对你做什么。这种策略依赖于直接互惠,在现实世界中比比皆是,特别是在生物彼此有历史的社区中。例如,如果邻居纽厄尔上周帮助修理了琼斯的坏割草机,那么琼斯更有可能为邻居纽厄尔换一个爆胎。这在动物界也同样适用:如果吸血蝙蝠上次未能找到猎物时,洞穴中的其他蝙蝠与它分享了血液大餐,那么它更有可能与它们分享血液大餐。
诺瓦克和西格蒙德认为阿克塞尔罗德的工作是数学上的一种优雅练习,但他们希望改变游戏,使其更直接地应用于进化中的具体问题。经典的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认为,合作的个体威胁到他们自身的进化适应度,因为合作总是涉及自我成本(分享血液的吸血蝙蝠自己获得的食物更少)。然而,生命充满了合作,从形成高级有机体的单细胞结合,到人类建造城市,再到蚂蚁建造复杂的公共巢穴。诺瓦克想知道,如果合作如此广泛存在,那么当自然选择似乎与之相悖时,哪些机制在起作用以增加合作呢?
1976年,英国物理学家罗伯特·梅勋爵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为理论生物学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在论文中引入了一些改变游戏和找出这些机制的新想法。梅认为,像阿克塞尔罗德那样的虚拟锦标赛可能无法准确地复制现实生活中的合作与背叛的相互作用。“我指出,许多计算机模拟的结果都依赖于[虚拟]人物决定并严格遵循某个策略,”梅说,“实际上,会有很多噪音和错误。你需要考虑到这一点。”
换句话说,真实的生物很少能完美地遵循一种策略。邻居琼斯通常会回报邻居纽厄尔的帮助,但如果琼斯刚和妻子吵过架,看到纽厄尔来请求帮助修补爆胎,他可能会决定不想弄脏自己的手。因此,诺瓦克和西格蒙德着手创建虚拟锦标赛,通过赋予虚拟玩家概率行为来允许噪音和错误。有些人可能会在伴侣在上一轮背叛后有80%的几率背叛;另一些人可能即使在上一轮伴侣背叛后也有50%的几率合作。这种概率行为增加了梅认为之前纯净模型所缺乏的噪音。
为了进一步将游戏条款置于一个合理的进化背景中,诺瓦克和西格蒙德赋予获胜玩家及其策略繁殖能力。在这个新版游戏中,虚拟玩家不仅仅在获胜时积累分数;他们会得到一个与自己完全相同的复制品,并配备相同的获胜策略。他们的后代随后取代了种群中的另一个玩家。游戏现在模仿了真实生物的发生情况:随机突变导致一些玩家拥有获胜策略,使他们能够获胜并传播这些策略,而另一些则死亡。在计算机玩了数千轮游戏之后,诺瓦克和西格蒙德将看到哪种合作或背叛策略在种群中占据主导地位。
正如诺瓦克和西格蒙德所预料的那样,“总是背叛”的方法在100代中取得了胜利。然后它让位于“以牙还牙”策略,持续了几代,两位科学家看着目光锐利的“总是背叛者”逐渐消失而欢呼。即使诺瓦克在1989年完成博士学位后,游戏仍在继续。然后他搬到英国,与梅在牛津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他与西格蒙德合作的第一个突破发生在诺瓦克带着电脑回维也纳度假时。检查他的虚拟世界时,他惊讶地看到了一个新的获胜策略的出现。后来被命名为“慷慨的以牙还牙”,采用这种策略的玩家偶尔会合作,即使对方已经背叛过。
诺瓦克从这些模拟中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进化信息。“我们所看到的是宽恕的进化,”他说,“慷慨的以牙还牙策略表明,我们从不忘记别人的好意,但偶尔会原谅别人的过失。这很有道理。以牙还牙可能会导致仇恨,但慷慨的以牙还牙则让你能够继续前进。”
随着游戏的进行,诺瓦克发现,尽管“慷慨的以牙还牙”是一种长寿策略,但它并非永远占据主导地位。仍然有一些“总是背叛者”存活下来,他们最终能够打破新的高度合作的现状。一个充满快乐合作者的社会很容易成为自私者的猎物,后者可以将事物再次推向弱肉强食的状态。但这种状态也会剩下一些合作者,他们最终会将事物再次推向大规模的慷慨。
我们在人类社会中一直看到这种模式。和平之后是战争,战争之后又是和平。帝国兴衰更迭。公司成长,吸引竞争对手的注意,失去市场份额,但随后可以重组(需要内部合作)并再次主导市场。似乎每一次合作和背叛的趋势都包含着其对立面的种子。但无论发生什么,诺瓦克意识到,总是有选择压力趋向于合作。
有一天,诺瓦克回到奥地利,和西格蒙德一起爬山,他们开始谈论那些彼此不太了解的人之间的合作,这种行为被称为间接互惠。虽然有些实验的产生漫长而艰辛,但诺瓦克在三周内开发了一个计算机模拟程序,解释了间接互惠。在这个游戏中,就像囚徒困境一样,玩家要么互相背叛,要么互相合作,但只进行一次——他们无法根据之前与其他玩家的经验来决定如何行为。但诺瓦克还增加了一个机制,让玩家建立声誉,声誉根据他们的合作行为历史而上升或下降。正如他所预期的那样,声誉良好的玩家比声誉不佳的玩家获得了更多的合作。
诺瓦克坚信,声誉的力量,或间接互惠——愿意与陌生人合作——是人类合作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由于合作在人类发展中如此重要,他得出结论,处理声誉的需求是推动语言和我们强大大脑发展的主要因素。
“从很早开始,选择压力就集中在群体内的社会互动上,”诺瓦克说。“你需要足够聪明,能够监控群体内的社会互动,理解行动的动机和意图。你需要能够记住它们,你需要能够谈论它们。在此之前有一种理论认为大脑袋使语言成为可能,但我相信恰恰相反——是语言的需求创造了大脑袋。”
在研究群体合作的兴起近二十年后,诺瓦克通过囚徒困境的视角看待整个世界:他总是在寻找合作与背叛之间的张力。2006年,他在日本的一次会议上,因旅途劳累而产生了某种顿悟。他在脑海中思考,就像神学院的数学家一样,他列举了五个关键机制,这些机制推动了我们这类高度社会化物种的合作。
第一个机制是“以牙还牙”,或称直接互惠——“如果你这样做,我也会这样做”——这代表了囚徒困境模拟中合作的首次爆发。
接下来是更高级的间接互惠机制,即声誉,当一个人愿意帮助另一个人,不是因为个人经验,而是因为其他人描述过与该人有过良好的前期接触。
诺瓦克将第三个机制定义为“空间选择”——因生活邻近而产生的互动。在小范围内,社会网络有助于生存,合作蓬勃发展。
第四是多层次选择,涉及城镇、部落或公司等更大群体。这些结构鼓励其成员之间的合作。
第五种机制是熟悉的亲属选择的一种变体,即与血亲合作的倾向。诺瓦克认为血缘关系可能发挥作用——但这种作用更多地由社会合作而非家族基因的传播来定义。
诺瓦克也对存在他遗漏的其他合作策略的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如果找到了,那将是令人兴奋的。我会非常高兴——我必须弄清楚它为何发展以及我为何遗漏了它。所有这一切的美妙之处在于它是如此开放式,”他说。
如今,诺瓦克正在剑桥捍卫并完善他重新定义的进化理论。来访者试图找到他的藏身之处时,可能会被一楼的一家大型体育用品商店所迷惑。这怎么可能是一栋包含科学研究中心的大楼呢?当抵达六楼时,景色也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电梯门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一张乒乓球桌、一堆破旧的球拍和几辆自行车。再往里走,一个两侧是华丽罗马柱的门廊通向教室和办公室,走廊是紫色的,点缀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民间面具。“我希望人们进来后不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诺瓦克被问及装饰时说。
罗马柱是一个视觉双关语:他的研究中心有一个名为“数学进化研究机会”(ROME)的项目。“参与者被称为罗马人,”他说,“如果很多人申请,我们说这不足为奇,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一个项目不成功,我们说没关系,因为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诺瓦克的进化动力学项目现在有15位同事从事各种课题,将进化数学扩展到远至感染传播等领域。应用于艾滋病毒的模型表明,该病毒在体内传播如此迅速,以至于最好的治疗方法是使用多种药物迅速攻击它,为艾滋病鸡尾酒疗法提供了支持。
在首次组建ROME项目时,诺瓦克偶然读到E.O.威尔逊的一篇驳斥内含适应性的论文,这篇论文似乎被其他科学家们普遍忽视了。诺瓦克从他自己对囚徒困境的研究中得知,合作的产生并非始于或需要亲缘关系,正如汉密尔顿的支持者所认为的那样;在他的游戏模拟中,合作可以在任何相互作用的玩家之间蓬勃发展。他读过其他科学家运用内含适应性进行研究的论文,并发现其数学是无稽之谈。
诺瓦克和威尔逊开始讨论他们对该理论的共同不满。不久,科丽娜·塔尔尼塔也加入了进来。当他们三人阐述各自的观点时,威尔逊拿出一个达尔文的摇头玩偶,并操纵它表示同意。“正如英国人所说,我们知道这会‘搅动鸽笼’,”威尔逊说。“我们预料到了。我们从1921年发表的一篇题为《100位物理学家反对爱因斯坦》的文章中得到了慰藉。”
正如爱因斯坦1905年关于狭义相对论的论文一样,2010年《自然》杂志的论文传递了一个简单的信息:牺牲自己以保护亲属基因并不能驱动社会生物的进化。相反,合作是为了保护社会群体而产生的,无论成员之间的亲缘关系有多近。
这种对现状的全面攻击通常不会顺利进行。“我……不知道《自然》杂志的编辑在发表这篇论文时在想什么,”非营利性罗宁研究所的生物学家乔恩·威尔金斯写道。内含适应性“确实改变了对社会特征感兴趣的野外生物学家所收集的数据类型,”他的同事琼·斯特拉斯曼说,她研究内含适应性如何控制黏菌的行为。在汉密尔顿提出他的理论之前,“人们根本不知道从微生物到这么多动物都能说,‘你是我的亲戚;你不是。’”芝加哥大学生物学家杰里·A·科因总结了许多同事的观点,他写道:“如果《自然》杂志聘请了称职的审稿人,并听从他们的建议,[这篇论文]永远不会发表。”
这种激烈的反应震惊了诺瓦克阵营的人。“对此有一种奇怪的愤怒,”化学家、前《新科学家》杂志编辑罗杰·海菲尔德说,他是诺瓦克《超级合作者》一书的合著者。“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报道科学争议。通常,如果其他研究人员不喜欢你的论文,他们会极力避免表现得像个眼睛斜视、口吐白沫的狂怒者,但这正是他们做出的反应。”
海菲尔德想知道,这种愤怒是否部分源于担心任何对公认进化理论的挑战都可能被用来削弱进化本身。“一些人感到不安,认为你会为神创论者和智能设计论者提供弹药——他们会说,‘啊,这表明达尔文理论存在缺陷,’”他说。也许诺瓦克成为了一个众矢之的,因为作为一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在一个大多数人将自己的宗教倾向(如果有的话)藏而不露的领域中显得格格不入。但梅、海菲尔德以及其他与诺瓦克合作过的人都认为他的信仰不影响他的科学。“马丁只是试图将进化建立在严格的数学基础上,”海菲尔德说。
尽管关于内含适应性的争论最近占据了大量关注,但诺瓦克更广泛的观点似乎正在站稳脚跟。“马丁所说的是,合作是意料之中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进化理论家大卫·克拉考尔说。“我们认为亲社会行为需要奖励和指导我们行为的制度。教堂、法律结构和官僚机构都在那里,以缓和人类所谓的先天倾向。马丁的重点是,这不是完整的情况。合作不需要地方法院。”
它是帮助我们进化的生物学内在组成部分。合作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核心。
部落合作 生物学家马丁·诺瓦克确定了推动合作进化的五种机制。其中最强大的一种是群体选择:在部落等群体之间的竞争中,联系更紧密、成员更合作的群体往往会胜出。
家族内部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多数进化生物学家认为合作行为源于个体确保近亲基因存活的需求。诺瓦克不同意:他认为所谓的亲缘选择只是推动更普遍合作冲动的几种机制之一。
邻里互助 研究表明,个体倾向于为居住在附近的群体利益而牺牲自己,无论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有多近。
我亦然,你亦然 最基本的合作形式,被称为直接互惠,当个体在期望将来也能得到类似待遇的情况下,为他人做一件好事时,这种合作便会产生。
克里斯汀·奥尔森是克利夫兰的自由记者、散文家和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