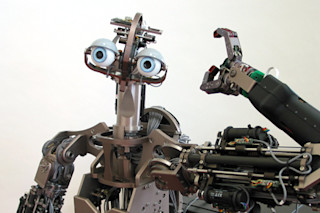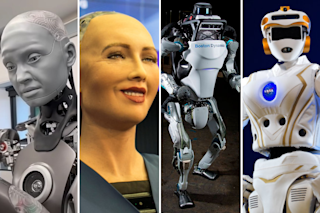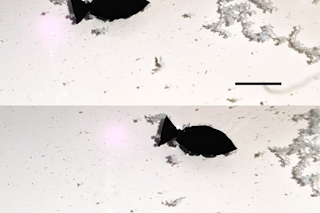乔什·邦加德(Josh Bongard)的生物被唤醒时——他必须先打开它们——它们显然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它们左右摇摆,扑腾乱舞,不是发现自己有身体,而是发现身体的存在;不是发现自己能动,而是发现运动是可能的。渐渐地,它们变得更加确定——你可以说,更加有意识。随着它们的成长,你会感觉到,从内心深处传来一阵胜利的欢呼,就像蹒跚学步的孩子迈出第一步。
邦加德的“婴儿”们,是机器与我们关系即将发生巨变许多早期迹象之一。自数千年前人工生命体的概念首次出现以来,问题一直不是它们能为我们做什么——能带来哪些服务或功能——而是我们将如何与那些既是人又不是人的实体建立关系。对此从未有过共识。弗兰肯斯坦的怪物是个悲剧,而皮格马利翁和伽拉忒亚则找到了幸福。
人形机器人此前只存在于小说中,但科学家们表示,这类机器可能很快就会在我们中间活动,担任医院护工和保安,照顾我们的老人,甚至成为友谊或性爱、亲情的对象。当我们进入这个新时代时,值得思考的是,这些机器人是否会表现出真正的情感或同理心。它们能否被设计成表现出忠诚或愤怒?
佛蒙特大学机器人学家邦加德认为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并补充说我们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回应。他表示,与机器人的情感关系“在不久的将来绝对是一种可能性。”“你已经看到了孩子们与玩具产生共情。我们许多人与宠物都有情感关系。那为什么机器人不行呢?”
足够聪明能为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机器,可能也能和我们一起做任何事情:一起吃饭,拥有财产,争夺性伴侣。它们可能对政治有强烈意见,或者像《太空堡垒卡拉狄加》中的机器人一样,甚至有宗教信仰。有些人曾担心机器人叛乱,但有那么多善于制动的侵权律师,更大的问题是:人形机器会丰富我们的社交生活,还是会成为一种新型的电视,破坏我们与真实人类的关系?唯一确定的是,我们知晓答案的那一天正在不断临近。
当然,直到现在,机器人仍然是相对粗糙的机器,每个都分配一个单一的重复性任务——与洗衣机或车床没有太大区别。它们通常是无实体的手臂或自动叉车。它们的原始工程师很少看到功能或设计与生物学模拟物绑定的理由;毕竟,飞机也没有羽毛翅膀。
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情况将发生变化。事实证明,机器越通用,它就越需要看起来和表现得像我们。凭借我们的双腿,我们可以转动、跳跃、踢腿、踮脚、奔跑、跋涉、攀爬、游泳并立即停止。我们有五个手指的手,配有可对握的拇指和柔软顺从的组织,可以握持和控制种类繁多的物体几何形状。我们的身体如此灵活,以至于我们几乎可以调动任何肌肉来完成操控世界的任务。
为了实现这种转变——爬我们的楼梯、操作我们的工具、在我们世界中导航——未来的机器人可能将拥有与我们近似的身高和体重、我们的手和脚、我们的步态和姿势以及节奏。柔软灵活的身体可能是机器在复杂、动态、受限空间中运行的先决条件,例如在人群中挤行。
这类人形机器人的一个明显家庭用途是照护我们日益老龄化的“婴儿潮一代”,这需要一种能铺床、购物、做饭、给药和洗澡的机器。军队对能在战场混乱中导航的机器的需求是无限的。社会各界都渴望能永久自我修复和维护的机器——像我们一样,能从经验中学习、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在需要时进化。纯粹从商业角度来看,你不需要成为艾伦·格林斯潘也能明白,机器能做的事情越多,市场就越大。
即使我们的物种看起来完全不同,我们最终可能还是会建造人形机器人来服务我们,因为这样做的好处会非常大。如今,世界各地有数十个实验室正在研究类人手、腿、躯干等,并非因为研究人员阅读了太多科幻小说,而是因为这种方法代表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最佳方案。他们建造人形机器人的努力各不相同,但都带来了贡献;最终,通过汇聚这些最佳努力,新一代机器人将会诞生。
身体的智慧
也许以我们自己的形象设计机器人最有趣的原因,是目前在机械工程和认知心理学研究人员中流行的一种新的智能理论。直到最近,包括心理学到人工智能(AI)在内的许多领域,普遍认为身体的控制权集中在大脑中。在机器人技术领域,这意味着传感系统会将数据发送到中央计算机(机器人大脑),计算机将努力计算出正确的指令。然后,这些指令(很像神经信号)将被分发到电机(作为机器人的肌肉系统),机器人就会按照指示移动。这种模型早在几十年前,当第一批计算机被制造出来时就被定义了,它从我们将大脑视为思想中心的概念中获得了权威性。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中央控制需要几乎无限量的编程,这实际上限制了机器人能做的事情。随着对活体生物如何运作的更深入理解,这些限制变得更加清晰:它们不是通过某种集中式任务控制的指令,而是通过与环境的分布式交互来运作的。
“传统的机器人模型是身体服从大脑,但在自然界中,大脑服从身体,”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的饭田史也解释道。决策源于我们身体材料的特性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当我们拿起一个物体时,我们能够握住它,主要不是因为我们的大脑说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柔软的手自动地围绕物体塑形,增加了表面接触面积,从而增强了摩擦附着力。当蟑螂遇到不规则表面时,它不会向大脑求助下一步该怎么做;相反,它的肌肉骨骼系统被设计成局部冲击会驱动它的腿到达正确的位置,以迈出下一步。

Domo是麻省理工学院CSAIL人形机器人实验室的新型上躯体人形机器人。| 图片Donna Coveney/MIT
发现这个事实的生物学家约瑟夫·斯帕尼亚(Joseph Spagna),目前在伊利诺伊大学任职,他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工程师合作,建造了一个受自然启发的机器人。名为RHex(因其六条腿而得名)的机器人,无需任何中央处理即可穿越各种地形。起初,它在带有大孔的铁丝网上移动时遇到了很多麻烦。斯帕尼亚的团队对机器人的腿进行了一些简单、受生物学启发的改动。在不改变控制算法的情况下,他们只是增加了一些脊椎并改变了机器人脚的方向,这两项改动都增加了机器人与网格之间的物理接触。这就是使设备前进所需的智能。在一个相关项目中,饭田和他的麻省理工学院团队正在建造尽可能少控制关节和电机的腿,他们称之为欠驱动的工程技术。
将我们所称的智能大部分归因于自下而上——即由身体——产生的理论,如今正在各地赢得支持。(饭田小组的非官方座右铭是“从运动到认知”。)这一观点的一些极端拥护者,被称为具身理论,他们推测即使是最高的认知功能,包括思想,也只不过是调节来自身体的智能流,就像收音机发出的声音通过调节旋钮来调控一样。具身理论表明,许多智慧确实是“身体的智慧”,就像那些令人烦恼的新时代大师所说的那样。
海星转身
邦加德和他的“孩子们”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像许多机器人学家一样,他对在不同地形(从沙地到岩石、草地再到沼泽)上导航的技术很感兴趣。几乎可以肯定,一台多功能机器将需要这项技能;一个家庭清洁机器人可能需要爬楼梯或梯子,爬墙,然后打蜡地板。旧的方法是设计一个中央计算机,识别新的地形和几何形状,并在数据库中存储特性,一步一步地指导机器人的步态。但这会失败,因为需要编程的变量太多了。“编程一台通用机器来预测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传统人工智能中的一个经典问题,”邦加德说。“它从未得到解决。具身理论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法。”
在邦加德的一个设备中,它像一个盘子大小的黑色四足海星,工作原理如下:启动后,海星开始笨拙地移动,同时记录身体的行为方式,并生成关于其部件在世界中如何运作的想法——比如关节a如何影响关节b,给定c单位的力,等等。然后,它将身体的实际行为与生成的模型进行比较,看看哪个模型做出了最好的预测,并将获胜的模型植入每一轮的行动中。通过类似基因重组的方式,海星解析并重新解析模型,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聪明。经过一定时间后,最聪明的模型被选为“执行官”——那个告诉机器人该做什么的部分。这个事件就像机器人的成年礼,标志着它准备好投入工作。现在,当它接到任务时,它会将其交给获胜的模型。模型会找出哪些关节和电机应该做什么,将这些指令分发给各个部件,然后机器人就开始工作了。在工作过程中,机器人会记录自己的表现。每当表现下降时,程序员就会指示机器人进化出一个可能效果更好的新模型。
邦加德说:“具身化让我们避免了植入人类的偏见。”“它让机器人自己找出适合自己身体的东西。”
我的机器人,我的自我
具身理论探讨了关于机器人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与它们的关系本质。许多多功能机器将作为协作的成员工作,包括人类和其他机器组成的混合团队。也许最明显的应用是士兵机器人,但任何有用的家用机器人显然都必须与其主人互动。
这些实体之间相互理解越容易,团队的效率就越高,这只是常识。如果智能,包括社交智能,是自下而上地从身体中产生的,那么确保所有成员拥有大致相同的身体将增强他们相互关联的能力。
例如,假设机器人鲍勃正在冰上行走时遇到困难。如果机器人爱丽丝自己学会了在冰上行走,她关于身体在类似情况下如何表现的记忆将有助于她识别鲍勃问题的性质。一旦她了解了情况,她应该能够通过立即向鲍勃传输正确的算法,甚至通过向他伸出援手来帮助他。如果机器人要通过模仿学习,这是我们所知的最强大的学习机制之一,那么我们的身体相似显然会很有用。
即使是口头交流也会变得更容易,如果我们的机器看起来像我们一样。“想象一下你对一个机器人使用‘竭尽全力’这个短语,”邦加德说。“机器人怎么会知道这是一种形容困难的比喻呢?程序员可以事先写进去,但他或她会永远写下去。这样的短语实在太多了。但如果机器人有和我们一样的身体,如果它有背部,那么它或许就能自己理解,自动理解。”
沟通远不止言语。坎迪斯·西德纳(Candace Sidner)是为军事承包商BAE Systems工作的人工智能专家,她是众多对能够理解和参与姿态交流的机器感兴趣的研究人员之一。这些非语言行为包括眼神交流、身体动作、姿势变化和手势。西德纳的特殊兴趣是参与度,即姿态中用于构建交流的往复部分的组成部分。她目前的目标是:建造一台能够同时与两个人进行对话的机器,弄清楚人类何时想互相交谈,以便它知道何时保持沉默以及何时发言。
然而,最终,正是物理上的相似性可能让人类以同样的方式回应机器人。“一旦你有了脸,”西德纳说,“人们就会期待在那张脸上看到某些类型的信息。如果看不到,就会觉得很奇怪,这种感觉增加了与机器人打交道的认知负担。”
计算机图形学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客观教训:一旦图像达到半现实的水平,市场就会要求更高水平的逼真度。未能达到完美会使使用者陷入有时被称为“恐怖谷”的境地,即缺乏真实感变得令人分心。这在动画电影中得到了体现
极地特快;
动画几乎完全逼真,除了人物的眼睛,这让几乎所有评论家都感到分心。
维持与机器人情感关系最困难的障碍可能是真诚的问题。这个实体真的关心我这个人吗,还是仅仅在操控我让我认为它关心我?克服真诚障碍的努力才刚刚起步。以最简单的问题为例:机器人需要多真实——多像人类——才能被接受为真诚?没有人确定,机器人学家们正在对各种可能性进行押注。南加州大学的Bandit II拥有一个简单的卡通脸,只有基本的面部特征活动能力。麻省理工学院的Leonardo有32个面部特征,对应32组机械肌肉,看起来像一只大眼睛、活泼耳朵的小动物。Kokoro的Actroid DER具有非常高的真实感,包括手臂和躯干的姿态。
我们都知道在与没有面孔的电子邮件搏斗时,我们常常需要看到对方的表情才能理解他们说的话。但是,我们可能不需要完美的真实感来建立真实的关系。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实验哲学家布莱斯·休布纳(Bryce Huebner)发现,他的人类受试者愿意接受机器具有“信念”甚至感受痛苦的可能性,但前提是这些机器拥有一张类人脸。休布纳怀疑,“如果人们愿意接受机器会感到痛苦,那么他们接受机器有其他感受,比如希望、愿望、梦想或恐惧,可能也不会太难。”当然,无论多么逼真,真实感本身是不够的。人类看起来也相当逼真,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却总是走向衰败。今年夏天,第一届人机个人关系国际会议将在荷兰举行。这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
机器人之爱
如果人类接受与机器的情感关系,这将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一层新的复杂性。一些专家认为这些新的联系本质上是没有威胁的。“我相信人类将与机器人建立个性化的关系,但我不会说它们会取代人类关系,”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从事人机交互与通信研究的机器人学家罗德·格鲁彭(Rod Grupen)说。“地球上有很多物种不会挑战我们与其他人建立的关系,”他补充道。
的确,麻省理工学院的谢里·特克尔等心理学家认为,机器人永远不会取代其他人,因为它们缺乏共同人类生命周期的基础。“我们由母亲所生,有父亲,我们会成熟,我们对生育做出决定,我们思考下一代,我们面对死亡,”特克尔说。“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一系列充满焦虑、喜悦、内疚和激情的复杂关系。作为人类,我们受制于我们的生命轨迹。”换句话说,缺乏共同的生物学将阻碍人类与机器之间最深层次的关系。
其他人则预测真正的亲密关系。国际电脑游戏协会主席大卫·利维(David Levy)在他的著作《爱与性与机器人》中分析了所有最困难的情况。他的核心观点是,心理学对任何类型的人际关系,包括性关系,都没有任何已知事实能排除与机器人建立类似关系的可能性。事实上,他认为,没有任何可以明确指出的人际关系回报能排除机器人提供更多这些回报的可能性,无论这些回报是什么。你对一个了解很多体育知识的伴侣感兴趣吗?很容易想象一个能满足这种需求的机器人。或者你更喜欢一个对体育一无所知但渴望学习的伴侣?这也很容易想象。
利维同意总会有一些东西让人类彼此感兴趣,但他没有说出那个“东西”是什么,书中也未提及。也许这只是一个虔诚的愿望。无论《爱与性与机器人》这本书还做了什么,它都让人思考人类物种是否会因为与性机器人调情而走向灭绝,这些机器人会毫不退缩地满足每一个情欲。
要避开这条路可能很难。具身理论表明,如果我们希望机器在最高水平上工作,我们就需要让它们接触我们的生活和世界。隔壁的机器人可能是巨额财富的继承者。它可能驾驶一辆时髦的红色敞篷车,或者成为你的国际象棋伙伴或朋友。
我们许多人肯定会觉得这一切令人毛骨悚然和不祥,但更好的功能性有其自身的逻辑。至少,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将改变我们更具特征的驱动力之一——即了解我们核心是谁和什么的需求。
“归根结底,机器人学关乎我们自身,”格鲁彭说。“它是模仿我们生活、探究我们如何运作的学科。”然而,正如所有工程师所知,你只有真正建造它,才能真正理解它;如果你能建造它,并且它能按设计工作,你就可以确信你了解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斯帕尼亚的蟑螂和邦加德的机器人海星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小步,未来还有更大的进展。
无论机器人学对人类物种是好是坏,一旦机器人拥有人形,关于我们本质之谜的旧有叙事很可能会被彻底改变。我们可能不得不学会与理解自我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