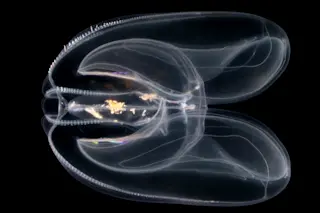时间总是向前流逝,当然,但进化呢?将进步的步伐强加在进化的过程中是很容易的。这就是为什么猿类进化成人类,从左到右行进的序列如此普遍的原因。当然,也有一些图片显示,智人(Homo sapiens)已经发展出高尚、直立的体态,又开始重新弯腰驼背,直到他(我注意到,从来不是她)弯腰驼背地坐在电脑或电视机前,或面临某种其他不光彩的结局。正如我在《寄生虫帝国》(Parasite Rex)中所写的,这种焦虑——主要是一种关于我们自身的焦虑,而不是关于自然的焦虑——促使生物学家提出了“退化”的概念。当大多数生命都在努力朝着更复杂的方向发展时,一些“落后者”又滑了下去。藤壶(曾是灵活的甲壳类动物)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如果一个谱系可以退化,那么它能否再生——它能否恢复其祖先失去的复杂性?1893年,法国生物学家路易斯·多洛(Luois Dollo)断然宣称不可能。进化要如此小心翼翼地重走老路来恢复某个丢失的特征,其可能性微乎其微。多洛法则在遗传学和现代进化生物学合成的兴起中得以幸存,尽管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不再像物理定律那样是不可动摇的法则,而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模式,说明了进化是如何运作的。如果一个动物谱系不再需要某些特征——例如眼睛——那么构建眼睛的基因就会逐渐发生突变,通常会变成死去的假基因。要让所有这些基因精确地变回它们以前的形式,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鲸鱼并没有重新进化出鱼鳍,而是进化出了桨状肢。为了纪念多洛法则发表一百周年,已故的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写了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他在论文中以卷曲的海螺壳作为新版、改进版多洛法则的证据。在某些腹足类谱系中,贝壳已经变得不卷曲。古尔德指出,不卷曲的贝壳允许腹足类灵活地绕过障碍物生长,或者向食物来源伸展。古尔德对其中一个群体进行了仔细研究,并认为其成员从未成功地重新进化出卷曲的贝壳。他认为,那些不卷曲的腹足类已经过于适应它们新的生活方式,以至于自然选择无法让它们恢复到以前卷曲的荣耀。现在,在多洛法则发表110周年之际,一项引人入胜的报告挑战了古尔德的观点。在一篇今天在线发表于《英国皇家学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的论文中,生物学家雷切尔·柯林(Rachel Collin)和罗伯托·西普里亚尼(Roberto Cipriani)研究了另一类腹足类——匙孔螺科(Calyptraeidae),其中包括 the slipper shell limpets、cup-and-saucer-limpets 和 hat shells。在200个物种中,只有十几个是卷曲的。过去人们认为,卷曲的物种首先分化出来,然后是其余物种的共同祖先失去了它的螺旋。但当生物学家通过对94个物种的三个不同基因进行测序来构建这些腹足类的家系树时,结果并非如此。他们发现,这些腹足类实际上在至少两个不同的场合重新进化出了卷曲的壳。起初这似乎难以置信。这些特殊贝壳的化石表明,在重新卷曲的物种出现之前,它们已经不卷曲了20到1亿年。卷曲的基因是如何在这段时间内得以保留的呢?柯林和西普里亚尼引用了今年早些时候一项关于竹节虫的研究。那项研究表明,一些竹节虫失去了翅膀,但它们的后代多次重新进化出了翅膀。这些重新卷曲的笠螺可能很少见,但它们并非偶然。这些谜题的答案似乎在于组装这些动物的基因。就竹节虫而言,建造翅膀的基因可能得以保留,因为它们在身体的其他部分还在做别的事情——它们建造了腿。柯林和西普里亚尼对贝壳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假设。重新卷曲的腹足类直接从卵中发育,但许多其他腹足类在其生命周期中有不同的阶段。作为幼体,它们会发育成一种贝壳,然后作为成体,它们会发育成一种全新的贝壳。柯林和西普里亚尼设想,一个谱系在成体贝壳中失去了卷曲,但在幼体阶段仍然保留了卷曲。因此,卷曲基因在数百万年里仍然处于活跃状态。然后,在一些谱系中,这些幼体卷曲基因被“借用”来建造卷曲的成体贝壳。最后,通过其他进化变化,这些腹足类失去了幼体阶段,简单地发育出不卷曲的贝壳。因此,进化似乎有时可以“回头走”。但前提是它将祖先的秘密保存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