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粒子狂热》具备了好莱坞大片的全部元素:一段史诗般的追寻、令人难忘的角色、充满张力的结局和一场宏大的碰撞场面。影片的结尾也让人期待续集。它还有一个浪漫的视角:影片的本质是科学家们与他们所追求的难以捉摸的真理之间的一段爱情故事。

这部纪录片带领观众走进位于瑞士日内瓦附近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幕后,从早期的试运行到2012年成功发现希格斯玻色子。《粒子狂热》巧妙地处理了科学内容,包括了那些提出解释宇宙方式的理论物理学家以及试图证实(或证伪)他们想法的实验物理学家的观点。但影片最大的优势可能在于其人文维度。影片跟随了六位处于职业生涯不同阶段(并且观点不同、常常相互矛盾)的科学家,展现了他们的个性、争执与情谊、奉献精神,以及偶尔的、理所应得的喜悦。
《粒子狂热》在2013年参加了国际电影节巡展后,将于今年春天获得更广泛的上映。(请访问particlefever.com查看最新的放映信息。)制片人大卫·卡普兰(David Kaplan),一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物理学家,他构思了这个电影项目并在片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与《Discover》杂志的Gemma Tarlach谈论了如何将多重宇宙理论带到你当地的电影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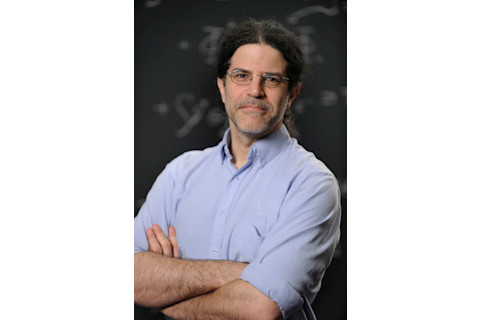
David Kaplan | Will Kirk/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Discover:您是如何想到要拍摄一部关于LHC和希格斯玻色子的电影的?
David Kaplan:我大学刚开始是电影专业。但我觉得电影太难了,所以转到了物理学。我发现它更容易。[笑] 但我意识到希格斯实验将彻底改变我们的领域——或者证明我们所做的一切可能都是徒劳的。电影是我最熟悉的媒介,所以七年前我开始带着摄像机去参加各种演讲,并与像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Sheldon Lee Glashow这样的人交谈。但我很快意识到,这部电影需要更有技术水平才能完成。
当您聘请了同样拥有粒子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导演Mark Levinson,以及凭借《现代启示录》和《英国病人》荣获奥斯卡奖的著名剪辑师Walter Murch后,您在电影中仅仅是出现在镜头前吗?
DK:我是一名物理学家,但在剪辑室里,我一直在那里,指导剪辑,确保他们忠实于事件。我们想展现作为一名科学家以及对未来感到不确定时的真实体验。
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它是出自一位活跃在物理学前沿的人之手,一位撰写论文、直接回应数据、情感投入其中、持有强烈观点并与科学界人士互动的人。我希望它能真正反映我所认识的世界。我拍这部电影是因为我希望它被拍出来,而不是因为我渴望拍它。
为什么您选择聚焦于对希格斯粒子的追寻?为什么不拍一部关于暗物质的电影呢?
DK: 希格斯实验是一个独特的机会。关于希格斯粒子,你可以预测:第一,LHC会证明它的存在;第二,它会证明它不存在;或者第三,它会证明它的存在,但不是按照标准模型预测的那样。但你可以预测一场革命即将到来。
但对于暗物质这类事物,我们有大量的间接证据表明,一种不属于我们已知物质组成的物质主导着宇宙,而且在最简单的理论中,LHC能够创造它。尽管有如此多的暗物质证据,但我们不知道它何时何地可以被创造出来。
现在希格斯粒子已经被证明存在,那么故事就结束了吗?
DK: 不,一点也没有。还有更多需要学习。例如,希格斯粒子本身并没有解释它的质量,或者它的机制最初从何而来。
看着LHC和各研究大学随着事件的展开而发生的戏剧性变化,真是引人入胜。感觉上,地球上的每一位物理学家都在情感上投入了对希格斯粒子的寻找。是什么让这次追寻对如此多的人来说如此个人化?
DK: 几十年来,我们没有经历过重大的新粒子直接发现。找到希格斯粒子让每个人都更加自信。找到希格斯粒子是一种巨大的解脱:谢天谢地,我们终于搞定了这件愚蠢的事,现在可以着手更深入的研究了。希格斯粒子几乎成了一种负担,因为我们通常不会坐着不动地等待。希格斯理论最早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理论研究不需要30到40年。但实验方面的进展非常缓慢,部分原因是这些实验非常难以进行,也因为社会政治原因。我们的领域仍然在从超级对撞机(一个原计划比LHC更大、但于1993年被搁置的德克萨斯州粒子加速器)取消的创伤后应激反应中恢复过来。
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您是否 tempted 去好莱坞发展?
DK: 就个人而言,我认为我还有一些物理学的东西要探索。我很乐意现在为人们的电影项目提供咨询,但我希望能把绝大部分时间花在做物理学上。我介于理论和实验之间。理论家可以在那里进行非常有创意的思考,设想可能发现其他实验错过的东西的实验。这就是我想思考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