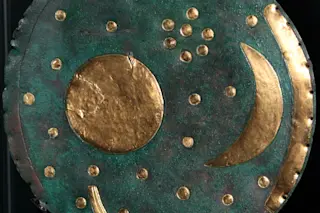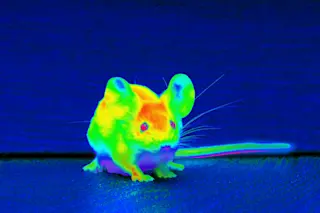地球比之前认为的缩小了五毫米的消息,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事件——我猜部分原因是五毫米不算多。五毫米大约是小指宽度的一半(对于那些仍然顽固地不学会使用公制的少数人来说,大概是五分之一英寸)。这是一个几乎微不足道的距离,五毫米。当然,与伟大的地球相比,五毫米的差异可能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对于那些像我一样,肩负着在科学杂志上撰写幽默专栏的特权的人来说,这绝对是值得大惊小怪的。如果说有什么早晨适合喝点香槟配早餐,而不是像往常那样喝几杯稳定的轩尼诗,那一定是这个早晨。一方面,你有像蒙提·派森式的荒谬,一种博尔赫斯式的怪诞,有人测量了地球,发现它小了五毫米。同时,与幽默密不可分的是几个无可置疑的实质性问题:这些人是什么意思,世界比他们想的要小五毫米?怎么能达到如此精确的程度?还有那个大问题:那又怎样?
我带着一种罕见的乐观精神前往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进行调查。要么这个五毫米的事情就像听起来那么可笑,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嘲笑在场的所有人,其中有些人,毋庸置疑,会留着胡子。要么,可能性较小,我发现它确实有什么严肃之处,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事情。
好了,我回来了。令我略感惊讶的是,是后者。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位于巴尔的摩以南20英里处,坐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周围如同情节剧反派翻动的披风般扩散开来的大片森林、封闭式社区和阴森森的政府机构之中。在铁丝网和面无表情的检查站后面,戈达德的建筑看起来低矮而没有窗户——即使是那些相对高一些或有窗户的建筑——使其成为“严肃思考”的重要前哨。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星球的新尺寸测量是由德国波恩大学的Axel Nothnagel教授完成的。然而,我现在却在马里兰州。如果你觉得这很令人费解,我恐怕你会暴露你在两个关键问题上的教育不足:这个笔下的作者,他碰巧不喜欢德国,还有特长基线干涉测量(Very Long Baseline Interferometry),这是Nothnagel用来以如此令人捧腹的精确度评估地球的技术。
我在这里是为了与两位对特长基线干涉测量有深入了解的人交流:戈达德空间大地测量学实验室的银河系外天体测量学专家Chopo Ma,以及IVS(国际VLBI服务)的协调主任Dirk Behrend。IVS的VLBI展开来就是(哦,瞧瞧)特长基线干涉测量。在一间位于戈达德特别没有窗户的33号楼深处的会议室里,这两位世界级权威调暗灯光,将地球的全息图像投射到屏幕上,并迅速与我分享了测量地球到最近毫米的精妙之处。
诀窍显然在于类星体。类星体是活跃的星系——非常遥远、非常活跃的星系,事实上,是宇宙中最遥远的、可探测到的天体。它们有多远?Ma相当随意地解释说,它们非常非常遥远,如果其中一个以光速横穿天空,在我们看来它似乎是静止的。当然,那是在你能看到它的时候,但由于它太远了,你实际上看不到。然而,听到它们是完全另一回事。类星体原来是庞大的无线电辐射广播者,从漆黑浩瀚的太空中发出柔和的爵士乐和模糊的交通信号的微弱低语。
它们的作用就在于此。由于它们非常非常遥远,并且在我们的天空中保持着几乎完美的恒定位置,类星体使我们能够以近乎完美的精度在地球上找到我们的参照系。通过收集任何特定类星体在世界各地不同地点发出的无线电信号,并测量信号到达不同地点之间微小的时间差,Ma和Behrend这样的人可以精确地知道这些地点之间的距离。
我带着几分羞愧提起了Nothnagel的五毫米问题,Ma以科学家们常常有的那种令人恼火的方式回答说,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他说,世界“是”也“不是”比之前认为的小了五毫米。这取决于长时间收集信息,并且由于VLBI,我们还知道地球在不断膨胀和收缩,并且在以使五毫米看起来像……嗯,像五毫米的量级上晃动。例如,整个固体地球每天被太阳和月亮的引力揉捏,会隆起约40厘米(16英寸)。
这并不是说Ma和Behrend认为Nothnagel的测量不重要。当大家似乎都在谈论全球变暖和冰川融化时,地球直径模型中五毫米的调整可能是在海平面在两年之间看起来上升还是下降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如果没有一个稳如磐石的银河系外参考点网络,我们可能无法检测到已经发生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是VLBI,我们可能会认为一切都很好。
当然,事情并非一切都好,或者看起来如此。冰川似乎真的在融化,海洋也确实在逼近。
然而,我以一种禅意的平静告别了Ma和Behrend。VLBI从业者自己也相当平静,想想看。科学家们常常是躁动不安的灵魂,充满急躁、野心、兴奋——但那两个人不是。我反复追问他们,对于VLBI从业者来说,是什么让他们心驰神往、在雨天也迫不及待地起床的那闪耀的圣杯……似乎并没有。在我们的谈话临近结束时,Ma最好的回答是耸耸肩说,也许VLBI的圣杯是“建立一套稳定的大地测量标准和测量方法”,这些标准和测量方法将需要不断更新……通过做Ma和Behrend这样的人已经在做的事情。
但你知道吗?如果有一天真的到来,很有可能它会彻底改变一切。
我们已经习惯了科学和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加剧人类的迷失感。心理学增强了我们的自我认知,但却动摇了我们的自我认同。量子物理学据我们所知,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解释整个宇宙,但我们是否有人感觉到即将到来的巨大赋权和理解的浪潮?恰恰相反。从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只言片语和预告来看,可以安全地断定,如果万物理论最终被发现,它只会给普通大众带来头痛、鼻血和困惑。哦,但它很简单!他们会喋喋不休地向我们保证,速溶汤的残渣在他们茬茬的胡茬上闪烁着绝望的光芒。我们怎么会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意识到,我们显然只是排列在一个九维莫比乌斯带上的无数宇宙中的一个,而时间和空间、物质和能量仅仅是四种不同频率的凝结概率的振动?
也许不一定如此。在一个漫长的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我们通过迷失的魅力来奉承和惊吓自己,那么,如果定向感终于要卷土重来了呢?当Ma、Behrend、Nothnagel以及其他人终于以完美的精确度完全绘制出世界地图时,如果它最终能让我们抛弃我们生活在相对主义和混乱的旋转、不可衡量的大潮中漂泊迷失的肤浅真理呢?如果我们开始认识到,几乎确切地知道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并不能代替确切地知道我们在哪里呢?换句话说,如果几乎确定自己的位置,最终会像轻微怀孕一样:一种持续的、啃噬性的焦虑,将你看到的一切都涂上末日般的预感色调?
也许在我们终于停止迷失的那天早晨,我们会醒悟过来,虽然是的,周围有混乱,现实的某些方面看起来很混乱,但并非一切都是如此。也许当我们不再感到迷失时,我们会再次感觉良好。因为它们就在那里,类星体,以完美的耐心和恒定性在宇宙的边缘等待着,就像沙坑边的父母,等待我们结束存在的愤怒,并向它们寻求支持。
我认为那将是美好的一天,我们终于,一次又一次,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之所以这么说,不仅是因为一个永远相信我们最好的日子还在前面的人,还因为一个卫星导航系统试图让我开过一个小悬崖,掉进一个砾石坑,就在我回机场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