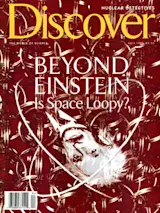尽管爱因斯坦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他至死未能实现自己最热切的梦想。这位我们这个世纪最著名的物理学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一套能够解释自然界在所有层面——从类星体到夸克——行为的综合性定律。他在二十多岁时已经证明了空间和时间是交织在一起的。随后,他又成功地展示了引力如何与这种弯曲时空的几何结构紧密相关。但是,当他试图将自然界的所有方面——所有的力和基本规则——编织成一块无缝的布料时,他失败了。无论他,还是其他任何人如何努力,新的量子力学科学就是无法融入其中。
如今,物理学家们仍然陷于同样的困境。自然界似乎遵循着两套互不兼容的规则。就好像物理学家被要求用跳棋去打保龄球,或者用打蛋器来发动汽车。在一个领域行之有效的工具,在另一个领域却完全不适用。他们不仅无法赢得这场游戏,甚至连开始都做不到。
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也称为广义相对论——至今仍在以令物理学家们惊叹不已的力量描述着宇宙最宏大的尺度。恒星、星系、黑洞的结构和动力学,乃至宇宙本身的形状和演化——所有这一切都是用爱因斯坦发展的工具来探索的。根据这一理论,引力并非源于物体发出的无形吸引力触手,将行星束缚于太阳,或将巨石固定在地球上。相反,引力是时空扭曲的结果。大质量物体会使柔韧的时空背景凹陷,就像巨石压在橡胶垫上一样。它们造成的凹陷会自然地吸引并常常捕获附近的物体,就像路上的坑洼会“吸引”汽车一样。广义相对论的语言描述的是一个平缓弯曲的时空,一个由山丘和盆地构成的景观,一个由平滑、连续的形态构成的流动。这种语言的字母是几何学;其词汇则由线条、角度、曲面、曲线组成。
然而,当我们把视线放大到亚原子层面,景象就突然改变了。爱因斯坦的规则不再适用。原子和核粒子像愤怒的蜜蜂一样嗡嗡作响。它们的能量和运动以离散的、跳跃模糊的小份呈现,其确切的行为和位置永远无法确定。在描述我们日常世界的物理学中经常使用的“总是”和“从不”这类词语,被“通常”和“很少”所取代。描述这种块状景观的语言是量子力学。要追踪这样一群疯狂跳跃的粒子,需要一套处理统计关系和事件概率的词汇。它的字母是代数符号和量子数:1、1/2、2。
试图用量子力学的规则来处理广义相对论(或反之)就像用圆的面积公式来计算你中彩票的几率,或者用概率论来测量房子的面积。然而,物理学家们正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们无法前进,直到找到一种共同的词汇,能让量子理论家与相对论者自由对话,让块状的微观世界与平滑的宏观世界在一个包罗万象的量子引力理论中结合起来。事实上,考虑到现实的图景如此迥异,物理学能够取得进展本身就有些令人惊讶。
当然,理解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比如火箭的飞行或保龄球滚下球道的轨迹,并不需要量子引力理论。现有的物理定律足以处理这些类型的问题。应用更精确的定律只会是浪费,就好像你用原子钟来确保自己准时到达机场一样。但量子引力在任何涉及极端精微之处,或引力集中、误差效应被极度放大的情况下都是必需的。这些情况包括一些科学中最棘手的谜团。
例如,我们已经很清楚,引力控制着恒星和星系的运动,但当一颗恒星中的所有物质被越压越紧,直到恒星的尺寸变成原子级别而非天体级别时,引力会做什么呢?当一颗特别巨大的恒星以超新星的形式爆炸,其残余核心在一瞬间坍缩成黑洞——那个任何光或物质都无法逃脱的引力深渊时,可能就发生了这种挤压。这个黑洞的核心是什么?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在试图描述其内部深处时会崩溃。计算结果会出错。理论家们为此付出的努力,只得到了一堆无穷大。
如果我们能将宇宙时钟倒拨约150亿年,回到大爆炸的时刻,那时可见宇宙中所有的物质和能量都被压缩在一个比亞原子微粒还小的空间里,那又会怎样呢?在那些地狱般受限的条件下,引力是如何作用的?这种行为又是如何产生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宇宙?至今无人能说。只有当物理学家能够将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融合,从而构建出一个成功的量子引力理论时,才能完全理解引力在亚原子尺度上的行为。
这就是为什么雪城大学的物理学家阿贝·阿西特卡 (Abhay Ashtekar) 和李·斯莫林 (Lee Smolin),以及他们的同事、匹兹堡大学和意大利特伦托大学的卡洛·罗韦利 (Carlo Rovelli) 的工作在物理学界引起了一阵骚动。在过去几年里,这三位科学家进行了一系列计算,可能使物理学向其珍视的目标——即找到一条穿越数十年来困扰理论家追求量子引力的数学障碍的道路——迈出了许多步。从他们初步的探索中浮现出的,是一幅关于空间在最微小尺度上可能是什么样子的诱人图景。他们的计算暗示,时空并非无限平滑,而是可能具有一种精细的结构,一种类似于由无数超微小圈环向各个方向交织而成的地毯的纹理。多年来,物理学家和科普作家们都谈到“时空织物”;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可能真的说对了。
对量子引力理论的需求是如此迫切,以至于二十世纪科学界一些最具想象力、最固执、最著名的物理学家都曾在某个时期研究过这个问题。严肃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紧随二战之后。在试图将引力与量子力学融合的尝试中,最流行的策略是将引力看作与那些已经很好地融入量子范畴的其他力——即电磁力、强核力和弱核力——类似。
在量子力学的宇宙中,一切——能量、运动、自旋等等——都以不可分割的份量出现。力很自然地融入了这个框架。量子世界没有将磁性看作是磁铁发出的无形力线的结果,而是将力的概念转变为力粒子的交换——一场亚原子级别的网球比赛。在电磁学中,这个微小的网球就是光子,它不断地在带电粒子之间反弹,产生吸引力或排斥力。同样地,引力是通过引力子的持续传递和吸收在质量之间传递的,引力子目前仅存在于假设中;它们尚未被探测到。
在数学上,物理学家将这些粒子视为微小的激发或扰动——在广阔、平静的时空海洋上移动的小波浪。但当涉及到量子引力时,一个主要问题出现了:将力视为粒子的理论假设亚原子世界中的每一个事件都发生在一个固定的、不变的时空背景上。时空是舞台,而像光子和引力子这样的粒子,则是演员,在舞台上来回穿梭。阿西特卡举例说,比如光。我们想象空间和时间就在这里。打开开关,光就来了。关掉开关,光就消失了。时空不是参与者。
但在广义相对论中,舞台和演员之间的区别并不存在。物理学家说引力是粒子交换时产生的。但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引力就是时空本身的几何结构。因此,引力子同时成为了演员和舞台。一个引力子可以进入时空的舞台,但这样做最终会弯曲和扭曲舞台,就好像舞台是果冻一样。这种双重角色使得用物理学家处理其他力的数学技术来处理引力几乎成为不可能。当他们尝试时,结果毫无意义;例如,某个事件发生的概率可能会超过100%。
广义相对论学者很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与粒子理论家争论,认为这项工作必须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完成,一种允许时空几何成为积极的参与者而非仅仅是被动舞台的方式。他们说,一个恰当的量子引力理论应该允许空间响应力或质量的存在而演化和改变。牛津大学的数学家罗杰·彭罗斯 (Roger Penrose) 曾指责粒子物理学家试图将广义相对论夷为平地,然后对其“尸体”挥舞量子理论的魔杖。引力根本不能像其他力一样处理;它与众不同。相对论学者们团结在彭罗斯周围,回到经典的广义相对论本身,致力于将方程改写成可以直接用量子力学处理的形式,但不一定假设引力最终会归结为粒子的交换。不幸的是,在建立了自己的方程后,他们发现这些方程完全无法求解,就好像他们建造了一座漂亮的房子,却没有门可以进去。
数学家,就像其他工匠一样,需要工具来揭示他们方程的意义。假设你有一个方程——例如,x² = 4。为了找出x是什么,你取4的平方根。同样的方法适用于任何x值,但如果你不知道平方根——如果你没有这个工具——你就无法解这个方程。相对论学者们建立的方程相当于关于引力在量子条件下如何行为的优雅陈述。它们内部是一致的,语法是正确的,言之有理。唯一的问题是,物理学家没有产生解的数学工具。
如果不是1985年的一项突破改变了他们对量子引力的思考方式,相对论学者们可能会被困住数十年。那一年,相对论学者阿西特卡在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间架起了一座可以跨越的桥梁。这是他自大学时代起就想建造的一座桥。
阿西特卡于1949年出生在印度西海岸附近的小镇希尔布尔;他通过宇宙学家乔治·伽莫夫 (George Gamow) 的科普书籍被物理学所吸引。他进入孟买大学后不久,就显示出对物理学的天赋。他在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费曼 (Richard Feynman) 所著的一本经典教科书中发现了一个错误,便大胆地写信告知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费曼竟然回信并承认书中有错。“这太令人振奋了,我至今还保留着那封信,”阿西特卡说。
阿西特卡对宇宙学的兴趣自然而然地引导他研究广义相对论,因为正是通过爱因斯坦的方程,宇宙学家才能理解宇宙如何膨胀以及它为何呈现现在的样子。当他于1969年抵达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时,他已经知道,远离公众视线的相对论领域最适合他沉思的个性和数学倾向。“相对论有‘绅士’追求的美誉,”他微笑着说。“你可以自由地与同事交谈,从不担心有人会窃取你的成果,这与高能粒子物理学领域那种更激烈竞争的氛围形成鲜明对比。”
量子引力尤其吸引他。“年轻时有一种天真的傲气,”阿西特卡说,“鼓励你去挑战最困难的问题。”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当他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并担任一系列专业职位时,他都在努力攻克这个问题。但量子引力一直未能被他掌握,就像他的相对论同行一样。
他猜想,所缺少的是一个关键思想,或许是与导致量子力学发展的洞见处于同一水平的东西。在1900年之前,物理学家对关于光如何被吸收和发射的令人困惑的实验数据感到困惑。然后,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提出,能量并非以连续不断的流形式流动,而是以离散的包或量子(源自拉丁语,意为“多少”)的形式出现。确实,当光被看作是一连串被称为光子的粒子时,实验突然变得有意义了。普朗克推导出了一个量——被称为普朗克常数——来描述量子宇宙中可能的最小能量单位,即最精细的可能颗粒。
阿西特卡的洞见是以数学突破而非新颖物理思想的形式出现的。他的新方法来自一位名叫阿米塔巴·森 (Amitabha Sen) 的芝加哥大学研究生,他现在是华盛顿特区摩托罗拉公司的一名物理学家。森开发了一种处理几何曲率的方法,使他能够更好地描述一个被引力场捕获的电子的运动。“我对森的方法有一种直觉,”阿西特卡回忆道,“认为它在广义相对论中将极具价值。”
他是对的。受森工作的启发,阿西特卡得以引入两个新的数学函数或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新颖的几何语言,用以重写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正如阿西特卡所熟知的,物理学的洞见往往取决于对数学的恰当选择。牛顿处理行星运动的定律,关键依赖于一种新的数学——微积分——它能描述处于不断变化状态中的力和物体。而爱因斯坦,如果他没有遇到黎曼几何,即曲面的几何学,也许永远不会将引力与弯曲的时空联系起来。
为了理解恰当的数学如何能使复杂问题变得简单,想象一个日常问题:一架飞机在距离机场三英里的地方盘旋。如果你想用平面网格的几何来描述它的运动,结果会非常凌乱。飞机每改变一次位置,它的经度和纬度也随之改变。如果你将其东西向位置指定为x,南北向位置指定为y,那么描述其路径的方程是x² + y² = 3²。坐标在不断变化。但假设你切换到另一种几何:一个带有径向或圆形坐标的图。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不必担心x和y。飞机只是离圆心三英里远,描述其飞行路径的方程不过是r = 3(半径 = 3)。
在某种意义上,阿西特卡找到了一种使用新的数学变量重写爱因斯坦方程的方法。这项任务需要数年的思考和走弯路,随后是数周时间用新方程填满他办公室的黑板。然而,等待是值得的。经阿西特卡转换后,爱因斯坦的方程变得与量子力学中已经可以轻松处理的方程极为相似。事实上,阿西特卡推导出的这四个方程在许多方面都与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 (James Clerk Maxwell) 在一个多世纪前引入的方程相似,麦克斯韦的方程显示电和磁只是同一种力的两个不同方面。电磁学是物理学家成功与量子世界融合的第一个力;现在广义相对论看起来更像电磁学,与量子力学的结合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希望。
在量子引力这个抽象且常常深奥的世界里,阿西特卡的名字如今被经常提及。《经典与量子引力杂志》(该领域的圣经)上的论文经常提到阿西特卡的引力理论、广义相对论的阿西特卡表述,以及阿西特卡变量。
这个数学本身并非新发明;类似的工具已经在物理学的其他领域使用过。从技术上讲,数学家将阿西特卡引入的这两个工具称为“联络” (connection) 和“标架场” (frame field)。联络(两者中更重要的一个)是定义物体几何结构的一种方式——例如,球面或鞍面的表面如何弯曲——这在处理时空弯曲时是极有价值的工具。就像方程 x² + y² = 3² 描述了我们的圆一样,更复杂的方程描述了更复杂的曲线。联络是一种巧妙的数学工具,能让你更容易地描绘和测量曲率,包括时空的曲率。甚至爱因斯坦在尝试用联络重写广义相对论时也曾 stumble。阿西特卡的巨大成就是找到了一对独特的数学形式,完成了这项工作。
奇怪的是,当阿西特卡在1986年发表他的研究结果时,并没有响起“尤里卡!”的欢呼声。当时更多的注意力被投向了新来的(且更受欢迎的)宠儿——超弦理论。超弦理论不仅仅是量子引力理论,即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直接结合。它同时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万有理论”。换句话说,它试图证明引力和所有其他力都只是在时间之初短暂存在的一种祖先力——一种统一力——的不同表现形式。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超弦理论陷入了困境。“不仅其数学难以处理,而且似乎没有一个唯一适用于我们宇宙的超弦解。有无数个弦理论!”斯莫林惊叹道。
因此,阿西特卡的方法开始显得更具吸引力,也更可行。它不是一个用单一法则描述所有力的“万有理论”。它仅仅是一种研究当您观察越来越小的空间切片时,引力可能如何作用的方法,直到您进入由量子力学统治的微观领域。
1986年初,在他的新形式广义相对论正式发表之前,阿西特卡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理论物理研究所举办的量子引力研讨会上,就这一想法发表了一系列讲座。李·斯莫林,一位年轻而热情的该领域研究者,当时也在听众席中。
十年前,当斯莫林到哈佛攻读研究生学位时,他违背了所有教授的建议,去追求量子引力,这个当时被认为远离物理学光荣之路的课题。正如斯莫林所说,“你不知道你离答案是5年、50年,还是100年。”圣巴巴拉的会议对他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在阿西特卡描述了他对广义相对论的重新构建后,斯莫林和研讨会上的另一位年轻相对论学者、现任马里兰大学的特德·雅各布森 (Ted Jacobson) 立即合作,为可能的解决方案开辟道路。他们当时并未想到自己能用阿西特卡的新框架真正解出爱因斯坦的方程,但几乎是偶然地,他们做到了。雅各布森记得和斯莫林坐在他家的厨房里,桌上摊满了成堆的纸张,为一个接一个曾经被认为无法解决的方程找到了解。他们正在用新的量子语言进行最初的、试探性的翻译。
对这种方法的兴趣迅速传播,吸引了皈依者,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来自维罗纳的卡洛·罗韦利。罗韦利接触科学相对较晚,直到20岁,在参与了20世纪70年代初意大利的学生反叛运动之后。“我们输掉了革命,所以我决定试试物理学,”他说。1986年做博士后期间,他设法获得了一份意大利的奖学金(以及他父亲的资助),前往美国专门与阿西特卡和斯莫林合作。罗韦利性格随和、富有创造力且平易近人,很快就适应了中间人的角色,帮助将安静沉思的阿西特卡的分析能力与鲁莽冲动的斯莫林的创造力结合起来。
想象一下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与塞隆尼斯·蒙克联手。作为物理学家,阿西特卡和斯莫林就呈现出类似的对比。阿西特卡对细节和形式的关注体现在他雪城的办公室里。那个房间就像一个科学修道院。看不到任何乱放的纸张;胶带座、订书机和笔筒在桌上有序排列。远处的墙上只挂着一张海报,是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的肖像。“一个超越时代的人,”阿西特卡评论道。
就在阿西特卡办公室往下三个门的地方,另一个房间看起来好像被飓风安德鲁的灾难性路径扫过一样。书籍、衣服和期刊散落在地板和所有可用的表面上。“我其实不怎么把这个房间当办公室用,更像个衣帽间,”斯莫林羞怯地说,用手捋了捋他凌乱的头发。就像他研究的亚原子粒子一样,斯莫林从不停歇。你总是在奔波中才能抓住他。
随着罗韦利的到来,这个迥异的二人组变成了一个更加平衡的三人组。如果说阿西特卡是巴洛克作曲家,斯莫林是爵士音乐家,更冲动、更具实验性,那么罗韦利就像是小号手温顿·马萨利斯,既能演奏爵士乐也能演奏古典乐。“我们每个人组织思想的方式都截然不同,这有时会令人沮丧,”罗韦利说。“但我们共同理解了我们各自无法理解的东西。”
就像勘探新领域的先遣队一样,罗韦利和斯莫林开始更深入地探索阿西特卡的方程,试图弄清楚这些方程可能对空间和时间说些什么。斯莫林早些时候注意到,他找到的解与涉及纽结的经典数学问题的解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斯莫林花了一年时间徒劳地探索这种关系,并在罗韦利到来时向他解释了这一点。一天之内,罗韦利就回应道:“我知道怎么做了。”
罗韦利提出了一种新技术,使用圈环(与纽结密切相关)作为量子理论的基础。将阿西特卡方程与圈环技术相结合,催生了一组新的方程,其中每个方程似乎都代表了一种可能的时空构型。如果数学看起来相似,这强烈暗示着物理现实也可能相似。效果最好的解描述了简单的开放圈环,相互连接。意识到这一点后,罗韦利和斯莫林开始面对其他量子理论家几十年来一直怀疑的事情:我们日常关于空间的概念可能需要改变。“我们的发现超出了我们最大胆的预期,”斯莫林说。
认为空间是连续均匀的介质是很自然的。当你挥动手臂穿过空气,动作会自由流畅地从空间中的一点移动到下一点。但这种空间是平滑连续体的感觉可能只是一种错觉。罗韦利和斯莫林相信,空间,在最微小的亚亚微观层面上,实际上是由离散的、独立的单元——圈环——构成的。
空间可能具有纹理并非一个全新的想法。在20世纪5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的理论家约翰·阿奇博尔德·惠勒 (John Archibald Wheeler),如今是美国相对论领域的泰斗(他创造了“黑洞”一词),曾提出空间可能由一种“时空泡沫”构成,一种时空气泡的泡沫。但“时空泡沫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估计,”惠勒解释说。“阿西特卡、斯莫林和罗韦利所做的,是阐明了那种泡沫的数学。”通过将圈环表述的量子理论应用于这个问题,他们首次直接从广义相对论的方程中推导出离散的空间单位。
一旦你适应了空间构建块的概念,它似乎就变得很自然了;这正是量子力学的核心所在。例如,一块铁在我们眼中看起来相当坚固和均匀,但当放大到十亿分之一厘米的尺度下观察时,它不过是散布着质子和中子等离散粒子的空旷空间。而这些粒子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夸克。现在,空间也加入了这场量子派对,但只在一个极其微小的尺度上;一个量子圈环的直径是微不足道的10⁻³³厘米(一厘米的百万亿亿亿分之一)。而这个数字,反过来,是普朗克长度的度量——我们宇宙中可想象的最小颗粒尺寸,源自最小的能量单位。
如果一个原子被放大到我们银河系的大小,即跨越约10万光年,那么这些量子圈环中的一个仍然不会比一个人类细胞大。所以,空间看起来如此平滑也就不足为奇了,“就像一件T恤从远处看是平滑的一样,”罗韦利说。如果物质被挤压到如此微小的维度,通常是自然界最弱的力的引力,将会压倒所有其他力。然而,在成功的量子引力理论被锻造出来之前,关于那个决定性转变的一切都将无从知晓。
那么,什么是量子圈环呢?在许多方面,它类似于围绕条形磁铁的磁力线,即当你把铁屑撒在磁铁周围时清晰可见的光环线。事实上,每个圈环都可以被看作是磁力线的引力等价物——一种引力激发。在圈环线的内部或外部什么都不存在,甚至连真空都没有;圈环本身定义了空间。
根据斯莫林的说法,谈论一个空间圈环的属性是很困难的,就像你不能谈论单个原子的温度或密度一样。温度和密度只有在处理数万亿个原子时才有意义。同样,我们所熟悉的空间也只有在考虑无数个圈环,它们相互连接延伸数英寸、数英里、乃至数光年时才会显现。爱因斯坦曾将时空描述为一块光滑的垫子,但量子圈环的概念表明,它更像一张网——一张网眼极细的网。
这正是阿西特卡、罗韦利和斯莫林在一篇题为《用量子线编织经典几何》的论文中所描述的。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有一台足够强大的显微镜来检查量子空间,我们会开始将其感知为一张向各个方向无限延伸的地毯。起初,圈环空间团队认为这张地毯可能是像纺织品一样构建的,由无限长的线交织而成,构成时空织物。一个量子圈环就是这个编织物中的最小单元。阿西特卡甚至去上了一节编织课,以便更深入地理解这个意象。但三位研究人员最终得出结论,这张地毯的构造更像是锁子甲,即中世纪士兵穿的柔性盔甲。地毯的每个环都是独立而清晰的,但又与其邻居相连。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是如何运作的,罗韦利制作了一个三维模型,一个由金属圆环构成的令人惊叹的网格,他开玩笑说,用了维罗纳所有能找到的钥匙圈。
有了这种织物,就可以思考如何利用这种编织结构。例如,引力可能是在这种织物上进行某种刺绣的结果;你可以想象一个引力子就是缝合到网上的一个刺绣圈。大量的引力子会扭曲这种编织结构,就像质量扭曲时空一样。量子线中更复杂的结或扭曲可能代表其他类型的物理效应,尽管这在目前是极具推测性的。而物理学界长期以来的一个猜想——即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小于普朗克长度——在想象量子圈环时开始变得有道理了;如果一个粒子比一个圈环还小,那就没有可以悬挂它的支架。时空根本不存在于圈环线缺失的地方,就像毯子在其线的编织之间不存在一样。
自从阿西特卡七年前首次发表他那篇开创性的论文以来,数十位理论家已经撰写了超过200篇论文,对这个主题进行剖析、修正和扩展。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从瑞典、英国、印度、日本、德国到南美——每个月都会来到雪城和匹兹堡,向这些圈环空间的权威们学习。“一旦我读了阿西特卡的论文,我就无法再用任何其他方式思考引力了。我很惊讶这事没有更早被完成,”现任佛罗里达大学的富布赖特学者耶日·莱万多夫斯基 (Jerzy Lewandowski) 说。
这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张开双臂欢迎这一新发展。广义相对论学者和量子理论家都对量子圈环有一些严肃的担忧。曾热切拥抱阿西特卡方法的特德·雅各布森,现在怀疑他与斯莫林合作得出的解可能并不具有物理意义,更多的是一种数学技巧而非对现实的一瞥。仅仅因为方程没有导致荒谬的结果,也不意味着它们导出了物理上正确的结果。他告诫说,目前,雪城和匹兹堡的研究人员似乎更多地是受直觉和希望驱动。“我不相信他们的数学已经支持了圈环对应于离散空间的结论。”
阿西特卡同意这个新领域的地位远未确定。但他争辩道:“如果一个新的变量能显著简化物理学中的一个问题,它通常在告诉我们一些非常深刻的东西,即自然界确实是由那些变量构成的。”
其他人对这门科学则更为谨慎。他们承认圈环空间的数学很美,但想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一些真正的物理学研究。“他们必须将他们的方法与某种至少在理论上可以通过某种思想实验在现实世界中观察到的东西联系起来,”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量子理论家、量子引力领域的奠基人之一布莱斯·德威特 (Bryce DeWitt) 说。“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知道这种方法是否值得继续追求。”
阿西特卡、罗韦利和斯莫林认为这样的批评是公平的,但强调他们距离形成一个完整的量子引力理论还很远。“这是未知的领域,”阿西特卡指出,“概念上的革命不会很快发生。”事实上,为了简化他们最初的计算,阿西特卡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在一个无时间的空间中工作,一个没有时钟的空间。在他们能够开始预测时空织物在量子层面可能如何表现(预测是推动科学前进的引擎)之前,他们必须找到一种将时间带回他们方程的方法。他们需要一个量子时钟。而这可能需要一些新的数学,这也是阿西特卡和斯莫林明年秋天将转到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原因之一。“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数学系有纽结理论、复分析和算子代数方面的专家,这些都是对我们工作很重要的领域,”阿西特卡说。该大学以提供建立一个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引力研究中心的机会吸引了他。
破解量子引力问题的愿望无疑是诱人的,尽管该理论永远无法被直接检验;要达到量子引力定律生效的温度和压力,物理学家将不得不复制大爆炸的条件,这是一项短期内无法预期的技术壮举。“我们能期待的最好结果是间接测试,”阿西特卡说,“弄清楚量子力学的编织状态将如何在我们日常物理学中显现出来。”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在未来几年内是可能的。
尽管如此,已经有迹象表明,一个可行的量子引力理论可能会带来一些有趣的见解。近20年前,斯蒂芬·霍金宣布黑洞并非那么“黑”,震惊了天文学界。据这位剑桥物理学家称,黑洞——那些据说没有任何东西能逃脱的无底引力井——会缓慢地发出辐射并最终蒸发掉。没有人预料到黑洞会以这种疯狂的方式行事,但当将量子规则应用于自然界能提供的最强引力场时,这似乎就是结论。“它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世界是如何构成的深刻道理,”斯莫林指出。黑洞蒸发暗示了当一个成熟的量子引力理论最终实现时,物理学家将会遇到的那种惊喜。它会彻底改变我们对宇宙的看法吗?“绝对会,”斯莫林回答说。“我们当前的大爆炸理论可能会看起来像托勒密的地心说太阳系模型一样古怪。”
圈环空间研究者们近来备受媒体关注,但其他的量子引力方案也正在被积极地探索。罗杰·彭罗斯提出了一个想法,即时空的连续体是以某种方式由涉及带自旋粒子的更基本过程构建起来的。他称之为他的“扭量理论”。其他人,如霍金,则通过将量子力学定律应用于整个宇宙来寻找答案,希望能重现我们宇宙历史中许多亿万年前量子引力主宰的时代。而超弦理论仍然是目前最丰富,尽管也是最复杂的候选理论。
当然,这些方法最终都可能行不通。也许物理学家将再次经历一次对物理世界基本理解的变革,其革命性和惊人性堪比从经典力学到量子力学的转变。
斯莫林自己也承认他倾向于这种观点。“我很惊讶圈环空间理论能走这么远,因为我一直坚信,我们现在发明的几乎任何东西,由于我们主要是在经典框架下受的教育,都不太可能足够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