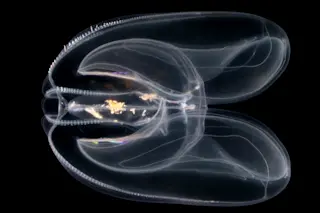大约十年前,应《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杂志的请求,我与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就睾丸问题进行了一场有趣的辩论。道金斯提出了著名的“自私基因”的比喻,用以解释生物体的性状如何从基因希望自我繁殖的想象角度来理解。这个比喻的底层逻辑很有说服力,但它并不总是能优雅地奏效——就像人类男性生殖器一样。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睾丸的位置似乎是一个奇怪的异常,就像把一辆装甲车的驾驶员放在一个绑在保险杠上的袋子里一样。如果人类有机体的全部目的是传递基因,为什么要把这些珍贵基因的储存库放在前面,置于危险之中?为什么不像保护大脑和心脏那样保护它们,用厚厚的骨骼保护,并在大脑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复杂的血源性感染屏障?
一种流行的解释是,睾丸需要保持凉爽才能使精子保持健康。这是真的,但作为一个进化解释,它很荒谬。进化掌握着所有的牌。她本可以轻易地塑造人类,使他们拥有能耐受正常体温的生殖化学物质。另一个被抛出的想法是,男人通过愿意冒如此大的风险来悄悄地向女人展示我们有多么强壮。这个想法可以通过枯燥的数学模型来支持,但说真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腰布早就应该使人类繁殖失效了,不是吗?
上周,当我在目睹人类基因繁殖的一个极其戏剧化和进化功能失调的时刻时,这些关于睾丸的旧想法在我脑海中盘旋,这使得睾丸显得微不足道:我的妻子生下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我看着人类最精致、最超然的体验,通过湿漉漉、血淋淋、失控的身体功能被传递出来。我们惊人的小女儿,已经充满了好奇心并积极探索,不得不挤过一个设计不佳、无法容纳她的大脑的骨盆。我妻子的身体痛苦地撕裂了,但并不比被认为是正常的更严重。每个人都筋疲力尽,如果不是因为发达的医学子宫,我们的孩子,就像任何健康的婴儿一样,会非常脆弱,生存几率很低。
这就是繁衍物种的方式吗?在换尿布的宝贵间隙,我一直在与一位老朋友,古生物学家尼尔斯·埃尔德里奇(Niles Eldredge)谈论人类有机体显然有缺陷的设计。
我注意到的一件事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宁愿认为自己拥有完美的身材。在尼尔斯和我看来,这似乎并非如此。以直立行走这件事为例。我喜欢行走节奏变成音乐的方式,而且双手自由是一个巨大的便利,但我们直立的身体结构是不完整的,充满了糟糕的结构妥协。危险的分娩(由于骨盆狭窄不当)只是最令人震惊的;我们还遭受坐骨神经痛、膝盖和足部衰竭等等。
与隔壁产房选择放弃无痛分娩的女性相比,我的妻子过得很轻松。她们出于个人原因选择了时代的痛苦。各种人,包括医院的工作人员,也鼓励我们尝试“自然”分娩,好像不面对又一个人类设计缺陷反而更符合我们的进化根源。虽然我尊重女性在这一最私密的时刻所做的选择,但我不认为人类物种曾经有过自然分娩这样的东西。
当我看着人类分娩这个可怕而又奇妙的过程时,一个画面出现在我脑海里。想象一个跳跃的运动员,也许是我们精力充沛的小女儿长大了,她的动作被相机闪光灯定格。这张照片记录了那一刻姿势的所有怪癖,而运动员却无法长时间保持。这就是人类的本质。古代的技师——今天被称为助产士、草药师、战士、火种师和萨满——早就学会了保护脆弱的新生儿和受伤的母亲。这种出于好意的干预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它通过减轻进化的手术刀——自然选择的压力——帮助人类的身体定格在目前的形态。
尼尔斯和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我们给了进化一个机会,她会如何改进人类的设计。可能会出现一个不同的物种,它将我们这样的物种仅仅视为一个过渡阶段。这个我称之为“智人”(Eureka sapiens)的假设物种会变成什么样子?
尽管四足动物也有下垂的睾丸,但它们的睾丸受到强大后腿的保护。智人可能会看到睾丸像卵巢一样迁移到腹部。为了冷却它们,腹部周围可能会进化出像跑车引擎盖上的进气口。智人雌性骨盆可能能够像蛇的颚部一样张开。我们实际上拥有这种能力的雏形:激素孕酮有时会在分娩前导致女性耻骨分离一点点。智人的婴儿将在子宫内停留至少一年,并且出生时消化道更强健,所以他们不需要哭那么多。结肠炎作为一个有利的适应性,其解释起来和脆弱的睾丸一样困难。
智人未能诞生,这是道德和同情的胜利。如果没有分娩技术的介入,自然选择将解决我们许多的缺点,但那将是一个极其残酷的过程。你身上任何基因决定的东西,包括你的眼睛颜色和性格特征,都是你所有未能成为祖先的生物(无论是像狮子一样大的还是像病毒一样小的)被吃掉,或者因为某种原因心碎而无法繁殖后,所剩下的东西。你是那个在进化残酷的过滤器横扫漫长时光后,在血泊中奄奄一息但仍活着的幸存者的后代的后代的后代。
有些物种,如令人印象深刻的蟑螂,已经长期保持不变,以至于我们倾向于认为它们是基因的杰作,正如终极批评者——进化背景下坚定不移的稳定性——所判断的那样。但生物学中没有什么是永恒或完美的。所有的生物设计在不同程度上都在变化。
然而,人类很不寻常,因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稳定在一个通常是过渡性的、有问题阶段——“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虽然技术让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许多旧的进化选择压力,但它也引入了新的压力;例如,我们现在正在改良自己以耐受化学污染物。尽管如此,认为我们的设计是完美的这种谬论,最近被一种同样错误的镜像观念所匹配:认为我们遗传基因中的缺陷绝对是坏的,并且必须完全抛弃。
体外受精赋予了准父母选择植入哪些胚胎、抛弃哪些胚胎的能力。正如当今人们常常指出的那样,我们正滑向“设计婴儿”的滑坡。最近几个月,英格兰的准父母们因为要求抛弃携带休眠基因的胚胎而成为新闻——这些基因可能会在孙辈中导致疾病,但前提是,这些胚胎在成年后,选择了同样携带隐性基因的伴侣。
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它假设一个令人恐惧的基因存在没有好处。就像想象我们的基因遗产必须完美会误导人们尝试“自然”分娩一样,其他人也被“无可争议的‘坏’基因必须被抛弃,因为大自然搞砸了”的观念所误导。
我回到那个跳跃的运动员的画面:尽管跳跃没有完成,但轨迹并非随机,中间的姿势也并非毫无意义。仅仅因为我们的基因进化被助产术等技术的突然出现所扰乱,并不意味着我们看似有害的基因总是完全没有益处。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研究员Stella Man最近发现,与耳聋有关的Cx26基因在帮助伤口愈合方面也起着作用。甚至有可能“有害”基因会对智力或品格等特质产生微小的着色影响。
我们人类是不完整的造物,缺乏蟑螂那种持久的进化完善。在我一篇早先的专栏(2006年6月)中,我解释说,无法确定一个大型软件程序事先会做什么。同样,也无法准确预测一个基因的价值。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基因的全部意义,因为进行提供这些知识的进化实验会过于残酷。
当然,有些基因是不可辩护的。亨廷顿舞蹈病(Huntington's disease)——一种纯粹的遗传性疾病,既致命又无法治愈——就是我们可以安全地称之为错误基因的一个例子,我们对此不应抱有任何忠诚。
然而,假设那些不方便但可存活的基因可能存在是有原因的,这也是有价值的。给予它们“疑罪从无”的处理,或者至少鼓励未来父母之间的多样性文化,他们将能够拒绝基因,以免我们基于不完全的知识而减少自身的生物多样性,这是合理的。
很容易走向极端,要么追求虚幻的自然完美,要么追求虚假的、消灭所有我们恐惧基因的人工完美。相反,我们必须划定一个大致的中间路线,以符合我们基因身份所固定的中间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