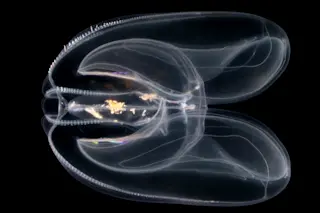圣经传说中的夏娃是一个诱惑者,从而开启了性别歧视史上的一个可悲主题。不幸的是,她最新的化身——所谓的“人类起源夏娃理论”——同样具有误导性,尽管她(正如夏娃本人一样)孕育了具有重大价值和后果的成果。
在过去五年里,关于人类进化的新闻报道中,没有哪个主题引起了比这更大的关注。1987 年,Rebecca Cann、Mark Stoneking 和 Allan Wilson 在英国顶尖期刊《自然》上发表的数据表明,所有现代人类的线粒体 DNA 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该祖先大约在 20 万年前起源于非洲。(Wilson,他发起了这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在一年前英年早逝,我们哀悼并深切怀念我们最喜爱和最杰出的同事之一。)他们的论证,如果正确,将具有极其令人兴奋的意义。(Wilson 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回应了对其最初工作的批评,并在最近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扩展了他们的结论。)不幸的是,他们也通过给他们的工作起了一个具有误导性但又朗朗上口的名字——“夏娃假说”——而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如果这个理论的实际内容不是那么重要,并且这个不恰当的名字没有如此有效地掩盖本应被重点突出的内容,我不会过度担心。两种错误的看法需要纠正。
首先,与一些人的想象恰恰相反,“夏娃理论”与女权主义无关,也与纠正一直以来充斥着人类学史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偏见无关。我们的线粒体祖先是夏娃而不是亚当,这仅仅是出于技术原因。虽然大多数 DNA 存在于我们细胞核内的染色体中,但线粒体(我们细胞的能量工厂)也包含少量 DNA。当然,卵子和精子细胞都含有线粒体;没有能量供应,精子就无法移动。但是精子起作用的部分,即在受精时与卵子结合的部分,不含线粒体,实际上只是一个细胞核。因此,我们所有人的线粒体,无论男女,都只来自我们的母亲。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其快速的进化速率(这在校准像智人这样年轻物种的时间尺度时很重要),线粒体 DNA 特别适合用于研究进化。
Wilson 及其同事通过测量所有主要种族群体现代人类之间的线粒体差异来进行研究。假设进化变化的速度恒定,然后他们推断出拥有共同线粒体序列的最晚近共同祖先。这位祖先就是线粒体夏娃。她是夏娃,因为线粒体仅通过母系遗传。当我们使用仅限于 Y 染色体上的男性基因进行类似的分析(目前有几项正在进行中)时,我们就可以谈论亚当了。
其次,夏娃的单一性并非是一种类似创造论的论点,认为人类起源于一个独特的女性。所有使用 Wilson 方法学的进化重建都追溯到一个共同的祖先状态。你选取当前的生物多样性,将其绘制在生命之树上,然后尝试追溯到一个共同的根源。这个根源是一个连贯的祖先群体——一群原始人类。在任何进化的群体中,大多数人都没有最终的后代,而一两个成员则产生了所有后代。(我们从人类家族名称和世系的研究所了解这一点;进化是一个极其偶然且基本上具有破坏性的过程,必须导致许多死胡同,正如我们这个大多是随机的世界中的任何分支机制一样。)“夏娃假说”并非描绘一个脱离普通群体生活进化现实的单一母亲,而是声称我们可以在大约 20 万年前将线粒体多样性追溯到一个非洲群体中的共同祖先(或者几个带有相同线粒体基因序列的近亲女性)。
该理论的真正激动人心之处在于“大约 20 万年前起源于非洲”这句话,而不是从误导性的“夏娃”这个名字中得出的任何推论。主要的争议也由此产生。事实上,就在最近,几篇出版物对 Wilson 及其同事用来生成支持智人起源于非洲的进化树的计算机程序提出了质疑(尽管在我看来,他们提出的 20 万年前“走出非洲”的设想仍然是最佳假说)。
出于文化偏见的原因,而不是有力的证据,传统的观点一直认为智人的大脑能力是在旧世界各地分布的种群中同时且独立产生的。(直立人,我们的祖先物种,在一年前就已从非洲迁徙到欧洲和亚洲。因此,拥有更大脑的进化优势如此强大,或者说,自然选择驱使直立人种群在所有大陆上都朝着我们卓越的智慧状态进化。)这种观点强化了我们希望将我们的物种视为一个可预测现象的心理愿望,认为我们现在统治世界是理所当然且必然的。我已将这些观点标记为“人类起源的倾向性理论”。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在 20 万年前才拥有非洲的共同祖先,那么欧洲和亚洲那些更古老的直立人种群就不是智人的祖先,而是我们从非洲较晚的一个分支事件进化而来。因此,我们遍布世界的传播是近期的,我们崛起的统治地位也更加脆弱,更不可预测。简而言之,我们成为了非洲一次幸运的、单一的历史事件的结果——一个祖先群体分化成了一个使我们所有人得以延续的细枝。我们是一个事物,一个单一事件,一段历史——而不是必然改进的可预测结果。我已将这些更谦卑的观点标记为“人类起源的实体性理论”。
这些理论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它们代表了进化一直以来的运作方式。进化是一棵枝繁叶茂的灌木,而不是进步的阶梯;虽然某些广泛的特征会不时重复(尽管鸟类、蝙蝠和翼龙各自独立进化出了翅膀,但所有飞行的脊椎动物都拥有相似气动形态的翅膀),但单独的细枝何时何地出现,在我们高度偶然的世界中是不可预测的。我们只需要把一个打破傲慢、粉碎自大的事实牢记在心:智人是渺小的一个细枝,而不是宏大、普遍的必然性之一。
在这里,夏娃也许能帮到我们。她摘取了正确的知识之果,以确保我们对进化的正确理解——一棵生命之树。也许她由此开启的对知识的探索,也能帮助我们获得那个更伟大的目标——智慧,而夏娃的作者用同一个意象来表达:“她是一棵生命树,她所持守的,是那些持守她的。凡持守她的,便为有福”(箴言 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