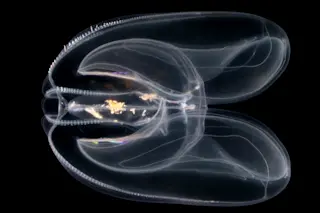正当关于现代人类起源的近期巨大争议似乎开始平息时,一位古老的祖先再次横冲直撞。践踏理论。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远超预期。要求新的解释。并无耻地在公共媒体上炫耀其对传统智慧的蔑视。
这次不安分的祖先是直立人——又名爪哇人,又名北京人,又名古生物学专家才知道的一长串正式名称。无论你如何称呼它,直立人传统上是一种安静、普通的古人类:眉骨低,骨骼粗壮,大脑比之前的古人类大但比之后的古人类小,面部比其祖先更不似猿猴且不那么突出,但比其后代更具猿类特征。在大多数人类进化的场景中,直立人的作用基本上是标记时间——一百五十万年——从其两百万年前在东非模糊的、假定的起源,到其最近进化成值得“智人”之名的物种。
直立人在地球上漫长的生存期间只完成了两项值得注意的壮举。首先,大约一百五十万年前,它发展了所谓的阿舍利石器文化,这种技术以大型、精心制作的泪滴状手斧为代表,比早期古人类使用的粗糙岩石工具先进得多。然后,五十万年后,借助这些阿舍利工具,这个物种走出非洲,并在旧世界的其他地方建立了人类的存在。但大多数时候,直立人只是存在,千百年来敲打着相同的石器,其时间跨度被一位考古学家称为“难以想象的单调时期”。
旧剧本是这样写的。如今,直立人开始即兴创作一个更活跃、更具争议的身份。过去一年的研究表明,几具来自东南亚的直立人化石并非一百万年前,而是将近两百万年前。这与该物种最古老的非洲成员的年龄相同,这意味着直立人比原先认为的更早离开其发源大陆——事实上,几乎是在它首次出现后立即离开。此外,1991年在格鲁吉亚城市第比利斯附近发现了一块下颌骨,它与来自非洲的直立人化石相似,可能已有180万年的历史,尽管这个年代仍然存疑。这些新的年代——以及它们引发的争议——将直立人从其解释性麻木中唤醒,清晰地揭示了关于地球上除了一个物种之外的最后一个人类物种的兴衰,人们的意见是多么不一致。
“现在一切都处于变动之中,”伯克利地质年代学中心的卡尔·斯威舍说,他是直立人非洲以外年代重定工作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一团糟。”
变动的焦点是该物种首次被发现的地点:爪哇。热带岛屿爪哇丰富的但又充满挫折的古人类学历史始于一百多年前,当时一位名叫欧仁·杜布瓦的年轻荷兰解剖学教授产生了一个固定想法,即猿猴与人类之间的“缺失环节”将在荷兰东印度群岛丛林密布的偏远地区找到。杜布瓦从未离开过荷兰,更不用说去过荷兰东印度群岛,他对人类起源地点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大部分是荷兰殖民地,而非任何科学证据。尽管如此,他还是在1891年爪哇中部一个名为特里尼尔的社区附近的索罗河畔发现了他的缺失环节——一个头顶部异常厚实、眉骨巨大的头骨。大约一年后,杜布瓦认为可能属于同一个个体的股骨在附近被发现;它看起来非常像现代人的股骨,以至于杜布瓦认为这种古老的灵长类动物是直立行走的。他将这种生物命名为“直立猿人”——皮特坎特鲁普斯·直立人——并凯旋而归。
找到化石被证明是容易的部分。尽管杜布瓦赢得了大众的赞誉,但他和他的“爪哇人”都没有得到当时解剖学家的完全认可,他们认为他的猿人要么只是猿,要么只是人。杜布瓦似乎一气之下,将化石藏匿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拒绝他人观看他的珍贵藏品。后来,其他类似的原始人类遗骸开始在中国和东非被发现。它们都具有一系列解剖学特征,包括长而低的颅腔,带有突出的眉骨和扁平的前额;从侧面看,颅骨后部呈锐角;以及深而坚固的下颌骨,没有下巴的痕迹。尽管最初被赋予了不同的区域名称,但这些化石最终被归为一个分布广泛的分类单元,这种生物与我们不太相似,但足够像人类,可以被纳入我们的人属:直立人。
几十年来,爪哇索罗河附近或沿岸的遗址是直立人新化石最丰富的来源。收获仍在继续:就在去年,在一个名为桑吉兰的著名化石遗址又发现了两个头骨,其中包括迄今为止已知最完整的直立人头骨之一。尽管爪哇的古人类产量丰富,但总有一些东西缺失——时间这个关键元素。除非化石的年代能够确定,否则它就悬而未决,其在更大的人类进化图景中的重要性和地位将永远被怀疑所削弱。在研究人员能够设计出更好的直接测定骨骼年代的方法之前——目前还没有能够可靠测定超过5万年历史的化石钙化骨骼年代的技术——标本的年代必须从其周围的地质中推断出来。不幸的是,爪哇这个人口稠密、耕种密集的岛屿上的许多发现并非由训练有素的挖掘者完成,而是由眼光敏锐的当地农民完成,他们在每年的雨季冲刷中发现骨骼,然后将其出售。结果,许多珍贵标本的原始位置,以及因此得知其年代的所有希望,都成了记忆和口头传说。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科学家们仍在继续努力确定爪哇化石的年代。大多数研究给出了大约100万年的上限。连同在中国发现的北京人头骨和欧洲的阿舍利工具的年代,爪哇的证据被视为证实直立人大约在那个时候首次离开非洲。
然而,有些人对这些年代的疑问已久。其中最主要的是伯克利地球年代学中心的创始人加尼斯·柯蒂斯。1971年,当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柯蒂斯,试图通过钾-氩法测定一块据称来自爪哇东部莫霍克尔托遗址的儿童头骨的年代,该方法用于测定头骨据称从中取出的沉积物中的火山矿物。钾-氩测年法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在使用,柯蒂斯在测定非洲古人类年代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包括路易斯·利基在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的著名古人类发现。该方法利用了火山灰中发现的放射性钾同位素会随时间缓慢且可预测地衰变为氩气的特性,氩气会 trapped 在矿物的晶体结构中。给定样本中包含的氩气量,与钾同位素的量进行比较,就像一个时钟,可以告诉我们自火山爆发、火山灰落到地面并掩埋相关骨骼以来过去了多少时间。
将该技术应用于与莫霍克尔托头骨相关的火山浮石时,柯蒂斯得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代:190万年。然而,这个异常离奇的年代太容易被驳斥了。与东非的火山灰沉积物不同,爪哇的火山浮石富含钾。而且,不出所料,厚厚的疑云笼罩着收藏家对其35年前发现化石的确切地点的记忆。此外,当时大多数古生物学家都坚信,直到100万年前,非洲是世界上唯一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因此,柯蒂斯的年代被认为是错误的,原因是最顽固地被珍视的:因为它不可能正确。
1992年,柯蒂斯在伯克利人类起源研究所的资助下,与同事卡尔·斯威舍一起回到了爪哇。这次,他得到了更灵敏的设备和测年技术的有力改进支持。在传统的钾-氩测年法中,需要从遗址中提取几克火山晶体才能进行一次实验。虽然这些晶体大部分可能来自覆盖化石的火山喷发,但总有可能混入来自数百万年前火山的其他物质,从而使化石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钾-氩法还要求研究人员将晶体样本分成两份。其中一半溶解在酸中并通过火焰;发射的光波长可以告诉样本中有多少钾。另一半用于测量晶体受热时释放的氩气量。这种两步过程进一步增加了出错的可能性,仅仅是因为它给实验提供了两倍的机会出错。
这种被称为氩-氩测年的改进技术巧妙地避免了大部分这些困难。火山晶体首先被放入反应堆中,并用中子轰击;当一个中子穿透钾原子核时,它会置换一个质子,将钾转化为自然界中不存在的氩同位素。然后,人工生成的氩和自然存在的氩在一次实验中进行测量。由于用于测量同位素的设备可以同时寻找两种类型的氩,因此无需分割样本,因此氩-氩法可以从微量的物质中产生清晰的结果。
在某些情况下——当火山物质相当富含钾时——来自单个火山晶体的所有氩原子都可以通过激光束的热量快速释放,然后进行计数。通过进行多次这样的单晶体实验,研究人员可以轻松识别并剔除来自较旧、受污染晶体的任何数据。但即使研究人员被迫取样多个贫钾晶体才能获得任何读数——就像在莫霍克尔托发生的那样——氩-氩法仍然可以产生高度可靠的年代。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员小心翼翼地一次加热几个晶体到越来越高的温度,使用精确控制的激光。如果样本中的所有晶体年龄相同,那么在每个温度下释放的氩气量也将相同。但如果混入了污染物,或者如果严重的风化改变了晶体的化学成分,氩气测量结果将不稳定,研究人员就会知道要丢弃这些结果。
柯蒂斯和斯威舍知道,在氩-氩步进加热法中,他们拥有准确测定莫霍克尔托贫钾沉积物年代的技术手段。但他们无法证明这些沉积物就是头骨被埋藏的沉积物:他们所拥有的只是发现它的当地人的口头证词。然后,在参观收藏化石的地区首府博物馆时,斯威舍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填充化石颅腔内部的硬化沉积物呈黑色。但在现场,据称曾保护婴儿头骨的火山浮石沉积物却是白色的。如果头骨被埋在白色沉积物中,它怎么会被黑色沉积物填充呢?难道现场和头骨根本没有关系吗?斯威舍怀疑出了问题。他借了一把小刀,拿起珍贵的头骨,在里面的基质上划了一小块。
“我差点因此被赶出这个国家,”他说。“爪哇的这些化石就像皇冠上的宝石。”
幸运的是,他的冲动得到了回报。小刀的刻痕在薄薄的深色颜料下露出了白色的浮石:多年前,有人显然将硬化沉积物的表面涂成了黑色。由于在据称的遗址方圆数英里内,没有其他沉积物在视觉或化学上与头骨中的基质相似的白色浮石,它与该遗址的联系突然变得更加紧密。柯蒂斯和斯威舍带着来自该遗址的浮石返回伯克利,并在几周内宣布该化石已有180万年的历史,上下浮动约4万年。与此同时,这些地质年代学家对来自桑吉兰地区下部的浮石进行了测试,那里曾发现直立人面部和颅骨碎片。测试结果显示年龄约为160万年。这两个数字显然打破了直立人非洲以外100万年的障碍,它们令人震惊地证实了柯蒂斯20年前在莫霍克尔托的工作。“这非常值得欣慰,”他说,“在被我的同事们嘲笑为傻瓜之后。”
尽管现在没有人再把柯蒂斯或斯威舍当傻瓜,但他们的一些同事在新年代得到证实之前,仍不会完全信服,除非莫霍克尔托头骨内部的基质本身也能进行检测。即使那样,头骨也可能在多年来漂移到含有与其原始埋藏地点无关的较旧火山晶体的沉积物中,或者它被河流带到了另一个更古老的地点。但斯威舍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要想驳斥化石的年代,莫霍克尔托和桑吉兰都必须发生这种情况。“我对这些年代感到非常满意,”他说。“但我花了一段时间才理解它们的含义。”
爪哇年代所能引申出的含义,取决于人们如何选择解读通常被归入“直立人”名下的化石证据。传统上归因于直立人的最早非洲化石是来自肯尼亚库比福拉遗址的两个近乎完整的头骨,年代介于180万至170万年前。在传统观点中,这些早期标本是从更原始、大脑更小的祖先——能人——进化而来的,能人的骨骼在库比福拉、奥杜威峡谷和南非的遗址中都有很好的代表。
如果这种传统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新的年代意味着直立人一定是在进化后很快就迁出了非洲,迅速深入到东南亚最遥远的角落。这当然是可能的:当时,印度尼西亚因海平面较低而与亚洲相连——从而提供了从非洲陆路通道——而爪哇距离肯尼亚仅1万到1.5万英里,具体取决于路线。即使直立人每年只行进一英里,到达爪哇也只需不到1.5万年——这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进化时间。
如果直立人确实比原先认为的早了近一百万年到达亚洲,那么其他更具争议的理论就变得更具说服力。尽管许多人类学家认为非洲和亚洲的直立人化石都代表一个物种,但其他研究人员最近争辩说,这两个群体差异太大,不能如此随意地归为一类。根据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人类学家伊恩·塔特萨尔的说法,传统上归属于直立人的非洲头骨往往缺乏最初用于定义亚洲物种的许多特殊特征,包括长而低的颅骨结构、厚实的颅骨以及坚固的面部。在他看来,非洲群体应该被归为另一个物种,他称之为匠人(Homo ergaster)。
大多数人类学家认为,区分化石记录中的物种的唯一方法是观察骨骼之间的异同;化石的年代不应起作用。但年代往往难以忽视,塔特萨尔认为,他所认为的同时生活在旧世界不同地区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群的新证据,极具启发性。“新的年代有助于证实这确实是两个不同的物种,”他说,“在我看来,直立人是一个独立的变种,只在亚洲进化。”
其他研究人员仍然认为,非洲和亚洲直立人形式之间的差异太小,不足以将它们划分为不同的物种。但如果塔特萨尔是正确的,他的理论就会引发一个问题:谁才是真正的非洲移民?匠人(Homo ergaster)可能是进行这次迁徙的物种,一旦它在亚洲建立起来,就进化成了直立人。或者,也许是某个更原始的、尚未识别的共同祖先种群冒险前进,在亚洲产生了直立人,而一个姊妹种群在本土大陆进化成了匠人。
此外,无论谁先离开非洲,还有一个问题是是什么促成了这次迁徙,而新的年代数据使得这个问题更加令人困惑。旧的解释是,原始人类跨越旧世界边缘的扩张是由复杂的阿舍利工具触发的,但这些年代数据已不再支持这一说法,仅仅是因为最早的人口迁出时,这些工具尚未被发明。事后看来,这个概念无论如何都显得有些老旧。阿舍利工具大约在150万年前首次出现在非洲,此后不久又出现在附近的中东地区。但尽管该地区有丰富的直立人化石证据,这些工具却从未在远东地区被发现。
到目前为止,这种缺失的最佳解释是“竹子线”。根据新泽西州威廉帕特森学院的古人类学家杰弗里·波普的说法,从非洲进入远东的直立人种群发现那里的竹子资源丰富,竹子这种原材料比顽固的石头更容易加工成切割和屠宰工具。因此,他们明智地放弃了效率较低的石器工业,转而采用以柔韧植物为基础的工具,而这种工具在考古记录中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这仍然是一个可行的理论,但来自爪哇的新年代数据又为其增添了一个更简单的维度:远东没有阿舍利工具,因为第一批离开非洲的直立人根本没有携带这些工具。
那么,究竟是什么推动了非洲的快速迁徙呢?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关键的发展不是文化上的,而是身体上的。利物浦大学的古人类学家伯纳德·伍德指出,像能人这样早期的原始人类是身材矮小,肢体比例更像猿的生物,而非洲直立人则更符合现代人的体型。高大、相对纤细、拥有更长的双腿,能够更好地长途跋涉,以及更能散热的身体,这个物种具备了使其摆脱非洲热带林地庇护的早期原始人类所需的生理机能。事实上,体型更大的直立人需要更大的觅食范围来维持自身,所以,该物种出现后不久就开始走出非洲是完全合理的。“直到现在,人们总是需要解释直立人进化后为何在非洲停留了这么久,”伍德说,“所以,爪哇的新年代数据非但没有带来问题,反而从某些方面解决了一个问题。”
当然,如果这些年代是正确的,那么人类在非洲大陆之外的进化公认时间框架几乎翻了一番,这对正在进行的现代人类起源辩论产生了影响。目前有两种对立的理论。“非洲起源说”认为智人是在非洲从直立人进化而来,然后在过去10万年间的某个时候,扩散出去并取代了欧亚大陆更古老的居民。“多区域连续性假说”则认为,现代人类是从旧世界各个地区的直立人祖先或多或少同时独立进化的。根据这个设想,非洲以外的现生人群应该在自己起源地区的古代化石解剖结构中寻找他们最近的祖先,而不是在非洲化石中。
碰巧的是,多区域论者长期以来一直声称,他们的理论最好的证据在澳大利亚,通常认为澳大利亚在约5万年前,由人类从印度尼西亚穿越而来定居。多区域论者说,现代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某些面部和颅骨特征可以一直追溯到桑吉兰最早的直立人标本——这些特征与任何近期从非洲抵达的智人(Homo sapiens)特征不同且早于它们。但是,如果新的爪哇年代是正确的,那么这些独特的特征,以及因此而来的原住民的亚洲直立人祖先,一定已经与人类其他地区的人类群体分离进化了近200万年。许多人类学家,已经对多区域论者提出的亚洲直立人可能长达100万年的隔离持怀疑态度,发现长达200万年的隔离极其难以接受。“有人能认真提出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血统可以追溯到那么远吗?”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人类学家克里斯·斯特林格(Chris Stringer)问道,他是非洲起源说的主要倡导者。
多区域主义者反驳说,他们从未主张完全隔离——人口之间总是存在基因流动,足够的杂交以确保明显的智人特征能够迅速传播到整个旧世界。“正如基因现在从约翰内斯堡流向北京,从墨尔本流向巴黎一样,自从人类进化以来,它们就一直以这种方式流动着,”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艾伦·索恩(Alan Thorne)说,他是一位直言不讳的多区域主义者。
斯坦福大学的考古学家理查德·克莱恩(Richard Klein)是“走出非洲”理论的另一位支持者,他认为证据确实表明亚洲人口与非洲人口之间存在长期而深刻的隔离。他说,化石记录显示,当古老型智人(Homo sapiens)在非洲发展时,直立人(erectus)在亚洲却保持着很大的相似性。事实上,如果爪哇一处名为 Ngandong 的遗址的一些直立人化石被证实与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的年龄一样年轻,只有10万年,那么直立人当时仍在爪哇存活,而完全现代的人类则生活在非洲和中东。更重要的是,克莱恩说,是文化证据。阿舍利工具即使在非洲发明后也从未到达东亚,这可能意味着发明者也从未到达东亚。“你可以说,新的年代数据表明,直到最近,亚洲一方面与非洲和欧洲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生物和文化鸿沟,”克莱恩说。换句话说,直立人一定有两个独立的血统,既然现代人类没有两个独立的血统,那么其中一个必然已经灭绝:很可能是亚洲血统,因更具文化适应性、携带工具的智人的到来而加速消亡。
当然,这个论点对多区域论者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但这场顽固的争论,在没有大量新化石、解释旧化石的新方法以及新年代数据的情况下,不太可能得到解决。在伯克利,柯蒂斯和斯威舍已经忙于将氩-氩法应用于Ngandong的化石,这些化石可能代表了地球上最后幸存的直立人种群。他们还希望在奥杜威峡谷的关键直立人头骨上施展他们的放射性魔法。与此同时,至少有一件事已经变得清楚:长期以来平淡无奇的直立人,在人类进化故事中,与其他任何角色一样迷人、有争议且难以捉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