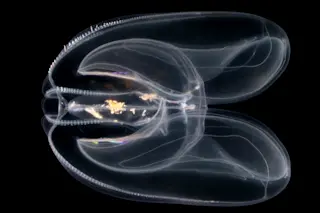苏格兰——从任何地方到博亨廷山(Hill of Bohuntine)这个陡峭的山坡上的特定地点,都要走很长一段路,向东眺望着格伦罗伊(Glen Roy)那片绿意盎然、布满石南花的深渊,那里连接着格伦格拉斯特(Glen Glaster)更平缓挖掘出的河谷。当然,如果你从美国来——比如从肯塔基州的彼得斯堡,或者田纳西州的代顿,或者其他成千上万的地方,你在那里用燃烧的美国国旗点燃一支万宝路,比被抓到带着一本《物种起源》更安全——你就会觉得这真是一次长途跋涉。
但我保证,你会很高兴你来了,有一天,感恩的上帝会在天堂洗净你疲惫的双脚。因为正是从这里,向东望去,你才能看到真相——科学界早已知晓,并因此长期保持沉默——那就是那位所谓的查尔斯·达尔文,留着愚蠢的胡子,有着愚蠢的理论,在今年这个他诞辰200周年的日子,他是错的。不是错了一点点。是大错特错。错得比喝了月光水的蓝提克猎犬还要离谱。错得比蒙着眼罩的南方女子组合(Dixie Chicks)还要离谱。而且,他还可能因此成为一个真正令人讨厌的家伙。
生日快乐,聪明人。
那一年是1836年。27岁的查尔斯·达尔文,那时还没有留胡子,刚从HMS“比格尔号”的船舱里呕吐着绕着地球一圈回来,在英国的法尔茅斯登陆,他的使命是巩固他日益增长的科学巨匠声誉。然而,在他花了两年时间洗澡和换了顶礼帽后,他的第一个目的地不是你想象中的伦敦动物园,也不是自然历史博物馆(那时还没有建成),而是苏格兰高地偏远而多雨的斯皮恩桥(Spean Bridge)这个简朴的小镇。
因为达尔文当时坚信地质学是未来的方向。他研究了雀鸟,并产生了那些会在二十年后汇聚成《物种起源》的思想,但地质学是当时热门的新领域,而且达尔文还拥有一个他希望借此一举成名的热门新理论。斯皮恩桥是当时和现在靠近一个引人注目且神秘的自然奇观“格伦罗伊平行公路”(Parallel Roads of Glen Roy)最近的居民点。当时,对于地质学爱好者来说,这个地方就像今天达拉斯的迪利广场(Dealey Plaza)对于阴谋论爱好者一样。如果你想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新领域与大人物们——比如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亚当·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亨利·德·拉·贝什(Henry De la Beche)——为伍,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斯皮恩桥,花几天时间在雨中爬上爬下巨大的山丘,进行素描,然后带着一个关于为什么格伦罗伊(在苏格兰语中,glen意为山谷)陡峭两侧以及附近几座山丘两侧,有三条平坦的、延伸数英里的架空公路的新理论回到文明世界。一个当地人流行的理论是,这些道路是芬恩·麦克库姆哈尔(Fionn MacCumhail),又名芬戈尔(Fingal),这位神话般的凯尔特巨人,他自己的狩猎小径。这很愚蠢——抛开巨人不谈,狩猎小径是啥玩意儿?——到了达尔文那里,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架空公路实际上是古老的海岸线,它们是在山谷中存在了数百年的湖泊形成的,而这个湖泊不知何故在三个不同的时期,分别停留在三个不同的高度。
湖泊理论的问题,这个让伟大人物关注的难题是,格伦罗伊的形状并不适合容纳一个湖泊,更不用说三个了。在其东北端,山谷两侧确实汇聚在一起,就像船头一样,但在西南方,山谷变宽并敞开,让所有降雨和溪水立即排出,并进一步浸湿苏格兰的其他地区。格伦罗伊要作为一个湖泊运作,就需要建造一道巨大的屏障,长达数英里,高近半英里,以堵塞山谷的出口并蓄水。谁能解释这道屏障从何而来,更不用说它又消失到哪里去了——很可能是分三个阶段消失的,对应三个不同的海岸线高度——人们普遍认为,这将给这个人带来不小的科学荣耀。
达尔文来了,他觉得自己对神秘的平行公路有所了解,因为他曾到过智利海岸的科金博(Coquimbo)。在科金博的公路上行走时,达尔文把口袋里装满了贝壳,而且几周前刚经历过一场地震,他合理地推断,科金博的公路是太平洋的古老海岸线,而太平洋就在那里,它们之所以处于现在的水平,不是因为海洋下沉或以某种方式干涸了,而是因为地球本身上升了,就像刚才在他脚下发生的那样。如果他能证明格伦罗伊的公路是与世界另一端的科金博的公路相同的过程形成的,那么他就可以提出一个全球性的“地壳抬升”理论,将其作为大陆形成的主要驱动力,这将是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可以成就他职业生涯的事情。
事实也确实如此。达尔文从苏格兰回来后,写下了他的发现,并向皇家学会提交了一篇论文,绕过了不太光彩的地质学会,声称格伦罗伊从未是湖泊,而是在苏格兰大部分地区被水淹没时,大西洋的一个海湾。达尔文的理论不需要山谷末端的屏障,似乎为地质学上的“万物理论”打下了不错的基础。达尔文因此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人们普遍称他为“值得关注的人”。
当然,他确实是。二十年后,他的《通过自然选择,或在生存斗争中保留受眷顾的物种的起源》将让维多利亚时代的世界各地的人们目瞪口呆,并永远回答最深刻的问题:我们为何在此?但格伦罗伊事件仍然具有启示意义,因为在他诞辰200周年之际,我们思考达尔文在宏大图景中的位置。
不仅仅是达尔文后来发现自己在公路问题上错了,尽管他确实很快就错了。1840年,狡猾的瑞士地质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来到格伦罗伊,提出了一个精妙的理论,认为山谷不是被泥土屏障阻挡,而是被冰川堵塞,随后的发现证实了这一观点。“我在格伦罗伊那里搞得一团糟,”达尔文后来写信给他的朋友和导师莱尔说,当时一个叫托马斯·杰米森(Thomas Jamieson)的人用了一些冰川动力学的知识来完善阿加西斯的理论。“我的论文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更重要的是他错在哪里。达尔文承认自己犯下巨大错误是在1861年,阿加西斯提出他的冰川模型二十年后,达尔文花了数十年时间,以一种与达尔文精神不符的固执,坚持他越来越站不住脚的海滩理论。当他的理论漏洞百出时,他却变本加厉,在1841年坚持认为,“我认为我毫无偏见地思考了整个情况,并坚信它们是海洋海滩。”有一次,他在给朋友约瑟夫·道尔顿·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的信中,半开玩笑地将自己生病的原因归咎于“一个大胆的狗娘养的(米尔恩先生)攻击了我的理论。”尽管他偶尔会表示对一些新的反对证据感到好奇,甚至“震惊”,但他总是得出结论,总而言之,他还是对的,而其他人都是错的。
这一切都只是说明,真正的查尔斯·达尔文可能比我们被告知的要更接近普通科学家的标准模型。尤其是在博亨廷山上向东眺望时,这种感觉尤为强烈。我受剑桥大学马丁·鲁德威克(Martin Rudwick)教授的指导,他是我参加的实地考察的组织者,而我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从他的实地考察笔记和整个职业生涯中“偷”来的。从博亨廷山上向东眺望,可以很好地看到一个巨大但缓和的山隘,在鲁德威克不带感情色彩的命名法中被称为R2山口(Col R2),与第二条平行公路(中间的那条)处于同一水平。在古代,当第二条公路形成时,它就是推测中的冰川湖溢出的地方。达尔文关于公路的海洋理论——它不需要湖泊,因此也不需要湖泊溢出口——他从一开始就承认,很大程度上是基于R2山口不存在的假设。事实上,他最初前往格伦罗伊进行实地考察的首要任务是确定是否存在第二条湖泊的“逃逸口”。我们也知道他爬上了博亨廷山,并且绝大多数人认为他向东看了。至于达尔文是否完全错过了这个山口,或者只是说服自己——在没有现代测量技术的情况下——它离第二条公路的水平线不够近,我们不得而知。
但当你挖开登山靴,试图找出困在你袜子里的恼人的石南草籽时,你不得不怀疑,那些为查尔斯·达尔文辩护的人,是不是该悄悄地收起“他是一位拥有超乎常人观察力和客观性的天才”的说法了。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宣传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人坚信“达尔文主义”是一种教义,一种计划,一种世界观,它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又支撑着意识形态。因此,就像达尔文自己知道必须在《物种起源》中塞入足够多的枯燥事实和证据,以抹去任何可能与之相似的煽动性或创造性作品的痕迹一样,那些被委托保管他遗产的人,则夸大了他的谨慎、他无私的勤奋,以及他那近乎诅咒的、看到事物真实面貌的独特天赋。正如西里尔·艾登(Cyril Aydon)在他的传记结论中承认的那样,达尔文可能没有爱因斯坦或牛顿那样强大的思维处理能力,但他“几乎超乎寻常地能够看到别人注意不到的东西。”
问题在于,通过崇拜达尔文这个人,我们却削弱了达尔文主义这个想法的极其显而易见的道理——至少对于那些不知晓他科学的公众而言是这样。我们仍然称之为“达尔文主义”,这一点就直接落入了其敌人的手中。你有没有听说过警察在犯罪现场互相喊道:“嘿,长官,这弹壳上可能有一些克里克-沃森森(Crick-and-Watsonian)的DNA”?你没有。因为一旦DNA的结构被发现,它就一直被发现,它的发现者在得到感谢和应有的报酬后,就被剥离了他们的发现,并允许他们继续自己的工作。
查尔斯·达尔文从未享受过这种奢侈。怀着最美好的意愿,我们让他的记忆得以保留,将他的声誉编辑和美化成他自己理论的人类类比。我们坚持认为,达尔文和自然选择一样,完全没有目的或议程,只是顺应现实为他留下的任何沟槽和通道。我们坚持认为,达尔文和自然选择一样,拥有无限的耐心,经受了数十年的缓慢进展和枯燥乏味,这足以让普通人发疯。而且,我们坚持认为,达尔文,就像他所取代的造物主一样,留着长长的白胡子,作为他智慧的证明。
但事实是,达尔文并没有留胡子。是的,他晚年留了胡子,那时他的健康状况不佳,刮胡子太疼了。但是,那个在与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的竞争中感到恐慌,担心自己要被抢先发表《物种起源》的达尔文,是干净利落的,就像几十年前陷入格伦罗伊平行公路困境的那个自大的年轻人一样。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不想在200年后仍然要向那些宁愿不理解自然选择的愚蠢的人们辩护其显而易见之处,那么我们应该努力记住那个没有胡子、更爱炫耀、更有人情味的达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