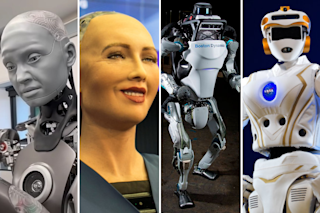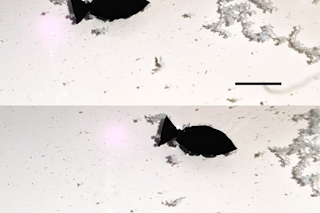玛格丽特·盖勒(Margaret Geller)于1986年秋天首次遇到了“火柴人”。虽然确切日期已从她的记忆中模糊,但她记得当时是午后,她的反应是一种欣喜。以前没有人见过“火柴人”——至少,没有真正见过。盖勒的研究生瓦莱丽·德·拉帕伦特(Valérie de Lapparent)注意到了它,但她说自己当时太缺乏经验,无法理解其含义。与盖勒在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cfa)合作的约翰·胡克拉(John Huchra)说,他一看“火柴人”就以为自己搞砸了观测。是盖勒的眼睛才认出了“火柴人”是真实而重要的东西。
盖勒、胡克拉和德·拉帕伦特绘制了附近的宇宙图,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仔细测量了1000个星系的距离,有些近至3000万光年,有些远达6.5亿光年。德·拉帕伦特将这些星系的距离和位置输入一个计算机程序,该程序打印出它们在宇宙中三维分布的二维表示。在打印输出上是北方天空的这一片区域,散布着1000个遥远的星系,盖勒说,正中间就是这个引人注目的“火柴人”形状。星系的分布看起来像一个孩子画的一个略带罗圈腿的人。这是一个对一个宏伟形象的异想天开的名字:“火柴人”横跨宇宙5亿光年。它的躯干由数百个星系组成,这是一个天文学家称为“后发座星系团”的巨大集合。它的手臂是另外两片星系,横跨夜空。
“火柴人”不仅在维度上宏伟,在命运上也宏伟。你甚至可以说它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在“火柴人”出现之前,宇宙似乎是一个平滑而均匀的地方。天文学家认为星系是随机分布的,尽管它们偶尔可能会形成像后发座星系团这样的星系团,其中包含多达一千个或更多的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甚至有一些证据表明宇宙至少包含一个巨大的空洞,位于牧夫座,似乎延伸了约2亿光年——还有其他一些迹象表明星系可能呈长丝状排列。但1985年,大多数天文学家认为这些结构并非宇宙本身产生的,而是用于调查宇宙的方法产生的。
然后盖勒看到了“火柴人”,这构成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星系正在二维结构上聚集,就好像它们是从宇宙虚无中凝结到无形气泡的表面一样。事实上,当盖勒后来撰写cfa星系巡天结果时,她将宇宙中星系的分布描述为“厨房水槽中的肥皂泡切片”。她的比喻暗示天文学家对宇宙的形成方式感到非常困惑。
早期宇宙,在大爆炸时期,是一个平滑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大爆炸留下了印记:宇宙背景辐射,这是一种比绝对零度高3度的辐射,弥漫在整个宇宙中。这种背景辐射比婴儿的屁股还要平滑得多,这意味着宇宙在几十万年前(甚至可能更年轻)同样平滑。现在它不是了。它充满了这些巨大的二维结构。也许最令人惊叹的是盖勒和胡克拉在1989年发现的,被称为“巨墙”:一片星系延伸至少5亿光年,横跨整个北方天空。它可能确实比5亿光年更大,但目前无人能知。
困惑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天文学家可以在他们视线的极限处看到巨大的结构,这意味着宇宙比今天年轻得多。当我们望向太空时,我们正在回顾过去;例如,来自十亿光年外星系的光,需要十亿年才能到达我们这里。“这真是令人惊叹的事情,”盖勒说。“历史就在那里供我们观看。它不像地球的地质记录那样被揉碎。你可以看到它完全是它曾经的样子。”
那么,发生了什么?我们所能看到的最远处的宇宙都充满了这些惊人的二维结构,因此,我们所能追溯到的最远古的宇宙也充满了它们。在宇宙成长起来的100亿到150亿年里,它已经从难以想象的光滑演变成现在这种“水槽肥皂泡”般的结构,而至今无人知道这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的。
盖勒正在努力回答这个问题,世界上至少还有一百多位天文学家也在做同样的工作。绘制宇宙结构图已经成为天文学中的一项新兴产业;自“火柴人”出现以来,天文学家已经启动了十多个项目来绘制星系分布图。盖勒与cfa天体物理学家丹·法布里坎特(Dan Fabricant)的合作可能是最深入的之一。两人正在进行一项巡天调查,该调查预计将于1998年末开始,以每晚数千个星系的速度探测宇宙。等到他们完成时,他们将调查超过50,000个星系,并绘制出宇宙中远达50亿光年的条带。这可能就足够远了——也就是说,足够回到过去——以了解我们所看到的宇宙为何与大爆炸时期的宇宙如此截然不同。“既然我们对附近宇宙的样子有所了解,”盖勒说,“每个人都想知道它是如何变成这样的。而这场竞赛正在进行中,以找出答案。”
“火柴人”的发现可能改变了玛格丽特·盖勒,就像它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一样。它将她推向科学的巅峰,并将她的名字与宇宙测绘以及宇宙结构本身联系在一起。在盖勒首次在休斯顿的一次会议上向她的天文学家同事展示“火柴人”的第二天早上,她登上了《今日秀》,带着“火柴人”和宇宙比以前想象的更加令人费解的消息。她接着获得了麦克阿瑟奖,并成为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和哈佛天文台的明星。然而,所有这些成就都不足以让盖勒在天文学领域感到自在。
有一种理论认为,当个体与环境格格不入时,创造力就会产生。简单来说,与社区和谐相处的人缺乏足够的动力去冒险创造真正新颖的东西,而那些格格不入的人则被不断证明自己价值的需求所驱动。他们失去的少,获得的更多。“不同步理论”或许可以帮助解释盖勒,她自开始学习天文学以来就一直在努力适应。盖勒最初的爱好是表演,但她的父亲,一位研究晶体结构的物理化学家,尽其所能鼓励她从事科学。他会带她去他在新泽西州贝尔实验室的实验室,那是贝尔实验室的鼎盛时期,她在那里玩他最先进的手摇计算器。“最大的挑战是让它发出尽可能长时间的巨大响声,”盖勒说。到她十岁时,她已经在做简单的计算了。因为她不喜欢上学,她的父母让她自学。她的母亲,盖勒从她那里继承了对语言的痴迷,会带她去图书馆,帮助她选择书籍,然后在家监督她学习。盖勒只会在学校出现参加考试,仅此而已。
作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本科生,盖勒最初学习数学,但后来转学物理。她说:“我不知道在数学中应该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在物理学中,我可以看到有些事情是已知的,有些事情是未知的。”她回到东部普林斯顿读研究生,在那里她学习天体物理学,了解星系巡天,并仔细研究星系目录。她也失去了信心,与环境格格不入。她说,在那之前,“我从未想过有什么事情是我做不到的。”
她讨厌普林斯顿。在盖勒于1970年到来之前,只有一位女性——格伦妮丝·法拉尔(Glennys Farrar,现任罗格斯大学)——成功获得了普林斯顿物理系的博士学位。那年普林斯顿刚招收第一批女本科生,据法拉尔说,物理系的气氛“糟透了”。盖勒说她不够成熟,无法应对:“学生会问我在普林斯顿物理系做什么,而男性都找不到物理方面的工作,或者他们会说,‘系里只有一位女性通过了普通考试,之后又招收了三位,她们都失败了。所以你有75%的几率会失败。’”
盖勒说,直到她来到普林斯顿,她才意识到科学界女性如此之少。不知怎的,她之前一直没有察觉。但“我整个求学生涯中,从大学开始到结束,从未有过一位女性教授。甚至所有的书都是关于男性的;我从不喜欢读关于科学史的书,也从未真正明白为什么。”在伯克利,这并没有困扰她,也许是因为物理学家习惯了与女本科生打交道。“我从伯克利毕业时非常自信,”盖勒说。“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几乎一点自信都没有。当人们告诉你因为你是女人而做不到某件事时,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会开始相信他们可能是对的。这很惊人,因为即使你知道这些事情完全是非理性的,它们也会伴随你很多很多年。”
盖勒曾多次想放弃普林斯顿,但她的父母说服了她。他们说我“不应该放弃,因为我从未在任何事情上失败过,如果我离开,我会觉得自己失败了,这会困扰我一生。拿到学位后再放弃。”她拿到了学位,但没有放弃。这段经历磨练了她。诺贝尔奖获得者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盖勒从普林斯顿来到哈佛时,他说这是她最突出的地方。“我很欣赏她,”他说。“不仅因为她的智慧,她还有一种坚韧,一种追求科学的坚定目标,确保她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会实现。”
尽管如此,正如盖勒承认的,她在哈佛的最初几年可以被称为她的“迷失岁月”。她还没有从普林斯顿的经历中恢复过来,现在她对天体物理学有着复杂的心情:“我觉得我能做到,但我想做吗?”最终,在1979年,她在英国剑桥大学呆了一年,并重新思考了事情。
她在剑桥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是评估宇宙结构的知识现状。她说:“我意识到除了我们星系之外,几乎什么都不知道。”当时已经进行了一些星系巡天,但规模很小,不足以就星系在宇宙中的分布得出确凿的结论。为了测量星系距离,这些巡天研究了红移,红移是衡量遥远物体发出的光波长向光谱红色端拉伸程度的指标,物体越远,红移越大。胡克拉和哈佛天文学家马克·戴维斯(Marc Davis,现就职于伯克利)测量了2400个星系的红移,这些星系最远只到3亿光年,以宇宙的标准来看,这只是我们自己的“后院”。那次巡天太浅,无法看到后来发现的显著模式。
鲍勃·柯什纳(Bob Kirshner),当时在密歇根大学,现在在哈佛大学,曾领导了一项对数百个星系更深入的巡天,但它们都只测量了天空的几个微小区域。盖勒将这种技术比作“在干草堆里扎几根针”来绘制干草堆的内部结构。这项巡天发现了牧夫座大空洞,但很少有天文学家相信这个空洞是真实的。盖勒说:“每个人都持怀疑态度。我认为这次巡天有问题,因为这个空洞比任何人认为存在的任何结构都要大得多。”
盖勒在英国的那一年没有写论文。她说:“我做的事情更有价值。我弄清楚了我认为有趣的问题的类型。”回到马萨诸塞州剑桥,她开始与约翰·胡克拉一起研究星系团,这让她开始思考更大尺度上星系的分布。她决定,应该有人进行一项深入宇宙的巡天,如果牧夫座空洞是真实的,这项巡天将能够看到像它这样非常大的模式。她毫不费力地就说服了胡克拉,胡克拉曾与戴维斯一起从事红移巡天工作,并且知道该领域需要一项更深入的巡天。盖勒将设计项目并处理数据,而胡克拉和德·拉帕伦特则会在夜晚待在望远镜旁进行观测。他们只需决定绘制天空的哪一部分。
正如他们今天都承认的那样,他们在那一点上很幸运。盖勒想测量跨越天空的连续条带中星系的红移。她认为,通过检查长而连续的条带而不是孤立的斑块,他们可以发现大型结构并理解它们的几何形状。胡克拉同意了,因为条带很容易测量;你只需让天空在望远镜上方移动,它就会为你完成繁重的工作。盖勒说,幸运之处在于条带的宽度。我们很幸运它足够宽,能够看到火柴人。
盖勒以视觉思维,将问题看作模式和几何形状,因此“火柴人”的出现代表了她生活中一些主导主题的融合。条带的选择是一种几何选择,而“火柴人”本身就是从宇宙背景杂乱中浮现出来的一种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一直在等待盖勒来解读其意义。在发现之后的几个月里,她花了大量时间制作了一个关于“火柴人”的视频,以向她的同事传达这种模式的美丽,以及随之而来的她的惊奇和顿悟感。她和她的cfa同事迈克尔·库尔茨(Michael Kurtz)使用她称之为“极其原始的图形”,展示了他们所截取的宇宙切片。盖勒说:“我们会坐在那里,被这个不断移动的切片完全迷住。我们会一遍又一遍地盯着它看。就好像我们吸了什么东西一样。”
随着“火柴人”的发现,盖勒声名鹊起。用温伯格的话说,她已经确立了自己在哈佛天文学界的“装饰品”地位。当她和胡克拉完成了另外四次红移巡天后,她为《科学》杂志撰写了一篇关于“巨墙”和宇宙测绘艺术的论文。随后,她获得了麦克阿瑟奖,这让她得以筹集20万美元,制作一部关于她与胡克拉及其他同事工作的纪录片。这部电影让她焕发了活力,教会了她新技能,并带给了她新想法。
然而,尽管获得了一系列荣誉,盖勒仍然只是史密森天体物理观测站的高级研究员,尽管她在哈佛有教授职位,但从未获得终身教职。她说:“我为此周期性地把自己逼疯。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没有这个?’我曾有一段时间因此而感到很难工作。然后我想,‘管他呢,我已经证明我能做到。为什么我不去做些别的事情呢?’”
这个问题接近于反问。如果需要一个答案(除了她对事业的热情之外),那可能就是新的巡天项目和丹·法布里坎特正在建造的仪器。盖勒在cfa启动的项目即将获得回报,她希望亲眼见证这一切。虽然法布里坎特在天文仪器建造者中声名显赫,但盖勒的成就也给他带来了一些小小的赞誉。她是在法布里坎特还在读研究生时认识他的,当时他只有45岁。后来,当哈佛-史密森光学天文学界忽视他的抱负时,是盖勒一直在培养它们。
法布里坎特的职业生涯始于建造用于从火箭和后来卫星进行X射线天文学研究的仪器。但当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时,任何科学卫星的发射,无论是X射线还是其他,都变得像是一个有争议的提议。法布里坎特将他的重心转向了光学天文学,而光学天文学正要经历其300年来的第三次重大革命。实现这一革命的技术被称为多路复用——不要与每次你去电影院有17部电影可供选择混淆,尽管概念相似。
第一次革命始于伽利略发明望远镜。在接下来的300年里,天文学得以发展,因为天文学家制造了越来越大的望远镜,这使他们能够收集到越来越多的光线,并看到越来越暗的物体。到1950年代,随着圣地亚哥附近帕洛玛山200英寸(5.1米)镜面的出现,望远镜已经达到了其可能的最大尺寸。在接下来的30年里,进步来自于收集撞击设备光线的新技术。这是第二次革命。天文学家停止使用只能捕捉到入射光百分之零点五的感光板,转而使用可以捕捉到90%以上光的电子探测器。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天文学正在迎来第三次革命。新的技术正在出现,让天文学家再次能够建造更大的望远镜——比如夏威夷的10米凯克望远镜,它使帕洛玛山望远镜相形见绌。与此同时,研究人员一直在开发能够同时观测多个物体的仪器(因此有了“多路复用”这个词)。例如,一个能够同时测量100个星系红移的望远镜,将比只能观测一个星系的望远镜提高100倍。“我们很少在天文学中获得100倍的进步,”法布里坎特说。
当挑战者号灾难促使法布里坎特转向光学天文学时,史密森尼和cfa正在考虑如何处理图森附近霍普金斯山的一台光学望远镜,它被称为多镜面望远镜(Multiple Mirror Telescope),简称mmt。这台望远镜设计于20世纪70年代,由六个相同的镜面组成,它们协同工作,就像一台六倍大的望远镜一样。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想法,因为建造六个适度的镜面比建造一个巨大的镜面要便宜得多。但是mmt一次只聚焦一个物体,这几乎注定了它从首次对天文学家所说的“初光”开放的那天起就注定要被淘汰。
在亚利桑那大学同事的建议下,cfa的天文学家们考虑将MMT重建为单个镜面,使其能够清晰地聚焦于相当于满月四倍大小的天空区域,而不是单一的恒星或星系。没有人确定他们将如何处理这个新的MMT(他们计划将其重新命名为“巨型镜面望远镜”,以保持首字母缩写不变)。法布里坎特,当时还只是一位年轻的X射线天文学家,参加了会议,但没有人真正重视他的想法。“他们有点令人沮丧,”法布里坎特说。“他们的态度是,‘我们真的不需要任何人做这个,如果需要,也不会是你。’”
盖勒是例外。火柴人让她相信,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天空巡天,尽可能深入到宇宙中,技术所允许的范围。到1990年,天文学家只绘制了区区10,000个星系图;盖勒喜欢说,从10,000个星系的位置来解释宇宙结构,就像试图从罗德岛地图来理解地球表面一样。盖勒想要的深度红移巡天只有通过新的多路复用仪器才能实现,因为你看得越深入宇宙,每个天空区域的星系就越多。当盖勒和胡克拉绘制附近几亿光年外的宇宙图并发现火柴人时,他们很幸运地在每一平方度的天空中看到了一个星系。然而,如果你望向50亿光年外的宇宙,你会在相同的天空区域看到一千多个星系。“这只是让你对宇宙有多大有一个概念,”盖勒说。有了合适的仪器,天空巡天可以同时绘制大量这几千个星系图,盖勒相信法布里坎特,无论是否是X射线天文学家,都有才能帮助建造它。
盖勒还觉得她现在有足够的声望来施加影响力。在接下来的六七年里,她成功地为法布里坎特争取到了建造两台用于红移巡天的新仪器的资金和许可。第一台——被称为“十谱仪”(Decaspec),因为它能同时观测十个星系——安装在基特峰附近图森的一台2.4米望远镜上。它在第一个夜晚就成功运行了,这与天文学史上大多数仪器不同。第二台安装在霍普金斯山一台较小的望远镜上,不仅在第一个夜晚完美运行,而且是有史以来建造的同类型仪器中效率最高的。法布里坎特和盖勒使用这台仪器进行了一次星系巡天,其深度是发现火柴人和巨墙的那次巡天的两倍。他们的新巡天显示出同样的难以解释的二维结构,但仍然没有关于它们如何以及何时形成的迹象。
现在,法布里坎特正在建造终极红移收集器,他们将用它来绘制50,000个星系图。它将被安装在改装后的MMT望远镜的末端,该望远镜预计将于1998年末以一个巨大的6.5米镜面首次观测。法布里坎特的仪器,被称为Hectospec,将一次收集300个星系射向镜面的光线。(Hecto在希腊语中表示100,这是一个正确的数量级,而且比Trihectospec更容易发音。)然后它将自动重新分配其300根光纤,一次一根,以便五分钟后可以开始观测另外300个星系的红移。如此夜复一夜,只要法布里坎特和盖勒能在望远镜上获得观测时间。
法布里坎特和他的同事们正在剑桥哈佛-史密森尼对面的一间实验室里完成Hectospec的设计。要了解法布里坎特正在建造什么以及它将如何运作,首先要想象望远镜本身。来自天空的光线落下并从巨大的主镜反射,然后从主镜上方6米处的次镜再次反射。两次反射后的光线再次落下,落在被称为焦平面的表面上,焦平面有时覆盖有感光胶片或电子探测传感器。在这种情况下,它将被Hectospec覆盖。
Hectospec 的光收集器是 300 根微小的玻璃纤维,每根纤维末端都有一个同样微小的棱镜,该棱镜固定在一个磁性吸附在焦平面上的金属按钮中。如果按钮放置正确,来自星系的光线将落在棱镜上,棱镜会将其引导到光纤中,光纤将与其他 299 根光纤一起进入光谱仪——该仪器将光线分解成其组成颜色,从而可以测量红移。
那部分相对简单。困难的部分是放置那 300 个按钮:弄清楚如何一个接一个地拿起它们,然后准确地放回下一个星系的光线将落下的位置,而不会缠绕玻璃纤维。更困难的是,所有这些重新定位都必须在望远镜上发生,望远镜可能以未知角度指向天空,温度范围从舒适的 70 华氏度到非常冷的 20 华氏度,具体取决于一年中的时间。速度也很重要。纤维重新定位得越快,可以调查的星系就越多,这至关重要,因为正如已经指出的,宇宙是巨大的。
移动按钮的任务由一对机器人完成,盖勒将其描述为“相当巨大的机械”。她补充说,如果你在街上遇到它们,你不会认出它们是机器人。它们就像未来机械制图桌的逃兵,在两根垂直的轨道上移动,使它们能够覆盖整个焦平面。每个机器人的底部都有一个夹具,可以夹住纤维末端的按钮。一旦夹具锁定,机器人将以每秒一英尺的速度重新定位纤维,这大约是小提琴手演奏行板的速度。
法布里坎特说,Hectospec的指导理念是建造他们能够完成的最雄心勃勃的项目,在望远镜上第一天就能测量最多星系的红移。“你可能会冒不够雄心勃勃的风险,到项目完成时,没有人会觉得有竞争力,”他说。“但如果仪器在你分配的夜晚表现不稳定,你就倒霉了。你必须非常确定它会起作用。”由于这项工作的棘手性质和Hectospec的特殊要求,法布里坎特和他的朋友们无法吸引任何工业制造商接受这项挑战,所以他们正在自己建造仪器。他们预计在1997年末完成,这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确保它在MMT一年后开启其巨大的单眼之前正常工作。
到那时,盖勒和法布里坎特将开始测量他们的星系——一次300个,一晚多达3000个,一年数万个。在他们进行这项工作的同时,他们将与另外半打红移巡天项目竞争。有些将绘制较少的星系图,但会更快上线。有些将绘制更多的星系图,但深度不会那么深。他们都将寻找结构开始的迹象,寻找宇宙开始形成盖勒所说的“这些美丽的图案”的时刻。“这可能就是盖勒仍然坚持这项事业的原因,”她说。“问题的宏伟性和美学。我看到了宇宙创造的这些美丽的图案,我想知道它是如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