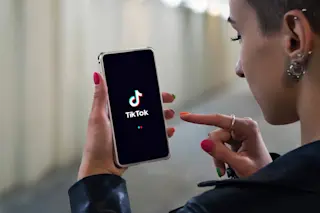理查德·扎雷不想谈论火星上的生命。并非说其他星球上生命的可能不吸引人,而是其他一切也都同样引人入胜。这位斯坦福大学的化学教授坐在他办公桌前巨大的会议桌后面,那张橡木桌面像一块土地,上面散布着讲义、信件、手稿、国会证词和正在进行的实验结果。其中很多都与火星有关——这很棒,有什么不喜欢的呢?——但在人们向他索要签名、农民打电话问他犁出的红石头是否来自火星、以及所有媒体都想和那位告诉吉姆·莱勒(Jim Lehrer)我们可能都是火星人的人聊上一分钟之前(泰德·科普佩尔(Ted Koppel)、《时代》杂志、要求他被沐浴在诡异红光下拍摄的纪录片导演(扎雷拒绝了),以及现在正在门口等他查收邮件的你),扎雷就已经够忙够快乐了。
他忙完后,跳出桌子,像老朋友一样和你打招呼。扎雷几分钟后有课要上,所以他穿着夹克打着领带,你忍不住注意到,因为领带上元素周期表垂直向下延伸,止于一个巨大的方形西部风格银色皮带扣。他宽阔的脸上挂着天真的笑容,仿佛他半期待着有什么愉快的事情发生,如果不是此刻,那也许是下一刻。你还记得在NASA总部宣布发现时那场著名的记者招待会上,他那张闪耀的脸庞,那是讲台上众多面孔中的一张,因为从火星陨石中寻找古代生命的证据需要许多聪慧的头脑共同努力。但只有一张脸在时差和电视灯光的眩光中依然微笑着,那张略显精灵般的大脸,戴着厚厚的方框眼镜,留着盐胡椒色的山羊胡。当然,你来这里是为了问关于火星的事情,但在你把笔记本从口袋里拿出来之前,扎雷先问了你一个问题,让你措手不及。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他指着咖啡桌上一个巨大且非常“激动”的物体问道。那是一个复古存在主义风格的人形雕塑,由滚珠轴承、六角螺母和螺纹管组成,一张脸像金属披萨。它高举着两根烛台,以防有人想进行一场安静浪漫的晚餐。你首先想到的是“旧货出售?”正当你绞尽脑汁寻找更得体的回答时,扎雷自己承认这件雕塑之所以在他的办公室里,是因为他妻子不让它进家门。
“我觉得它又丑又有力。她只是觉得它丑。”他笑了。然后他告诉你他是如何在最近的柏林发现这个雕塑的,那是在一栋二战中被烧毁的废弃百货公司里,现在被毒贩、妓女和艺术家组成的联盟占据,与警察对抗。这是一个好故事,讲述故事的声音又高又急促,一个音节跳到另一个音节,就像一个人卷着裤腿在溪流中踩着石头跳跃。讲完之后,你开始欣赏这件雕塑,但扎雷几乎没有时间赶去上课。他小跑着走向演讲厅,不像一个迟到的教授,而像一个在晴朗夏日早晨匆匆走向游泳池的男孩。
“没有什么比教大一化学更好的了,”他在路上说,“这是研究人员的秘密武器。这些孩子们真的让你思考。”
你跟着他走,发现自己在一个周一的早上也变得相当开朗。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到火星上的生命。
扎雷(Dick Zare)很小的时候,在家中发现了一些化学书籍。它们属于他的父亲,他父亲成为化学家的希望在经济大萧条中破灭了。父亲做过从冰淇淋小贩到地毯清洁工等一系列工作,他会告诉儿子不要碰那些书:它们只会带来不快乐。扎雷把书带到床上,用手电筒在被子里阅读。那是“禁书”。
他父亲的预言错了180度。快乐的时光是在书中度过的。与人相处,尤其是与父亲相处,更困难。迪克是那种玩“围着玫瑰转”游戏时都不肯牵手的孩子,他差点在幼儿园不及格,因为他不会系鞋带。他父亲曾试图教他,那是一次如此痛苦的经历,以至于他再也不想学了。五岁时,他接受了治疗,但没有帮助。三年级时情况变得更糟。他家从几乎全是犹太人的克利夫兰高地搬到了林德赫斯特,在那里扎雷一家是唯一的犹太人。圣诞节来临时,扎雷的老师问他为什么不和其他孩子一起唱颂歌,他回答说他不知道歌词,即使知道他也不会唱,因为它们是假的。他被其他孩子揍了一顿,并被称为“杀基督者”。
“我是否让你们感受到了事情的真相?”他问道,笑容现在带着痛苦,但依然纯真。“那是一场灾难。”他指的不仅仅是被揍。他指的是整个事情。童年。
但总有出路,一种能让自己感觉良好的方式。八岁那年,扎雷发现了一个地方,那里有成千上万本“禁书”像被子一样堆积如山,手电筒的光芒从不熄灭。在克利夫兰公共图书馆,他可以逃离数小时,阅读和下棋。(他现在仍然下棋。同时下几盘。蒙着眼睛。)在初中,他是个独狼,背着科学书去学校,那时他已经足够知识渊博,知道自己所知甚少。这导致了与他的科学老师的破坏性争论,那位老师认为如果他承认自己不知道某些事情就会失去对课堂的控制。最终,这位可怜的老师忍无可忍,直截了当地告诉扎雷的父母,他恨这个孩子入骨。校长决定,迪克离开这所学校是最好的选择。
不知怎的,他获得了附近私立男子大学预备学校的奖学金——扎雷怀疑是为了凑够犹太学生的名额。不管他最终怎么到了那里,结果都很好。他的天赋得到了认可和培养,尤其是一位名叫奇尔顿·汤姆森(Chilton Thomson)的英语老师。到了高年级,扎雷已经用战后剩余的继电器制造了一台原始计算机。当他赢得哈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时,汤姆森带他去了他的私人裁缝那里,为他量身定做——西装、鞋子、衬衫、领带,所有汤姆森自己上大学时的得体行头。
“我看着所有这些东西,问他我怎么才能报答他,”扎雷回忆道,“他对我说,‘老实说,你无法报答我。但总有一天,你可以帮助别人。’我一直珍视这些话。”
扎雷的课是早课,所以学生们进入演讲厅时都处于昏睡状态。那些清醒到能说出句子的人三三两两地低声交谈,而其余的人,背着背包,双腿叉开,等待咖啡因和生物钟启动大脑功能。一个小时内会有很多事情发生。这门课名为《化学科学前沿》,由扎雷和化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lman)授课,名副其实:它不拘泥于教科书,而是将学生们直接推向边缘,并辅以一些生动的指导,以防他们跌落。这门课以斯坦福大学最难的课程而闻名,但学生们投票选它为校园内最好的课程之一。
今天的讲座是化学分析入门的第二部分。在上一节课中,扎雷向学生们介绍了质谱法,这是一种通过离子碎片模式识别未知化合物的技术,当化合物受到电荷撞击时会产生碎片。扎雷用投影仪在屏幕上投射出两列数字:离子碎片的原子量(代表质子和中子的数量)以及每种碎片的丰度。课堂的挑战是利用这些信息揭示爆炸分子的隐藏身份。(对于你来说,三十年没上化学课了,挑战是不要放弃希望。)这些列显示,最大数量的离子原子量为96,其次是61。扎雷拿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道
96
-61
35
到目前为止,你还跟得上。他站开片刻,赞赏地看着这些数字,仿佛即使这么简单的问题也蕴含着某种奇妙的东西——一种能量,一种可能性。
“三十五,”他愉快地说,仿佛这是一个特别友善的数字。“这给了我一个线索。”
线索是元素氯的主要同位素原子量为35。96是总母分子的原子量,所以61一定是移除了一个氯原子的母分子。但这虽然揭示了氯是该化合物的一种成分,却存在一个问题:扎雷指出,氯有两种形式——普通的氯35和不那么常见的氯37。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原子核中多了两个中子,这改变了它的重量。因此我们利用这个新线索进一步解码碎片模式。
扎雷分发了一份作弊小抄,在黑板上做了一些数学计算,推导二项式展开的系数,你模糊地记得那是一种古老、庞大的难以理解的东西,而现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正在变得有意义。他用更复杂的计算填满了黑板,进入了更危险的领域,但他却无比耐心,仿佛他不是在教授,而是在自己重新发现。扎雷不时停下来,像雕塑家审视从石头中浮现的人物一样,观察着不断演进的解决方案。无论有意无意,这些停顿都给了学生们赶上并理解的机会。此时你已经迷失了,但他们正在朝着它前进,嗡嗡作响,18、19岁的年轻人焦虑感暂停了一小时,全神贯注于问题的核心。然后扎雷开始谈论爱因斯坦和E=mc²,最终这一切以一件相当惊人的事情告终,他说给学生们:“我想告诉你们一个疯狂的想法:可以通过分子的分子量来计算分子的能量。”
“顺便说一句,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他随口一说,就像把一颗种子撒进犁过的土地里,“所以去吧,去做吧。”
扎雷办公室门外贴着一张海报,上面公布了他最近在德国一所大学举行的一系列讲座。当你等他与一位研究生谈完时,你的目光游走在海报上的讲座主题之间。每一个主题都代表着他正在进行的工作的某个方向。大多数都以不熟悉的术语表达:利用共焦荧光显微镜进行溶液中单分子检测和双分子反应过渡态区域的可视化。扎雷讲完了,察觉到你的困惑,便走过来帮忙。他逐一将每个主题还原为本质。
“第一场讲座是关于我们开发的一种观察单个分子的技术,”他说,“那是分析化学的终极极限。你无法看到更小的东西。第二场讲座也是关于目睹不可目睹之物,在这种情况下,是化学反应中旧键断裂和新键形成这种亲密的动作。”他跳过了第三个标题《地外访客的实验室测量》,然后解释了第四个,它涉及一种检测基因缺陷的新技术。其他一些则提出了量化大气中微量化学物质的方法,或测量难以想象的微小时间尺度上的电信号,或研究记忆的生物化学。扎雷的研究具有许多吸引资助机构的特质。而“心无旁骛”并非其中之一。
“他就像个小孩子,”史蒂芬·彭托尼(Stephen Pentoney)说,他曾是扎雷的博士后,现在在贝克曼仪器公司工作,该公司已获得扎雷实验室产出的50多项专利中的几项授权。“他会参与到一切事物中。”
然而,对扎雷本人来说,“一切”才是重点。“你知道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是如何定义一神论的吗?”他问道,“那是一种相信最多只有一位神的信仰。嗯,我相信最多只有一门科学。我对划分不感兴趣。它们只会妨碍创造性科学的开展。”
扎雷实验室实际上是一个三层楼高的创造性科学熔炉,或者说是一个由独立炉灶组成的集合体,因为每个门背后都火焰熊熊。大约30名博士后和研究生互相帮助,但每个人都在锻造自己的创作。博士后罗素·洛(Russell Low)说:“这里有十几个独立的项目正在进行,每个项目都新颖奇特,每个都处于前沿。”洛和徐昊(Hao Xu)日夜观察着最简单的化学事件:当一个氢原子与由两个其他氢原子组成的分子碰撞时会发生什么?自由原子将分子分解,并取代其中一个原来的键合原子,这个原子则在纳米空间中嚎叫着离开。这种最基本的化学反应已经吸引了理论化学家和实验化学家60多年,但至今仍未完全理解。多亏扎雷、洛和徐开发的一种检测技术,它可能很快就会被完全理解。
隔壁,研究生丹尼尔·邱(Daniel Chiu)在一个由激光、镜子和显微镜组成的“城市”中,生活在一块黑布后面。他花了一年时间才搭建好这些仪器,但回报非常值得:一台能让他在一个室温溶液中观察和录制单个分子的设备。蛋白质是如何折叠的?总有一天,你只需看着屏幕就能知道。DNA分子是如何随时间演化的?再播放一遍录像,自己看。
扎雷实验室里挤满了像邱和洛这样的学生,虽然这些人如果不是有天赋和愿望就不会在这里,但扎雷是把这一切凝聚在一起的人,每周七天——至少在他不向国会作证、不飞往南极洲收集陨石、或不担任国家科学委员会主席的时候。这个职位给了他巨大的机会来帮助制定国家科学政策,他很享受这个前景。但没有什么比他的人更重要。
“我?我只是个大啦啦队长,”扎雷笑道,“只不过这个啦啦队长保留发出嘘声的权利。”然后他补充道,“如果这一切有个主题,那就是我们倾向于使用激光。”
你后来才意识到,他用一个更大的轻描淡写来掩饰之前的轻描淡写。“迪克对科学的贡献在于向化学家们展示了激光可以是一种多么神奇的工具,”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扎雷在哈佛的博士导师达德利·赫施巴赫(Dudley Herschbach)说,“他将其应用于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那些涉及分子之间亲密相互作用中实际行为的问题。他将我们带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
在他大学三年级时,扎雷开始思考我们是如何看的:不是关于视觉感知的生物机制,而是关于光的本质以及它如何与物质相互作用,从而首先产生可以被感知的模式。他曾被教导说,眼见为实;但如果他无法理解我们是如何看的,他又怎能相信任何事物呢?最初对光的好奇,变成了一场灵魂的危机。有一段时间,扎雷认真考虑过辍学。幸运的是,他找到了一些与他的才华相匹配的斯多葛主义智慧。例如:光既有波动性,也有粒子性。这令人沮丧。但你学会了与它共存。
1964年,他在分子光解离方面完成了一篇开创性的论文,讲述了光脉冲如何瞬间触碰分子并将其分解,其速度之快,以至于碎片在飞散时能提供关于该分子形状、它在空间中如何定位的线索。他的工作完全是理论性的,但当他接触到新发明的激光时,他发现可以用激光来魅惑分子,让它们咯咯地笑、跳舞,甚至在它们与其他分子发生化学反应这种亲密互动(也就是生命)时,展现出它们的本质。
扎雷利用光的众多技巧之一,也是他的同事们可能最赞赏的一个,涉及一种称为激光诱导荧光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激光束照射到分子上,促使该分子产生微小的、色彩斑斓的骚动,从而揭示其身份。分子吸收一种颜色的激光,被激发到更高的能量水平。当它跌落回基态时,会发出其他颜色,这种模式就成为分子的“指纹”。将激光诱导荧光与其他分子检测方法结合起来——例如,毛细管电泳(其发展也由扎雷率先开创,在此表示感谢)——你就能得到一个极其灵敏的探针,不仅能识别分子,还能揭示它们在任何特定纳秒时刻所处的能量状态。
相比这项发明,在火星陨石中检测可能存在的生命化学痕迹,似乎就像孩童玩耍。但你开始体会到,扎雷的所有工作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孩童玩耍。“我是个机会主义者,”扎雷说,“如果我遇到一个我不懂的问题,我就想解决它。所以总是有很多项目在进行。火星只是其中之一。但后来它爆炸了。”
几年前一个安静的夜晚,扎雷在校园里遇到一位陌生人,那人告诉他陨石中包含着来自外太空的信息,一切由此开始。
“这让我产生了兴趣,”扎雷说,“我告诉他,我想我有一台机器可以帮助解读那些信息。”
那位陌生人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彼得·布塞克(Peter Buseck),他曾在斯坦福大学度过一个学术休假。那台机器是扎雷实验室的另一项作品,以激光为核心,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是两台激光——微探针两步激光质谱仪。它的设计出人意料地简单。第一步:将有机物样品放入一个含有电场的真空室中,然后将一束红外激光脉冲聚焦在一个小目标区域,大小约相当于一个句号。脉冲只持续几百万分之一秒,但其强度足以以惊人的速度加热目标,每秒超过1亿摄氏度。这种快速的辐射冲击会从表面升腾起一团完整的、未受损的分子蒸汽。
在第二步中,这股上升的蒸气团被第二束激光袭击,这是一束紫外脉冲,亮度是第一束的60倍,但只持续几纳秒。这股难以想象的短暂能量爆发将中性分子中的一个电子撞掉,使它们带上正电荷。接下来是一场微型赛马。带着正电荷的分子从蒸气云中疾驰而出,冲向约五英尺外的一个带负电的探测板。平均而言,它们需要大约65微秒才能跑完这段距离。但由于不同分子的重量不同,有些分子跑得比其他分子快:分子越小,到达探测器越快。分子的飞行时间作为其质量的衡量标准,然后可以用来确定其身份。
扎雷和他的学生们开始用他的激光质谱仪分析陨石样本,只是为了看看里面有什么。很快,他和研究生西蒙·克莱米特(Simon Clemett)开始追逐更大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更小的颗粒:由U-2间谍飞机穿透平流层收集的星际尘埃团。大约三年前,他的一位合作者将扎雷介绍给了NASA约翰逊航天中心的戴维·麦凯(David McKay)和埃弗雷特·吉布森(Everett Gibson)。他们告诉他,他们有一些 intriguing 的陨石材料,问他是否可以帮忙分析一下。不久之后,克莱米特收到了来自NASA的三块岩石邮件。它们只被代码名米奇(Mickey)、米妮(Minnie)和高飞(Goofy)标识。
“我有所怀疑,但我们真的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克莱米特说,“我做了一些初步测试,JSC的人都兴奋不已。”他们要求他和小扎雷做更多的测试,但化学家们想知道大惊小怪的原因。这时他们告诉我们,这块陨石是火星的,他们正在寻找生命的迹象。
扎雷实验室发现的是多环芳烃(简称PAHs)的痕迹。这些有机化合物通常是微生物腐烂的产物。但扎雷怀疑火星微生物并非作用因素,因为PAHs也可以完全通过无机方式产生,而且以前在天外物质中也多次发现过。然而,与此同时,NASA的科学家们在陨石中发现了古代生命的其他可能证据——可能是由细菌产生的矿物质,以及可能是化石细菌本身的图像。扎雷仍然坚持着。然后,他和克莱米特发现,PAHs和这些其他痕迹并非随机散布在岩石中,而是聚集在碳酸盐球状体中。于是,他们也兴奋起来。即便如此,克莱米特还有数月痛苦乏味的工作要做,以验证他和扎雷发现的PAHs确实来自火星岩石。“我们最终相信,这个案例是可以成立的,”扎雷说。
NASA-斯坦福的研究人员决定是时候发表他们的结果了。然后,爆炸发生了。新闻发布会和宣传;收件箱里塞满了祝贺邮件;UFO绑架受害者打电话来,占用电话线,直到扎雷足智多谋的助手找到一个支持小组供他们咨询;以及所有扎雷称之为“火星狂热”的其他喧嚣。几乎立刻,他们就遭到了批评的反弹。反对者高喊证据不足,或者过于间接,或者模棱两可,或者这一切都是NASA为了阻止吝啬国会的斧头而编造的。大多数抱怨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完全恰当的。正如已故卡尔·萨根所评论的那样,非凡的主张需要非凡的证据,而这无疑是一个非凡的主张。
“如果我们被证明是正确的,”扎雷简单地说,“这意味着生命并非地球独有。如果火星在早期历史中能够支持生命,那么它很可能也在无数其他行星上演化。所以突然之间,宇宙变得更加激动人心和奇妙了。”
然而,扎雷首先承认,在火星生命仅仅是一个假设之前,还需要更强有力的证据。自最初的公布以来,他和克莱米特已开始在陨石中寻找氨基酸。如果这些蛋白质的组成部分与多环芳烃(PAHs)一同被发现,将进一步巩固这一论断。
扎雷和克莱米特也渴望继续对星际尘埃进行更困难的分析。问题在于其尺寸,或者说缺乏尺寸。在对火星陨石的研究中,两步激光装置锁定了重两三毫克的岩石样本。与这些宇宙尘埃颗粒相比,它们简直是巨石,因为这些尘埃颗粒的重量不足千分之一克。
“没有人分析过这么小的东西,”克莱米特说,“所以你发现的任何东西都是一个惊喜。”
一个惊喜,或许也是一个机会。从它们所含碳的同位素特征来看,这些粒子中的分子可能代表了我们太阳系凝结而成的原始星际物质。这种被扎雷称为“宇宙污垢”的物质,可能比实验室里研究过的任何其他物质都要古老,来源也更遥远。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机会。几十亿年前,地球只是一个贫瘠的球体,所有的碳都以二氧化碳的形式消耗殆尽。然后不知怎的,这个星球——也许火星也一样——获得了所需的碳,使一些事情得以发生:生命。很有可能,大部分碳是通过星际尘埃粒子带来的,就像现在正在研究的那些粒子一样。这让扎雷提出了一个对他来说大小和契合度都恰到好处的问题。
“生命究竟是什么?”他问道,“我小时候以为我知道答案,那时候人们会带我去动物园。生命就是动物奔跑、飞翔,或者植物消耗氧气。现在我们发现,生命更多地与细菌有关。我们正在发现细菌生活在氢气中,排放甲烷,生活在硫磺中,无处不在——而动物园里没有展示这些。生命原来比我们想象的要顽强得多。我想了解更多。”
你觉得他会的。而且他会玩得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