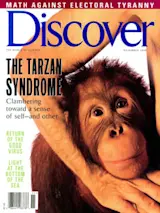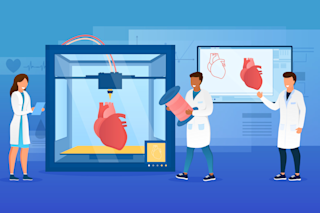你是说你认为你发现了一种细菌传染病,但你没有告诉我?亲爱的孩子,我不相信你完全意识到你可能已经找到了一种杀死致病菌的最高方法……而你没有告诉我!
嗯,先生,我想确定一下——
我欣赏你的谨慎,但你必须明白,马丁,这个机构的基本目标是战胜疾病,而不是做漂亮的科学笔记!你可能已经取得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发现之一……
确实可能。辛克莱·刘易斯1925年普利策奖获奖小说《阿罗史密斯》的主人公马丁·阿罗史密斯,接着利用他的发现对抗西印度群岛一场毁灭性的瘟疫。这当然是虚构的,但它反映了真实事物的希望。阿罗史密斯发现的细菌传染病是真实的,是新发现的一类病毒——噬菌体(细菌吞噬者)——的杰作,它们捕食其他微生物。在20世纪20年代,抗生素时代尚未到来,噬菌体看起来似乎是人们渴望已久的“魔术子弹”:一种强大、特异、持久的疾病疗法。
事实并非如此。多年来,噬菌体时常被用于阻止细菌感染,但既不持续也不令人信服。然后,随着20世纪40年代抗生素的兴起,噬菌体疗法被遗忘。当你只需服用几片青霉素就能焕然一新时,谁还愿意费心使用活的传染性病毒呢?西方科学家将噬菌体疗法束之高阁,埋藏在历史的尘埃中。
如今,它可能卷土重来。在抗生素预示着细菌性疾病终结约50年后,它们的黄金时代正在衰落。疾病当然依然存在——甚至可能正在上升。越来越多的微生物对我们的抗生素药物产生了耐药性,科学家们再次寻找奇迹疗法。有些人回顾过去,寻找那些几乎被遗忘的“食菌者”。事实上,噬菌体疗法从未真正消失。在远离西方医院和实验室的世界一角,医生和医护人员 routinely 使用噬菌体疗法来治疗各种疾病,正如马丁·阿罗史密斯所希望的那样。
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如费利克斯·德赫雷勒所坚持的。噬菌体疗法的坎坷历史始于这位易怒的法裔加拿大细菌学家,他在巴斯德研究所于1917年宣布,在调查巴黎一次痢疾爆发时,他发现了一种对引起疾病的细菌产生奇怪作用的东西。当他将这种神秘物质通过过滤器过滤,然后将所得液体倒入装有混浊痢疾细菌的试管中时,培养物突然变得清澈。两年前,英国细菌学家弗雷德里克·特沃特也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但他无法解释。对德赫雷勒来说,这毫无疑问。我立刻明白了:导致我培养物清澈的原因实际上是一种看不见的微生物……一种细菌寄生病毒。他称这种病毒为噬菌体。
这是一个大胆的结论。病毒在仅仅二十年前才被发现。你甚至无法通过当时最强大的显微镜看到它们;科学家们不得不从现有证据中推断它们的存在。在世纪之交,人们对微小细菌(除了显微镜外本身不可见)受制于更微小的微生物的说法,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接受程度。但德赫雷勒没有退缩,最终他的坚持取得了胜利。《纽约时报》在1925年宣布,“微小而致命的杆菌仍然有更小的敌人”。
虽然典型的细菌直径约为一微米(一微米是一毫米的千分之一,或一英寸的二万五千分之一),但噬菌体只有大约一微米的四十分之一,或一英寸的百万分之一。多亏了电子显微镜,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噬菌体构成了一支古怪的飞船状生物舰队——蛋白质月球着陆器,具有模块化的中空头部、隧道状的尾巴和细长的腿,以便更好地抓住粘滑的细菌表面。噬菌体将基因携带在其头部内,一旦降落在合适的细菌上,它会利用尾巴的核心在猎物的内部构建一个通道;然后它像子弹通过枪管一样将基因射入其中。一旦进入,基因就会迫使不情愿的宿主构建新的噬菌体,在四分之三小时内,多达200个新的飞船可能从微生物表面爆裂而出。这些年轻的噬菌体漂浮出去感染更多的细菌;不幸的宿主被炸成碎片,迅速死亡。
这就是为什么费利克斯·德赫雷勒怀疑这些非凡的食菌体可能会成为我们的盟友。就像它们在实验室培养皿中摧毁致病菌一样,也许它们也能在我们的体内摧毁它们。
这在当时是一个诱人的想法,现在也是如此,因为细菌对抗生素越来越占上风。现在对多种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的细菌包括:肺炎球菌,引起耳部感染、脑膜炎、血液感染和肺炎;葡萄球菌,住院患者中最常见的皮肤、伤口和血液感染病因之一;肠球菌,医院获得性伤口和尿路感染的常见病因;链球菌,引起链球菌性咽炎、猩红热、肺炎,以及最近的骇人食肉感染;以及霍乱弧菌,引起霍乱。肺结核也卷土重来。耐药性结核杆菌(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的出现,导致了有史以来最大杀手的再次流行。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受到感染,每年有200万至300万人死于肺结核。
但即使抗生素耐药菌没有如此迅速增长的威胁,噬菌体疗法仍然具有吸引力。抗生素存在某些风险。它们杀死多种细菌,而不仅仅是特定的目标,因此不仅清除体内有害微生物,还会清除有益微生物——例如,有助于消化的细菌。为了使抗生素疗法有效,患者必须在较长时间内认真服用多种剂量。一旦懈怠,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正在对抗疾病的新一轮攻击,这次是由耐药细菌引起的。抗生素可能导致肠道疾病和酵母菌感染。最后,有些人对抗生素有过敏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治疗可能比疾病本身更糟糕。
这些问题都不适用于噬菌体。噬菌体不会引起过敏反应,而且以挑剔著称——它们只针对它们应该攻击的细菌。如果你错过了一剂噬菌体,也没问题。因为它们在攻击的细菌内部繁殖,它们会在体内停留几天,然后身体才能将它们清除。
至少,这是想法。德赫雷勒大力推行它。痢疾、肠道疾病、伤寒、感染伤口、疖子、手术感染、霍乱、腺鼠疫——德赫雷勒用他的噬菌体治疗了所有这些疾病。他不是唯一一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都在试验噬菌体治疗。在20世纪30年代,制药公司礼来将噬菌体列入其生物疗法,并将其出售。噬菌体疗法产品甚至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许可。
然而,并非所有的报道都充满热情。即使是成功的报告也常常受到怀疑。德赫雷勒急于推广噬菌体,没有费心应用严谨的科学对照,比如给一些病人服用,对另一些病人不给药,然后比较结果以确定噬菌体治疗是否真的有效。许多其他噬菌体实验也同样缺乏有说服力的标准和对照。
吉姆·布尔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进化遗传学家,他特意阅读了当时的文献。“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评论,对数百项研究的评论,都表明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尝试噬菌体疗法,但没有一致的模式,”他说。“有时它有效;有时无效。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的群体生物学家布鲁斯·莱文同意道:“很难评估噬菌体疗法有多好。他们没有进行真正的对照。”
现在,莱文和布尔正在根据现代实验室技术重新审视噬菌体疗法,试图确定它是否真的有效。“我并非一定认为它会奏效,但至少有一个完整的传统可以作为起点,”莱文说。“面对所有的抗生素耐药性问题,我们必须尝试一些新的方法。”
因此,在1994年春天,莱文和布尔从1940年代以来少数几项噬菌体疗法研究中,挖掘出1982年英国研究人员H. Williams Smith和Michael Huggins的一项研究成果,他们发现噬菌体在治疗大肠杆菌致死性感染方面比抗生素在小鼠身上表现得更好。莱文和布尔与研究生Terry DeRouin和技术员Nina Walker决定亲自进行这项实验。
研究小组向15只小鼠的右大腿注射了一剂大肠杆菌,向左大腿注射了一剂噬菌体。另外15只小鼠注射了细菌但未注射噬菌体——这些是对照组。结果惊人。莱文说:“对照组小鼠在32小时内死亡。其他小鼠的大肠杆菌在它们的腿部形成脓肿,但它们都活了下来,全部15只。”然后,研究小组将噬菌体疗法与抗生素治疗进行了比较。他们向48只小鼠注射了大肠杆菌,然后将它们分成每组12只。八小时后,他们给其中一组小鼠注射了噬菌体,给两组小鼠注射了链霉素,而剩下的对照组小鼠只注射了生理盐水。这次,所有对照组小鼠都死了,24只链霉素治疗的小鼠中有16只——三分之二——也死了。但12只用噬菌体治疗的小鼠中只有1只死亡。再次,噬菌体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莱文现在想用噬菌体对抗葡萄球菌和肺炎球菌。布尔正准备用它们对抗沙门氏菌,沙门氏菌是伤寒和食物中毒的病因。
但所有研究人员都未鼓吹噬菌体治疗的前景——至少目前还没有。“我们不想给人留下我们认为噬菌体疗法是某种万能药的印象,”特里·德鲁安说,“它存在巨大的局限性。”最大的问题是噬菌体往往对某些细菌非常非常特异。这是病毒挑剔的缺点。虽然一种抗生素可以杀死多种细菌,但一种噬菌体只会针对一种或最多几种细菌。如果你没有精确选择正确的噬菌体,你就会倒霉。作为证据,研究小组尝试用不同菌株的噬菌体治疗感染大肠杆菌的小鼠;15只动物中有9只死亡。没有人希望在人类身上看到这种错误。
因此,在实践中,对于每种疾病,从最轻微的腹泻到中度的喉咙痛,甚至更糟,在开出噬菌体治疗之前,可能都必须进行培养和鉴定。那将是一项昂贵且耗时的苦差事。布尔提出了一个警告性的场景:“我的女儿几个冬天前得了肺炎。她发烧到104度,一直不退。我们尽快去看医生——大约在发病18小时后。他们给她做了脊髓穿刺、血培养,但从未诊断出是什么病。但他们还是给她注射了抗生素,不到6小时,她的烧就退了,她也好了。”
好吧,我们可能需要等待更长时间才能使用需要我们确切知道她感染了哪种细菌的疗法。要克服这个限制真的很难。我们可能真的要等到“奇迹药”用尽了,人们才会开始考虑噬菌体这样的疗法。噬菌体疗法需要一个惊人的成功。
费利克斯·德赫雷勒也有同样的想法。他相信他能在拥有1500年历史的第比利斯城——黑海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首都——找到他的成功。1934年,他在这个河谷城市与格鲁吉亚微生物学家乔治·埃利亚瓦合作了六个月,共同创建了现在被称为埃利亚瓦噬菌体、微生物学和病毒学研究所。它旨在成为噬菌体研究的世界中心。不幸的是,研究所研究员尼娜·查尼什维利说,由于斯大林时期艰难的政治局势,他们的梦想无法实现。1921年,在苏联成立三年前,俄罗斯入侵了格鲁吉亚。从那时起,直到70年后苏联解体,格鲁吉亚人民对恢复国家自治的任何希望都被系统地扼杀了。1937年,斯大林的残酷副手拉夫连季·贝利亚(两人都是格鲁吉亚人)下令逮捕埃利亚瓦为“人民公敌”。不久,他被处决。
德赫雷勒的宏大希望破灭了;他再也没有回到第比利斯。但研究所幸存了下来,从那时起,在西方几乎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它一直在为格鲁吉亚以及前苏联其他地区生产噬菌体。治疗范围令人惊叹。痢疾、食物中毒、伤寒、烧伤、皮肤感染、喉部感染、败血症和尿路感染只是其中一部分正在治疗的疾病。“如果有人患有肠道疾病,那人可以饮用噬菌体,”查尼什维利说。“如果是皮肤感染,噬菌体可以涂抹在患处。我们已经开发了气溶胶和片剂制剂。此外,研究所还研发出一种特殊的噬菌体疗法来对抗葡萄球菌感染。它是用于静脉注射,直接进入血液的。”
噬菌体也被用于杀死引起阴道感染和不孕的细菌,以及治疗肺部手术后的感染。它们被用于清除伤口感染;作为消毒剂,清洁手术室和消毒手术器械;以及作为预防性措施。例如,在手术期间,它们通常被应用于切口以预防术后感染。此外,查尼什维利说,噬菌体疗法已被前苏联各地的军事团体使用。如果他们进入疾病流行的地区,他们就会服用噬菌体。(其中预防的感染包括细菌性坏疽。)抗生素的出现并没有改变太多。“噬菌体疗法非常有效,尤其是与抗生素结合使用时,”查尼什维利说,“它能延缓耐药性的产生。”
格鲁吉亚国立儿科医院儿科主任伊拉克利·帕夫列尼什维利对此表示赞同。他的医院使用噬菌体疗法来对抗耐药微生物。“我们在抗生素耐药细菌感染方面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他解释道,“它们对阿米卡星、庆大霉素、头孢菌素——这些作用范围很广的第三代抗生素——都产生了耐药性。但相同的菌株对噬菌体非常敏感。噬菌体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事实上,效果非常好,以至于在儿科医院,给每个孩子服用噬菌体成为标准做法。帕夫列尼什维利说:“孩子一到这里,就会立即服用噬菌体进行预防。”“这有助于防止沙门氏菌,以及志贺氏菌和葡萄球菌(所有这些都是痢疾)的传播。”这意味着每年要给多达11000名儿童服用噬菌体。从1987年(该工作的第一年)到1992年(最后一年),感染率下降了六倍。“我可以告诉你,这些噬菌体绝对无害,”帕夫列尼什维利说。“即使你没有得到临床改善,你也不会损害肝脏、肾脏或任何其他功能。而且这些噬菌体都不会损害正常菌群——只会损害致病菌群。”
这种方法强调了噬菌体疗法的灵活性。除了能够针对特定感染开具特定的噬菌体外,医生还可以通过将多种噬菌体混合在一种制剂中来提供广泛有效的剂量,就像广谱抗生素一样。尼娜·查尼什维利解释说:“为了扩大治疗范围,我们像调制鸡尾酒一样将噬菌体混合在一起。”噬菌体鸡尾酒通常包含本地菌株,甚至来自特定患者的菌株,因为这些菌株最有可能阻止本地细菌。而且,由于一些非凡的监测工作,研究人员精确地知道需要阻止哪些细菌菌株。
尼娜的叔叔特穆拉兹·查尼什维利(Teimuraz Chanishvili)担任该研究所科学负责人已有36年。他说:“1967年,卫生部长颁布了一项法律,要求我们将前苏联所有共和国分离出的所有致病细菌菌株都送来。”“我们收到了42,000个菌株。我们正在对这些菌株测试我们的噬菌体疗法。这是一项非常耗费精力的实验室工作。但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建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噬菌体库,它们具有相当广泛的作用范围。之后,我们就可以预测致病细菌菌株,并从我们的文库中选择合适的噬菌体。”
噬菌体培养的原理很简单——有细菌的地方通常就有捕食性噬菌体——但实际情况却很复杂,需要大量劳动。研究所的任务包括在试管中培养其大量的致病菌,筛选出攻击它们的致命噬菌体,在细菌农场中培养大量的病毒,并对它们进行分类和储存以备即时使用。特穆拉兹·查尼什维利已将这一程序提升到艺术水平。在1990年的巅峰时期,研究所已发展成为一个能够为大多数需求提供各种噬菌体,并能快速为疑难病例培养专业噬菌体的机构。查尼什维利说:“那是最快乐的时光。我们拥有良好的设施和足够的资金来开展真正的研究。”
然而,也存在一些限制。并非所有疾病都能用噬菌体治疗。查尼什维利说,由肺炎克雷伯菌感染引起的肺炎,尚无特异性噬菌体。噬菌体目前还不能用于对抗结核病或性传播微生物淋病和衣原体。而且,由于噬菌体,就像它们攻击的细菌一样,对身体来说是外来物,当它们进入血液时,可能会引起免疫反应。查尼什维利解释说:“如果你将噬菌体用于眼睛、耳朵和喉咙,吞服以改善内部系统,或涂抹在皮肤上,都没有问题。”“但如果你想进行注射,它可能会引起反应。”这种反应包括抗体积累,最终可能中和噬菌体——患者会经历几个小时的轻微发烧。但没有必要让这个过程达到那个程度。查尼什维利继续说:“你使用噬菌体几天后,就必须检测抗体是否出现。如果出现,你只需更换制剂。”对于婴儿,由于他们的免疫系统不像成人和年长儿童那样发达,这种反应甚至从未发生过。
与抗生素疗法不同,细菌通常不会变异以对鸡尾酒中的所有噬菌体产生耐药性,但如果它们发生变异,查尼什维利说,你可以获得新的噬菌体。而且,噬菌体的生产成本远低于抗生素。
布鲁斯·莱文对此并不信服。“我预计那里的惯性比这里大。即使机构不奏效,它们也更不容易消亡或衰落。我建议在看到一些数据之前保持谨慎。现在是时候让外部科学家去那里认真看看他们一直在做什么了。”吉姆·布尔说,“我很怀疑。”
老问题:听起来很棒,但证据在哪里?“有对照研究,”尼娜·查尼什维利坚持说。确实有。但几乎所有这些研究都是俄语的,西方科学家很少见到,而且其中很少有能达到西方标准的——这仍有待确定,如果西方将来决定关注第比利斯的话。
但即使没有研究,超过半个世纪的经验难道不算数吗?伊丽莎白·库特认为算数。库特在华盛顿州奥林匹亚常青州立学院进行噬菌体分子生物学研究,曾多次访问第比利斯,并与研究所科学家合作进行基础噬菌体研究。她毫不怀疑那里正在发生有价值的事情。“这不是高科技,也不是生物技术,所以西方人,少数知道它的人,往往不信任它。但如果它没有任何作用,他们就不会一直使用它。这非常值得探索。”
她也毫不怀疑噬菌体疗法可能很难推销。它不像抗生素那么干净整洁。你有生物物种会变异并以各种混合物结合。让这样的东西通过FDA将很有趣。
与此同时,西方医学步履蹒跚,努力应对传染病爆发性复苏。第比利斯的噬菌体疗法也步履蹒跚。噬菌体研究所最辉煌的成就发生在几年前并非偶然。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格鲁吉亚一直深陷内战和混乱之中。鼎盛时期,该研究所曾拥有约700名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如今,这个数字可能还不到200人。位于姆特克瓦里河畔的庞大园区正在坍塌。水电每天只能供应几个小时。走廊阴暗,门锁着,窗户在风中吱呀作响。由于前苏联客户的需求瓦解,设施恶化,政府支持几乎为零,该研究所的噬菌体生产时断时续,新的研究已不可能开展。
“我们处境艰难,”尼娜·查尼什维利说,“如今研究所只剩一半的生命力——但它仍然存在。”
它仍然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费利克斯·德赫雷勒会欣赏这种讽刺——西方越来越绝望地寻求治疗细菌性疾病的新方法,而第比利斯噬菌体研究所,作为这些疗法的源泉,却越来越绝望地仅仅为了生存。他可能会欣赏它,也就是说,在他没有对世界其他地方不关注而大声疾呼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