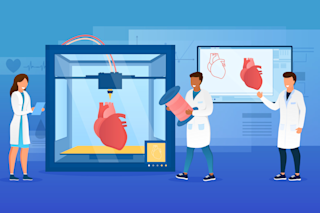无论是为了出版一本关于世界健康的著作而挑战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院长,还是挑战宇宙学的巨擘,罗伯特·兰扎从未循规蹈矩。因此,这位叛逆的医生引领医学界最具争议的领域——为治疗而创建克隆胚胎以及工程制造备用人体器官——也就不足为奇了。
治疗性克隆的价值对兰扎来说一直很清楚,他早年在南非心脏移植先驱克里斯蒂安·巴纳德手下工作。从那时起,兰扎就明白组织移植的障碍在于受体的排斥反应。从整个器官到一定剂量的胚胎干细胞,如果组织的DNA来自其他人,那么在没有强效免疫抑制药物的帮助下,移植就会被排斥。兰扎发现,“治疗可能比问题本身更糟糕。”但是,胚胎克隆,作为一种源源不断的、带有个人DNA印记的干细胞来源,可以改变这种局面,使其有利于患者,并预示着医学领域一场堪比抗生素和疫苗所带来变革的范式转变。
兰扎一心一意地追求这个新时代,这在科学洞察力和开创性发现方面都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如今,他已是再生医学领域的世界级力量,他已接近提供可能重塑免疫系统、治愈受损心脏甚至挽救肢体的细胞疗法。然而,近20年来,政府政策一直让他的创新成果“束之高阁”。他曾因操纵胚胎而被指责为杀人犯,一度人身威胁如此普遍,以至于他认为自己会被杀害。
经受艰难困苦并为自己的信念而奋斗,这很适合兰扎。他在波士顿罗克斯伯里区(Roxbury)和后来的郊区斯托顿(Stoughton)的贫困环境中长大,与母亲关系紧张,与职业赌徒父亲疏远。兰扎说,他一年到头很少被允许进入自己的家,除了吃饭和睡觉。无处可去,他将青春时光都花在附近的荒野中,沉浸在大自然的奥秘里。
尽管兰扎最初在学校被贴上“迟钝”的标签,但在1969年,年仅14岁的他将黑鸡的基因转移到白鸡身上,这一成就使他脱颖而出,而此时距离科学家破解遗传密码仅过了三年。这项非凡的早期壮举最终发表在《自然》杂志上,预示着他拥有原始的科学天赋,他的导师(其中包括乔纳斯·索尔克和B.F.斯金纳)将其与爱因斯坦的天赋相提并论。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称兰扎是电影《心灵捕手》中虚构天才的“活生生的化身”,他的马萨诸塞州口音和兰扎一样浓重。
如今,兰扎住在马萨诸塞州一个小湖中的一个岛上,那里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化石和恐龙骨骼博物馆,四周环绕着他所珍爱的大自然。《发现》杂志高级编辑帕梅拉·温特劳布在兰扎的伍斯特办公室采访了他。
你一直反抗权威,不是吗? 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对我这个来自罗克斯伯里,家庭粗糙且缺乏教育的孩子,有不同的计划。会有争吵。警察会被叫来。
斯托顿公立小学有三个班级:A、B和C。我被分到C班,和那些对着老师扔纸团、留过级的孩子在一起。
你是怎么应对的? 附近有个高尔夫球场,所以我通过收集和归还高尔夫球来赚钱。攒够18.95美元后,我就可以通过邮购一只小松鼠猴,它被刊登在《野外与溪流》杂志的背面,坐在一个女人的手掌里。我寄去了钱,然后就忘了这件事,但一年后我放学回家,厨房中央就有一只猴子,被绑在一个装着颗粒的盒子里。“别靠近,它会攻击人,”我妈妈说,但那只小小的松鼠猴宝宝却在打喷嚏;它感冒了。我走过去,它就蜷缩起来。它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它就像一个小人儿——小指纹,一切都像。它实际上比我很多朋友都聪明。
那时我独来独往。我下池塘抓咬龟。我冬天在野外走了几英里,循着脚印追踪浣熊。有一次,气温低于零度,我掉进了离文明世界15英里远的池塘里,水没到了腰部。我爬上树,在树洞里捕捉小猫头鹰。我进行长途跋涉,试图弄清宇宙的运作方式。即使在那样的年纪,我也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敬畏和惊奇。
一只松鼠猴和大自然维系着你。这足够了吗? 幸运的是,我还有一个邻居,芭芭拉·奥唐纳和她的丈夫尤金——非常好的人。如果我带虫子给他们,他们会给我买放大镜;如果我发现鸟蛋,他们会给我买一本关于鸟的书。时不时地你会遇到一个无私奉献的非凡人类,芭芭拉·奥唐纳就是那样的人。当一个黑人家庭搬到隔壁时,邻居们试图阻止,但芭芭拉出面干预了。她总是为正义而战。人们说你继承了父母的超我结构。嗯,不是我的父母,但希望我继承了芭芭拉和尤金的。今天,我的同事、[天主教]教会、总统甚至教皇都可以攻击我,但你知道吗?我见过更糟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我在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你很幸运能得到这样的好意和支持。然而,学校官员还是让你留在C班? 我五年级的时候,我的老师意识到我与C班格格不入,并鼓励我做一个科学项目,所以很自然地我做了关于动物的项目,我的好朋友史蒂文做了关于岩石的项目。他得了第一名,我得了第二名。那是我的第一次参赛。从那时起,我开始觉得我不应该因为我的家庭情况而被标签化,人们应该能够证明自己。
我想你就是这样证明自己的。 之后每年我都做一个科学项目,八年级时,我的邻居芭芭拉·奥唐纳成了我的科学老师。如果不是她当时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就不会有今天。她安排我进入高中的荣誉生物班,这个班实际上只对A组顶尖的学生开放。这引起了混乱,因为我超越了所有在我前面的人。“在这个唯一的荣誉生物班里,他们竟然有一个失败者……这是什么老鼠拖进来的?”我决心证明他们错了。于是我萌生了一个想法,要赢得整个科学博览会,这只有高年级学生才能做到。我的计划是改变一只白色动物的基因组成,使其产生色素。
遗传密码在三年前,即1966年才被破解。你却计划进行基因工程。 我的荣誉生物老师告诉我那是不可能的。这让我觉得很有挑战性。我从高尔夫球中攒下了零钱,然后乘坐公共汽车和电车去了哈佛大学康特威医学图书馆。我最终找到了一篇关于使用乙醇从细胞中提取核蛋白(含有DNA)的文章。芭芭拉开车带我去了一个农场,获取了有色素鸡下的蛋,我们又找到了另一个农场,获取了白普利茅斯岩鸡下的蛋。我仍然记得当时努力弄到设备。我去医院,说服他们给了我注射器。另一家医院给了我青霉素,这样我的动物就不会感染,我还找到了一个在州实验室工作的人,他地下室里有离心机和化学品——我就是在那儿提取的DNA。但我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家里完成的。我妈妈不允许我在房子里放任何东西,所以我找到了地下室炉子旁边的一个未完工的后屋,在那里,在一个小角落里,我为白鸡卵建造了一个孵化器。在非常早期的阶段,我用注射器将色素基因引入了白色胚胎。这当然非常麻烦,因为我必须弄清楚如何制作鸡蛋,以便你能看到正确的位置在哪里,而且大部分都会被我杀死或死亡。我正在努力改变鸡的基因组成,而我妈妈却在和邻居聊天,说:“哦,是的,罗比正在努力孵化鸡卵。”

空 | 迈克尔·刘易斯
成功了吗? 一些白鸡出生时带有色素斑块。但要真正证明这一点,我必须对我的实验进行盲法和对照。我需要更正确地进行这些实验,而不是在我的地下室里,现在我正在想,“好吧,我真的需要找一个懂这些东西的人谈谈。所以我要去地球上最伟大的地方,哈佛医学院,我要和一位哈佛医生谈谈。现在是时候把这件事提升一个档次了。我们要认真起来了。”
你预约了吗? 哦,不。我甚至不知道要去哪里。我四处走动,问别人如何找到哈佛医学院。我一无所知。我终于找到了它,那花岗岩和被世代人来人往磨损的石板台阶。我的内啡肽在飙升。我走到前门,警卫不让我进去。我不会那么轻易放弃。我绕着大楼试了所有的门,但一切都锁着。于是我站在一些垃圾桶旁边,试图看起来不引人注目,直到有人走过来——一个矮个子男人,秃顶,穿着卡其裤,手里拿着一串钥匙。我以为他是看门人。所以他打开了门,我就溜了进去。他继续走着,但在走廊走到一半的时候,他转过身说:“先生,我能帮您吗?”
“不,我在找一位哈佛医生。”我说。
那时我不知道,这位正是神经生物学系主任史蒂芬·库夫勒。我却告诉他,我认识一个住在我家街角的看门人,我在学校食堂洗盘子。我说,我也是弱势群体。他知道我把他当成了看门人。他说:“你为什么来这里?”我说:“哦,这和核蛋白以及诱导白化鸡的黑色素合成有关。”我看得出我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不知道DNA是什么,[我想]。最后他说:“嗯,我想我知道有人能帮你。”我记得他带我坐电梯上去,经过所有的面条状电线、那些神经生物学设备和电路——那真是太棒太令人印象深刻了——直接到了乔什·桑斯那里,他现在是哈佛大学脑科学中心的负责人。他当时只是个研究生,正在给毛毛虫插探针,观察它们的神经元。我跟乔什聊了一整天。最后他们邀请我回去正确地重复实验。这篇论文最终于1974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看门人时不时地出现,我看到他都很兴奋。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谁。
那么高中里发生了什么? 老师给了我C,其他人得了A。他不喜欢我的写作方式,但当我赢得州科学博览会后,我的成绩就被改了。科学博览会那天晚上,我妈妈试图阻止我出门。“你哪儿也不许去。”她说。芭芭拉在前门按喇叭,等着载我。我说:“妈,我要去。我才不管你说什么。”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反叛。我记得她泪流满面。当我到达时,整个体育馆的人都溢到了后门。然后他们从下往上颁奖,第四大奖,第三大奖。然后我是第一大奖,我注意到我妈妈在里面——她确实最后出现了。然后我获得了马萨诸塞州医学会奖,《波士顿环球报》也给了我一个奖。那是我的平反,证明我并不愚蠢。
你进入了常春藤盟校,很快就与心脏移植外科医生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合作。这是怎么发生的?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我参加了大学学者项目。我们作为本科生可以选修任何喜欢的课程,所以我从1975年开始选修医学院的课程。那是心脏移植医学领域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所以我想去南非与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合作。我写信给巴纳德,他说:“是的,你可以来。”那段经历既令人着迷又可怕。一些心脏移植患者的免疫抑制药物用完了;他们无法呼吸。他们坐在轮椅上。他们的身体正在排斥器官,他们正在家人围绕下死去。无论如何,我带着与巴纳德合著的一大堆论文回到了费城。
显然你没有从事外科手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到我从医学院毕业时,心脏移植手术已经很普遍了,所以我搬到了洛杉矶,做了一件我从未告诉过别人的事:我花了几年时间攒硬币,吃罐装菠菜和意大利面,同时试图理解宇宙,我觉得这项努力已经走到了死胡同。
放下一切,花几年时间思考宇宙学,这可能被称为自我放纵。 对我来说,这相当于在欧洲徒步旅行——我是在宇宙中徒步旅行,我需要思想上的自由来思考。告诉你,把这个谜题拼凑起来并非易事,但两年后,我提出了一个关于宇宙的新理论。
你与天文学家鲍勃·伯曼合著的关于这项工作的书,名为《生物中心论》,即将出版。在书中你提出,我们当前的宇宙理论除非考虑到生命和意识,否则将永远无法奏效。你能解释一下吗?
看看这个咖啡杯。你说它就在那儿,但事实是你无法通过大脑看到它。你的大脑外面有一层骨头。发生的事情是你所看到的一切都在你的脑海中重构。我们有空间和时间这些词,但你无法触摸它们。它们不是物体,它们不是事物,它们是永恒的。空间和时间实际上是动物感官知觉的工具,是我们组织和构建信息的方式。
你曾暗示现实是由有意识的观察者决定的。大多数物理学家将意识视为一种偶然。 今年二月《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它表明如果你用光子做实验,把它放进仪器里,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会改变过去已经发生的一个事件。这不是很奇怪吗?这就是你和我在的同一个宇宙。这个实验中的物理学怎么会表明如果你现在做某事,它会追溯性地改变一个已经发生的事件?你可以玩你的小游戏,但无论你怎么切割这块馅饼,如果你观察一个物体,它表现为粒子,而如果你不观察,它就表现为波。这并非系统的人为产物。这些实验是真实的。接受它吧。
你说过物理定律是精确平衡的,以使生命存在。 如果大爆炸的质量有十亿分之一的差异,你就不会有星系。如果引力常数有丝毫不同,你就不会有恒星,包括太阳,你就只会是氢。这样的参数有200个。我们现在有人在谈论智能设计,说“上帝”是解释。但这实际上是因为量子理论是正确的:一切都是观察者决定的,过去和现在只相对于你这个观察者。这一切都吻合,但问题是,你确实需要接受人们不会接受的事情:当你背对月亮时,它就不再存在了。
尽管宇宙充满不确定性,你还是去追求一个最切合实际的目标。 考虑到我在宇宙中的微小作用,我认为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努力治疗甚至治愈糖尿病,以及其他影响数百万人健康和生命的疾病。我没有像心脏那样移植整个器官,而是决定用细胞来工作——从生物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看,细胞是现实的基本单位,也是我们观察者决定世界的基础。我接触的人是帕特里克·很快-熊(Patrick Soon-Shiong),一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他正试图移植产生胰岛素的细胞——胰岛,作为糖尿病的治疗方法。那里的障碍与我们面临心脏移植时的障碍相似:克服组织短缺和预防排斥反应。

空 | 迈克尔·刘易斯
策略是什么? 起初,我以为我们可以从尸体或动物身上分离出胰岛,然后把它们装进小胶囊里,以保护它们免受排斥。我们成功地为我们的第一个病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是一位患有胰腺炎的波音公司高管。他不得不切除胰腺,我们没有把他的腺体扔掉,而是把它带回实验室,取出了大约5万到10万个产生胰岛素的细胞。我们将这些细胞注射回他的门静脉,它们在肝脏中安家,这个人就好了。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意味着如果你能提供一个人自己的细胞,你就能消除排斥反应的风险,而且你可以在他余生中为病人提供产生胰岛素的细胞,而无需注射胰岛素。
你是怎么从胰岛细胞转向胚胎细胞的? 大约在1990年,我还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时候,马萨诸塞州舒兹伯里的BioHybrid Technologies公司找到了我。起初我想:“我为什么要离开阳光明媚的加州,回到雨雪交加的地方呢?”但我还是去面试了,总裁,一位名叫比尔·奇克(Bill Chick)的杰出人士,问我什么能让我开心。我提出了一个我认为荒谬的薪资数字,等我回到家,就收到了消息说被接受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低于市场价。在公司圣诞派对上我遇到了他的女儿,她说:“所以你就是那个系着俗气领带的人。你就是我爸爸偷来的那个人。”
原来,奇克自幼患有糖尿病。现在他快要死了,但他想用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提出的封装方法来挽救自己。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竞赛——比尔做了太多的血管成形术和心脏手术,他快要散架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真的在狗身上取得了成功。我们从健康的狗的胰腺中提取了胰岛细胞,将它们封装起来,然后移植到患有糖尿病的狗身上,这些狗变得不再需要胰岛素了。就在那时,我得知了克隆羊多利,它是由苏格兰爱丁堡罗斯林研究所克隆出来的,我说:“啊哈!就是它了。”如果你能创造一个基因上与成年个体相同的胚胎——也就是说,一个克隆体——你就可以收获免疫相容的细胞,替换你想要的任何组织,而不用担心排斥反应。
本质上,克隆体会为亲本提供干细胞吗? 对。胚胎干细胞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如果它们来自另一个个体,仍然存在排斥问题。你仍然需要强效免疫抑制药物,而这些药物会导致癌症。我的想法是克隆患病的个体,不是为了繁殖,而是为了治疗。通过这种治疗性克隆产生的干细胞,像其他胚胎干细胞一样,能够发育成多种细胞类型,并作为身体任何需要补充的部位的修复系统。你解决了排斥问题,并且拥有无限量的组织。我试图说服比尔尝试这种方法,但他不为所动。最终,他中风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1998年,他死在了我眼前。
后来我得知,BioHybrid公司附近街上有一家世界顶级的克隆公司,叫做Advanced Cell Technologies,简称ACT。这简直就像命运的安排。那时我已经对马萨诸塞州产生了感情。我买了一个小岛,住在那里。我的化石和恐龙骨骼都在那儿,我还对岛屿进行了景观美化。我的岛上有天鹅;有一个海狸,还有一个离我家门10码远的海狸窝。我想留在那儿。
所以你去了ACT并找了份工作? 在他们雇用我之前,他们给了我一项任务,就像带回女巫的扫帚一样。有一个问题是国家卫生研究院是否会允许这项工作。尽管这是为了治疗而不是繁殖,但它仍然涉及克隆胚胎,公众完全反对。许多人认为这是谋杀。所以我被要求让全国所有诺贝尔奖获得者签署一封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信,致给NIH的负责人哈罗德·瓦姆斯。那是在老派的时代,一切都通过传真。实际上,我有一个装满了7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签名的信件的抽屉。这项努力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几个月后,许多大学校长也签署了。
当时,ACT是一家家禽遗传公司的子公司,从事农业工作。当我加入时,他们从动物克隆转向人类治疗,我们知道我们会受到巨大冲击。我可能是唯一一个受到[天主教]教会、教皇和几位总统谴责其工作的人。一度我们这里有保镖。街上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然后一家当地体外受精诊所的一名医生被锁定为目标。我当时觉得我活不过几年了。
而你,独自一人在岛上,是如此容易受到攻击。 我会出去散步,听着周围的声音。我是克隆领域最受关注的人之一,却又如此孤立。我估计有超过50%的机会会被干掉。但我仍然想尝试着走出去。我一直都跟着我的心走。
你能描述一下ACT最初的突破性工作吗? 我们将成人细胞的人类DNA注射到去除细胞核的卵子中。我们成功地克隆了早期胚胎,它们长到四到六个细胞大小。这显然远未达到获得干细胞所需的囊胚(一种具有更大细胞团的胚胎)。事实上,即使到今天,在多利羊克隆十年之后,科学家们仍然没有克隆出足够发达的人类胚胎来产生患者特异性细胞。
您一直在探索其他生产患者特异性细胞的方法。它们是什么? 我们最近发表了一篇关于我们创造的一种细胞——血管造血祖细胞的论文,这种细胞仅在胚胎中短暂存在,但在成年个体中不存在。我把它们想象成独角兽,这些我们假设并寻找多年的难以捉摸的细胞。血管造血祖细胞能够发育成所有血细胞——包括免疫细胞、红细胞,所有血液系统以及脉管系统——它们一直是生物学的圣杯。我们发现我们可以从人类胚胎干细胞中制造出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个这样的细胞。现在我们拥有了它们,我们正在首次利用大自然早期最深刻、最强大的细胞构建模块之一。关键在于,我们可以利用短暂的中间细胞,如血管造血祖细胞,作为工具箱来修复成年个体,这样您就不必截肢,您可能不必失明,以预防心脏病发作。我们可以通过在它们分裂时添加某些分子来引导它们发育成不同的细胞类型。
它是如何工作的? 我们发现,当我们把这些细胞注射到受损的缺血性肢体中时,一个月内血流几乎100%恢复。以前,这条肢体本应被截肢,但现在它得到了恢复。至于心脏病发作,注射这些细胞使死亡率降低了一半。
由于这些细胞能产生免疫系统,那么用它们来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呢? 有80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有趣的是,当人们因癌症进行骨髓移植时,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会进入缓解期,就好像免疫系统被消除并允许从头重建一样。利用作为免疫系统祖细胞的血管内皮祖细胞,我们也希望能替换免疫细胞。
还有其他类似的中间胚胎细胞,能形成神经系统或大脑吗? 是的。你可以这样想:你有一棵树,它的枝条会产生身体所有不同的组织类型。例如,血管造血祖细胞会产生一个分支——血细胞、血管和免疫系统。但也有神经干细胞以及早期祖细胞,它们在身体的大多数其他系统中都具有这种可塑性。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发现如何分离和扩增它们。
你只用细胞有点局限。你最初和克里斯蒂安·巴纳德一起移植心脏。 为了充分发挥干细胞的潜力,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将它们重构为更复杂的组织和结构。因此,如果我们要制造动脉、骨骼,甚至整个肾脏或心脏,我们就需要学习如何在可生物降解的支架上组装和培育它们,这些支架之后可以被人体吸收。在一项研究中,我们用这些细胞制造了小肾脏,甚至可以产生尿液。尿液中含有浓缩的肌酐或尿素,这意味着肾脏实际上正在从血液中清除有毒物质。整个膀胱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生长的。其他研究人员正在为关节制造骨骼、心脏瓣膜和软骨。
这似乎是前所未有的救命技术,但这项工作却因政治而受阻。当这些细胞被存放在实验室里,而你却能帮助人们时,这一定令人沮丧。 四年前,我开车去上班,行驶在一条安静的小路上,限速每小时15英里。我急匆匆地冲进停车场,旁边停着一辆警车。我差点撞上它。“哦,天哪,我完了,”我想。我走进办公室,开始工作,几分钟后,隔壁办公室的一位科学家走了进来,说:“鲍勃,外面有位警察想见你。他带着手铐和枪。”整个实验室都以为他是来逮捕我的。他说:“兰扎医生,我能和你到你办公室谈谈吗?”所以我把他带了进去。原来我刚刚发表了一篇论文,表明我们可以创造出能够恢复动物视功能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这位警官有一个16岁的儿子,如果没有这种疗法,两年后他将完全失明。当他讲完他的故事时,我几乎要哭了,因为我们有这些细胞,而且它们当时已经冷冻了九个月。
你为什么不能把它们从储藏室里取出来帮助那个男孩? 我们没有2万美元,那是我们进行与人合作所需的临床前研究所需的费用。那时,我们的电话已经被切断了。我们没有传真机。我甚至负担不起我的吸管的瓶装水。重点是,根本没有资金,因为基础研究通常由政府资助,而政府不会资助干细胞研究。
你还在保险库里存放着什么,仍未获得资助?
我们拥有能逆转患有脊柱裂无法行走的绵羊瘫痪的细胞。在注射我们的细胞后,我们治疗的第一只动物恢复正常,行走自如。同样的模型也适用于瘫痪的人类,但由于缺乏资金,我们五年内未能重复这项实验。本可以治愈的人却坐在轮椅上。
几年前,一位女士联系了我。在肿瘤化疗过程中,可能有什么被激活了,出于某种未知原因,她小脑中的神经胶质细胞开始退化。她是一位有很多孩子的女士。她慢慢地开始失去说话的能力。她开始使用助行器。她越来越糟,不久前,她去世了。
你本可以帮助她吗? 是的,我们有细胞,可能只需注射一次就能帮助她。她的一个儿子一直来问:“你们能做些什么吗?”但我们没有资源去完成FDA的程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知道这项工作被耽搁了,真是令人心碎。
在这一切之中,你还在努力实现你的第一个梦想吗,那就是从人类克隆体中获取胚胎干细胞? 我们正在继续这项工作,但由于诱导多能干细胞(iPS细胞)——即已被重编程回胚胎状态的成人细胞——的发现,紧迫性有所降低。我们正在研究重编程皮肤细胞的新方法,这将使我们能够安全地创建一个干细胞系库,使其与整个人群高度匹配。结果显示,只有100个细胞系就能为您提供50%的美国人口的完整单倍型或免疫匹配。这些重编程的细胞争议较小,因为您不需要使用克隆或胚胎。
这些技术预示着人类寿命的未来会怎样? 事实证明,人类寿命在接近120岁左右的上限时趋于平稳。通过消除传染病、一些慢性病和癌症,我们可以将寿命延长到100岁以上。我认为,通过组织工程,我们可以像修理自行车轮胎一样修补你,用一个肾脏替换一个肾脏,用一个心脏替换一个心脏,达到大约120岁。我一直认为这是极限。但有了这些血管生成祖细胞,我现在开始质疑我自己的规则。这些细胞可以进入并修复内部受损组织,几乎就像纳米粒子一样。我们也许可以用类似的神经元细胞系做同样的事情,修复大脑本身的损伤。因此,如果它继续以这种方式发展下去,我们可能会打破这个天花板,就像打破音障一样。我将非常不确定寿命将走向何方。
你正在开创医学的未来,但它仍然停滞不前。 我们不是在治疗疾病,而是在试图绕过神学问题。这与我医学院所学的知识不同。我无法告诉你我多少次举手说:“够了,我受不了了”,但第二天我又回来了。我们步履维艰,但他们无法永远阻止我们。我们现在有足够多的努力,希望有办法绕过许多这些反对意见。但这只是一个遗憾,研究被搁置了这么久。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范式转变。人们会回过头来看我们,说:“他们以前会把人的腿截掉。”然后他们只需打一针,血液就会恢复,肢体就会得救。如果我是一个病人,我知道我的腿要被截掉,而且有什么可以做的,我就会要求它。但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科学家,都不知道我们有能力做什么。我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我正在做这项工作,我可以看到在我眼前什么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