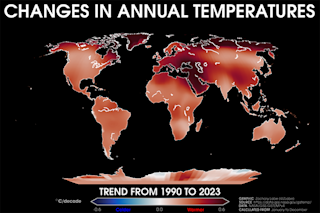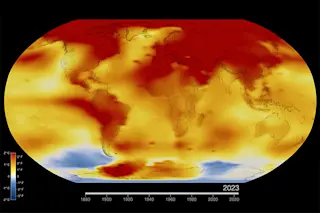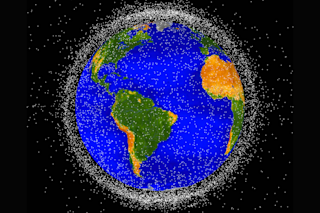《经济学人》有一篇关于“印度两栖动物的命运”的精彩文章,以及一个普遍存在的保护悖论。
随着经济的加速增长,[印度]森林的破坏似乎也随之加速。科学与环境中心(一个游说团体)估计,过去五年批准砍伐森林的许可数量翻了一番。仅在2009年,就有87,884公顷(占原始森林和其他森林总计6800万公顷)的森林获准砍伐。然而,尽管经济增长损害了环境,但也催生了一股反向力量:日益增长的环保意识。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经济活力威胁到一个国家自然财富的任何地方,但在印度可能尤为如此。环保意识根植于印度的政治文化之中。圣雄甘地是一位早期的环保主义者,而最初的“拥抱树木者”是印度人:20世纪80年代,*奇普科*运动(chipko movement)运用甘地的手段阻止了喜马拉雅山的森林砍伐。与此同时,印度过去20年的增长——尽管仍有数百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催生了一个庞大、具有环保意识的中产阶级。
历史学家塞缪尔·海耶斯(Samuel Hayes)在他的著作《1945年以来的环境政治史》中写道:
现代社会的环境驱动力源于人们对生活中想要的东西的新价值观。
这几十年前在工业化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就已经显现出来了。20世纪70年代初,一系列基础性的环境法律(保护空气、水源和濒危物种)的颁布,是将这些新的人类价值观在美国的法律化。然而,从那时起,环保立法的执行(和扩张)遭到了持有不同价值观的各方的强烈反对。我感兴趣的是,这些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如何将景观变成了战场。例如,我写了很多关于犹他州一个偏远地区——九英里峡谷(Nine Mile Canyon)——的故事,那里牧场、保护、石油与天然气开发以及历史遗迹保护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冲突。我还探讨了在人口更稠密地区,商业和房地产利益与生态 concerns 发生碰撞,并如何通过细致的努力才达成对不同价值观的调和。正如《经济学人》文章所说,印度正在进入类似的领域。
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调和对环境的关注与发展的愿望。
这意味着印度的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将不得不得到调和,而如果以过去三十年美国的环境政治作为参考,这个过程将不会是美好的。这也意味着,正如“突破研究所”(Breakthrough Institute)的迈克尔·申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在最近一次与科学作家约翰·霍根(John Horgan)的访谈中说的那样,人们将不得不接受一些令人不适的权衡。
我们现在是地球上占主导地位的生态力量,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更积极地管理我们的环境。这既是责任,也是机遇,它要求我们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如果我们想要更多的森林和更多的野生地方,那么我们就需要更多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以及更集约化的农业。如果我们想要减少全球变暖,那么我们就需要用清洁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包括大量的核能。如果我们想拯救亚马逊雨林这样的地方,那么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在接下来的50年里,亚马逊的很大一部分将得到开发。选择将取决于我们想要在哪里发展,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拯救什么。
我们希望就这些选择及其 underlying values 进行更广泛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