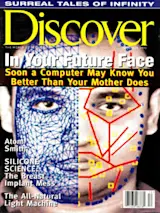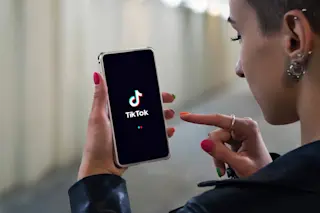我没想到最近的一个周末会有一部分时间被悬挂在一个移动的飞艇下,在时代广场上空800英尺处。通常情况下,我从不指望一个周末会有一部分时间被悬挂在一个移动的飞艇下,在时代广场上空800英尺处,所以当我发现自己正在做这件事时,请想象我的惊讶。
当然,在流行语中,悬浮在城市上空的移动气囊被称为飞艇,纽约当然也有不少。在任何一个周末,五大区的上空都被各式各样的飞艇交织着,包括固特异飞艇、富士飞艇、海洋世界飞艇和大都会人寿飞艇。诚然,在洛克希德宽体飞机和法国航空协和式飞机时代,任何能在大阅兵中舒适地跟在“麋鹿头”身后的飞机,都不会显得特别引人注目,而且当有其他旅行方式时,很少有人会选择这种笨重缓慢的飞行器。但是,飞艇是否受到了不公正的评价?这些庄严的天空巨鲸是否比我们所看到的更多?
比空气轻的飞行器的历史始于1783年,当时孟格菲兄弟——曼尼、莫伊和雅克——在法国阿诺奈发射了第一个实用的热气球。当时对热气球的需求并不大,但孟格菲兄弟显然在职业日迟到了,在莱特兄弟和史密斯兄弟抢走了飞机和润喉糖之后,他们只好将就着能得到的。尽管如此,孟格菲兄弟的成就仍然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建造了一个由布料和纸张制成的气球,高75英尺,宽49英尺,内含77,000立方英尺的热空气,通过燃烧稻草和羊毛加热。
热气球确实有缺点,其中之一就是保持空气的温度。另一种选择是用氢气而不是空气来填充飞行器的气囊。氢气是所有元素中最轻的,因此浮力最大。问题是氢气也是最不稳定元素之一,在火焰、火花甚至一句考虑不周的言论面前都会爆炸。
旁观者:嘿,那氢气是不是胖了一点什么的?
氢气:砰!
尽管如此,在蒙特哥菲尔兄弟放飞气球的同年,法国物理学家J.-A.-C.查尔斯发明了自己的一种比空气轻的飞行器,其特点是一个涂有橡胶的丝绸气囊,能够容纳22,000立方英尺的氢气。查尔斯的设计非常成功,氢气飞行器迅速取代了热气球模型,到下一个世纪中叶,这种飞行器被广泛使用,主要用于军事。在美国内战和普法战争期间,气球都被用作空中观察哨,既帮助确定了军事历史的进程,也为那个时代的报纸增添了无数令人难忘的战场语录(是的,下面有普鲁士人)。
最终,这些气球有了一个简单、拟声的名称——飞艇(blimp)——据说这是为了唤起巨型气囊被拇指敲击时发出的声音。但尽管有这个巧妙的绰号,这些飞行器仍有问题,其中最棘手的一个就是它们的尺寸。随着比空气轻的飞行器越来越受欢迎,建造者试图运载越来越大的货物和乘客。然而,负载越大,所需的氢气就越多,这就需要巨大的气囊,而19世纪可用的相对低质量的织物很难制造出这种气囊。
答案是一种全新的飞艇——硬式飞艇,它由轻质骨架和布制气球构成,无论变得多大都能保持结构完好。第一艘硬式飞艇于1900年由德国的费迪南德·冯·齐柏林伯爵发射,巧合的是,他已经以一种飞艇命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建造了几十艘这种飞艇,配备了螺旋桨,并将其飞越英吉利海峡,用于轰炸英国。当然,按照法律规定,德国工程师发明了再美味的馅饼,也必须至少尝试用它轰炸英国,即使在今天,整个英国城市也偶尔会被徕卡相机和梅赛德斯轿车的空袭击倒。
一度看来,德国齐柏林飞艇将成为行业标准。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切都改变了,德国建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硬式飞艇——804英尺长的“兴登堡”号。该飞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三年下水,部分目的是向世界展示德国的工业实力。不幸的是,当“兴登堡”号在1937年完成跨大西洋航行时,显然遭到雷击,在飞艇甚至到达新泽西州莱克赫斯特的系泊桅杆之前,它就“德国,德国,无处不在”了。
从那一刻起,氢气飞艇就开始走下坡路,设计师们迅速转向了不可燃的氦气。但对轻于空气的飞艇声誉的损害已经造成。如今,在美国只有大约十艘氦气飞艇获得了执照,其中大部分用于广告或广播。尽管濒临灭绝,但现代的轻于空气的飞艇是一种设计精巧的机器,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笨拙的祖先。
美国飞艇群中所有现代成员的共同主要特征是,它们是飞艇,而非齐柏林飞艇。俄勒冈州希尔斯伯勒的飞艇制造商美国飞艇公司总裁吉姆·蒂勒说:“硬式飞艇的刚性一直是一个缺点。当你使用硬质结构时,你必须意识到如果弯曲得足够大,它们就会断裂。这意味着你必须把它们做得非常坚固。而对于软结构,你可以弯曲它们,弯曲它们,什么都不会发生。”
为了建造如此灵活的飞艇,像蒂勒这样的当代制造商依赖于19世纪的祖先无法获得的材料。他公司制造的飞艇主体由两部分组成:内层(气囊)和外层,称为外罩。气囊实际装有氦气,由防漏聚氨酯条焊接而成。一个130英尺长,能容纳68,000立方英尺氦气的气囊仅重250磅,每周氦气泄漏量不足1%。然而,气囊虽然防漏,但不防穿刺,因此它由一个相对较重,重450磅的涤纶防撕裂织物外罩保护。虽然外罩是外部结构,但其体积实际上比它包裹的聚氨酯气球小几英寸。这种故意不合身的尺寸有助于防止破裂,确保当飞艇完全充气时,承受负荷的是更坚固的外罩,而不是更薄的气囊。
但仅仅将大码男装店的气囊塞进女士青少年服装店的外罩里,不足以让充满氦气的飞艇飞行。氦气是一种惰性元素——也就是说,它不易与其他元素发生反应——正是这种不活泼性使其不仅在飞艇中,而且在嘉年华、生日派对和白炽灯中都能安全使用。事实上,这种元素是如此良性,以至于国家氦气协会最近考虑发起一项全新的营销活动(氦气:它的原子序数拼写为F-U-N!)并请愿将该气体的元素周期表缩写从He改为Hee-Hee。但氦气不爆炸并不意味着它不膨胀;它会随着周围空气的温度和压力而剧烈变化。
蒂勒说:“如果你把一艘飞艇装满氦气,然后让它越飞越高,里面的压力会随着大气压的下降而稳步上升。最终,飞艇会爆炸。”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蒂勒的所有飞艇还在气囊内额外配备了一个冰屋状的气球,称为气囊室。气囊室充满了普通空气而非氦气,在飞艇离地时约占飞艇总气体体积的20%。当飞艇升得更高,大气变得稀薄时,空气会从气囊室排出,以防止气囊内的压力过大。当飞艇下降到较稠密的大气中时,空气会被泵回气囊室,以防止压力过低。
蒂勒向我介绍了更多关键的飞艇数据,包括他的普通飞艇的最大重量(4,400磅——包括人员)、最高速度(每小时55英里)、连接乘客吊舱的螺旋桨驱动内燃机的大小和制造商(两台68马力Limbach飞机发动机——类似于老款大众甲壳虫中使用的类型),以及用于填充大部分飞艇的氦气的天然来源(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附近一个巨大的地下矿藏——这个矿藏长期以来一直未被发现,直到眼尖的德克萨斯人注意到附近牲畜群在地面上方1,500英尺处盘旋)。
然而,再多的谈论飞艇也比不上亲身体验,所以我联系了美国飞艇公司的一位客户——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请求乘坐几个小时。让我惊讶的是,大都会人寿欣然同意了。
我应该找到大都会人寿飞艇的系泊地点位于新泽西州林登的林登机场,就20世纪的航站楼而言,它远非杜勒斯机场。主要的候机区与其说是出发休息室,不如说是郊区的一个书房,里面有娱乐室风格的镶板、娱乐室格子布面家具,以及简直是娱乐室劣质品的裱框画。据我所知,没有空管员在地板革上玩扭扭乐,我认为这是一个优点,但总的来说,这个地方并不能让人产生信心。
幸运的是,我在候机兼娱乐室的停留时间很短;我到达几分钟后,载我前往飞艇停泊区的面包车就停在了外面。那天下午,方向盘后坐着查理·格雷厄姆,他也是我空中两小时飞艇的驾驶员。当查理从航站楼短途驾车到飞艇场时,他简单介绍了飞艇业务,我所听到的让我确信我确实在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士手中。
他说道:“驾驶飞艇与其他任何飞机都不同。我们大多数人都持有飞机或直升机驾驶执照,但你仍然需要单独的FAA执照才能指挥一艘比空气轻的飞行器。目前,全世界只有大约30名活跃的飞艇飞行员,这使得我们比航天飞机飞行员还要稀有。”
当我们到达大都会人寿飞艇本应在的草地时,那里没有飞艇,没有机库,甚至连一个挥舞着带锥形头的“外星手电筒”的停机坪服务员都没有。我只看到一根30英尺高的杆子从地面升起,还有六个穿着配套马球衫的男人站在周围。查理指着这些人说:“这是我们的地勤人员。”他又指着那根杆子补充道:“这是我们的车库。晚上,我们把飞艇的头部系泊在这根桅杆上,让它就这样漂浮在那里。”
焦急地扫视天空几分钟后,我看到有人指向大致东北方向,并发现一个 unmistakable 的蓝色圆点正从地平线上方靠近。如果说没有人应该目睹制作香肠和法律的两个活动是真的,那么飞艇降落可能也应该被列入其中。它的运作方式是:
a) 穿着配套衬衫的飞艇工作人员站在那里无所事事,而飞艇变得越来越大,最终大到你可以看到飞行员今天早上刷牙是否漏掉了一个地方。
b) 飞艇降得如此之低,以至于从其机头垂下的长绳开始在地面上拖拽。
c) 飞艇工作人员注意到这一点,然后开始飞快地跑,试图抓住缆绳并把飞艇固定住。
d) 飞艇遇到上升气流,在奔跑的人抓住它之前又飘回空中。
e) 反复进行。
查理告诉我,风是飞艇着陆的一个重要变量。理想情况是,在最后下降时恰好遇到逆风。这会减慢你的速度,并降低你的高度和地速。有云层覆盖也有帮助,因为明亮的阳光会加热氦气并增加其浮力。
又经过了两三次接近后,恰好适宜的条件突然出现,飞行员得以将飞艇降到足够低,让地勤人员抓住缆绳,将其固定到位。此后仅片刻,另一位飞行员便跳下,查理和我登上飞艇,然后起飞。
乘坐比空气轻的飞行器离地,出乎意料地忙碌。我不知道自己具体想象了什么——或许是绝对寂静、风力辅助的上升,只被IMAX旁白的声音打断,说着类似“自从第一个人类观察到第一只鸟在稀树草原上扑腾,人类就一直梦想着自由飞翔”的话。但实际情况完全不是那样。吊舱的敞开窗外,两台Limbach发动机呜呜作响,隆隆运转。在我前方,飞艇的机头上下晃动,左右摇摆不定,悬垂的绳索懒散地前后摇摆。我左边的查理操作着油门、方向舵踏板和气囊绳,做出荒谬的舞蹈动作,一半像查克·耶格尔,一半像威尔伯·莱特,一半像威利·旺卡。然而,很快,飞行变得平稳,当我们滑翔在新泽西海岸上方约600英尺处时,查理开始了我们的旅程。
“我们将从曼哈顿西南部接近,”他对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喊道,“所以你看到的第一个地标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当然,曼哈顿西南部就是自由女神像,当我望向飞艇的机头之外时,它确实出现在正前方,并且越来越近。从地面到火炬,自由女神像高302英尺。根据查理的高度计,我们距离海港不到500英尺,因此片刻之间,我们离纪念碑顶部已经足够近,如果自由女神没有戴帽子,我就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那绿色的头发是否有黑色的发根了。
我们懒洋洋地绕着雕像盘旋——近到足以引起基座周围人们的明显挥手,远到足以在自由女神决定放下火炬拿起一份卷起来的报纸时安全脱身——然后便驶向曼哈顿市区。我们现在正接近的主岛部分最显著的特征是几百英尺前方高耸的世界贸易中心双塔。我又看了一眼高度计,我们大约在800英尺高;我知道,双塔高过1300英尺。现在,我并不自诩为导航高手,但你也不必是庞塞·德莱昂才能知道,当时选择左、右或上都是不错的选择。幸运的是,查理选择了左边,我们绕过西北塔,开始滑翔在曼哈顿本身的密林上空。
从街面看,纽约市可能有点挑战。但从130英尺长的氦气袋提供的视角来看——尽管我尽力保持城市的玩世不恭——却变得几乎田园诗般。十四街以北的联合广场园林景观,缩小成一片点缀着绿色的陶土潘帕草原。二十三街钟楼近在咫尺,其巨大的西面钟面上的时间清晰可辨,却又远在下方,使其更像是蒂梅克斯女士表。时代广场,名义上的世界十字路口,今天看起来几乎不像是街区十字路口。岛屿北部末端的乔治华盛顿大桥,看起来几乎不够宏伟,不配以马丁·范布伦命名。最后,便是沿着哈德逊河和进入新泽西州的漫长返程。
当我们最终抵达机场时,查理令人印象深刻地在第一次尝试时就将飞艇成功降落。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并没有为此邀功。他在地勤人员奋力抓住缆绳时操作着控制装置,然后点头道别,我跳下飞艇。飞艇随后不声不响地飞回蓝天,查理则飘走,继续几个小时的空中广告工作,展示大都会人寿的色彩。就空中旅行而言,我这两个比空气轻的飞行小时缺乏很多——没有目的,没有目的地,当然也没有机上零食服务。但即使我在纽约再住50年,这几乎肯定是我唯一一次在如此远的市区出行,并且确信我能顺利通过所有的红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