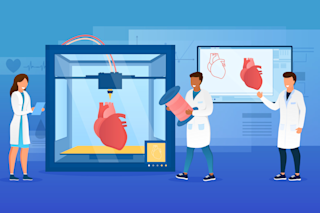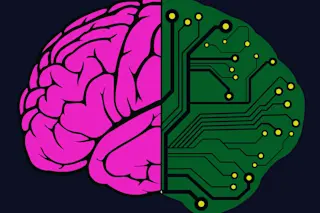斯图加特的天色仍是一片漆黑,但汉斯-马丁·施莱尔会展中心外已经排起了长队,等待上午6点开放由德国解剖学家Gunther von Hagens创作的、令人震惊且备受争议的“人体世界”展览。一本宣传册将“人体世界”描述为“三维的医学字典”,无疑有少数参观者是为了精确地了解这些而来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观众是为了亲眼目睹这个巡回展览的宣传语所承诺的壮观景象:“真实人体解剖展”。
真实的人体。Von Hagens发明了一种化学工艺,有效地将尸体的组织和器官转化为逼真、可塑的塑料,然后他 painstaking 地进行解剖并展出。他的作品并非平躺在台板上的苍白躯壳。它们是粉红色的肉体,被剥开、拉开,并以动态甚至夸张的姿势展示。一个标有“肌肉男”的人物站立着,赤裸着全身,骄傲地从一只手中垂下他完整的皮肤斗篷。“躺卧的孕妇”正如其名:一个维纳斯般的形象侧卧着,凝视着观众,随意地展示着她敞开的腹部,里面露出了一个发育完全的胎儿。
这不是你奶奶的葬礼。Von Hagens颠覆了人体形态,同时也颠覆了关于生者与死者之间恰当关系的几乎所有公认的惯例。对他的批评者来说,结果是一种亵渎,甚至是罪恶:人类遗体应得到比“人体世界”所表现出的撑杆跳、踢球、打篮球等姿势所赋予的尊重要多得多。Von Hagens已经抵挡住了天主教抗议者和盗墓指控。在伦敦,“人体世界”展览于2002年至2003年展出11个月,当时的报纸头条从谨慎的慈善(“过分的血腥——还是有史以来最棒的艺术展?”)到公开的蔑视(“死亡博士和他的旅行怪胎秀”)。他的许多同行也尤其持怀疑态度。费城医师学院19世纪病理学博物馆——穆特博物馆的馆长Gretchen Worden说:“这是‘热狗解剖学’,他在玩弄尸体。”
Von Hagens则认为,该展览不仅具有教育意义,而且是美丽的:它将人类尸体从《沉默的羔羊》和《犯罪现场调查》等法医剧的低俗窥探中解救出来,恢复了其前维多利亚时代作为谦卑和惊奇之源的地位。“电影业已经靠将解剖学犯罪化赚了很多钱,”他说,“我正试图创造另一种美学。”
von Hagens越是谈论,越是清楚地表明,“人体世界”展览的议程既不是严格的科学也不是艺术,而是——或者再加上——政治。作为一名在极权主义东德生活了25年的居民,von Hagens曾因试图叛逃而入狱两年。现在,他与权威有账要算——那些声称某些教育展览不适合公众观看的政客,那些声称对人体解剖有独家观看权力的科学家——总之,任何坚持“最好不要看、不要问、不要自己判断”的人。“人体世界”是对故意视而不见者的挑衅。“这是再民主化,”von Hagens说,“普通人也应该有同样的观看权。”这一理念是他于2002年11月在伦敦现场进行尸检的决定性因素——这一行为在英国170年来一直被视为非法。他仍在等待苏格兰场的起诉决定。
也许是有意为之,“人体世界”周围的争议反而增加了它的吸引力。自1996年该巡回展览首次亮相以来,欧洲和亚洲已有超过1300万人付费观看。为了应对斯图加特的人潮——展览只持续九天——展会一直从早上6点开放到午夜。对von Hagens来说,人群是他对各种批评者最有力的回应:如果他所展示的东西如此不雅,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排队观看?
“不应该隐藏任何东西,”von Hagens说。现在是早上9点刚过,斯图加特展览厅已经挤满了1000人的容量——一群活生生的人伸长脖子,审视着他们裸露、不动的同类。Von Hagens本人身材高瘦,和蔼但脸色苍白——一个穿着白色袜子和勃肯鞋的快乐殡仪员。如果不是他一直戴着的软呢帽,他会在人群中默默无闻——在所有照片中、接受采访时、在跨越世界各个角落的过夜航班上。为了避开人群,他带我们来到一个被隔离开的房间的尽头。然而,几分钟之内,一群签名索求者聚集在隔离带外,等待着戴帽子的男人。
Von Hagens发明塑化技术是为了对抗解剖学经久不衰的敌人:时间本身。尸体以惊人的速度腐烂;解剖学家只能在它们褪色之前研究它们的精细结构,并妥善保存它们。作为20世纪70年代海德堡的一名解剖学助手,von Hagens痴迷于嵌入有机玻璃的标本。他想,这很好,但如果塑料能在标本内部呢?他开始尝试一种方法,在真空压力下,去除标本中的原始液体,并有效地用塑料聚合物取代它们。他成功的第一个标本——一个缩小成黑色肿块的肾脏——激励了他继续前进。他将自己的技术命名为“易腐生物标本的聚合物浸渍”,犹豫了一下,最终定名为“塑化”。
在改进并获得他的技术专利后,von Hagens带着塑化技术四处展示其奇迹,与同行解剖学家交流。他很快发现,清洁工和他的同事一样着迷。他扩大了范围,保存了完整的尸体,用切肉机切割并剥开它们。他为公众创造了一个巡回展;“人体世界”就此诞生。为了供应展品,von Hagens现在在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两个车间雇佣了200多名技术娴熟的解剖学家。Von Hagens强调,“人体世界”中出现的身体和身体部位完全来自无偿捐献者,他们是普通人,专门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他。展览中有一个展区专门解释捐赠过程,甚至允许新捐赠者注册——他们也蜂拥而至。每年有数百名捐赠者将他们死后的身体捐献给von Hagens,有些是出于纯粹的教育利他主义,有些是为了让他们的生命获得持久的意义,还有些是为了获得他们15分钟的成名机会,即使只是因为他们被分离的肝脏。
Von Hagens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将“人体世界”带到美国——只要他能找到一个足够勇敢的博物馆、画廊或废弃的仓库来接待他。“我知道它会大受欢迎,”他说,“美国人非常注重身体。但它也是一个充满狂热者的国家。我将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地点把它带给人民。”
作为一个展览,“人体世界”的布局有点像汽车展。它从最基本的元素——骨骼——开始,那是我们内心深处所谓的标志性的白色骨架。接着是二十几个全身模型,每一个都比前一个更“内翻”:一个大步流星的骨架——“跑步者”——肌肉和肌腱像被风吹动的丝带一样从骨头上向后飘散;炫耀皮肤的“肌肉男”;“守门员”,一个肌肉发达(且无皮肤)的身体,水平悬在空中,一只手够着一个足球,另一只手拿着它全部的内脏器官。
在这些展台之间,陈列在玻璃柜里的是器官:心脏、大脑、肝脏、肠道、生殖器。想知道真正的子宫是什么样的吗?或者23英尺长的肠子是如何装进人类腹腔的?看了这个展览你就知道了。“人体世界”并没有描绘完美。参观者可以看到增大的脾脏、被尼古丁熏黑的肺、被阿尔茨海默病摧毁的大脑皮层。没有结石被放过。总体效果是通过减法展现健康,人体通过其无数的失败仍然显现出强健。参观者很快就会明白,不存在一个通用的“人体模型”,而是“人体主题”的无数变体。
总体的效果是引人入胜,却又不知为何不令人作呕。塑化工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节保存了标本——肌肉可以分辨到每一根纤维——但又具有足够的塑料相似性,以至于参观者不怕仔细地长时间观看。为了缓解观众的不适,von Hagens一丝不苟地剥离了每个标本之前主人的身份。面部已被移除或被充分解构,以至于无法辨认。(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塑化工艺保留了毛发、睫毛,甚至纹身,提醒人们这些人物仍然是独立的,尽管是匿名的。)
匿名性既是法律上的必要,也是一种美学选择。一个有身份的尸体就是一具尸体,而一屋子尸体将构成一个非法墓地。Von Hagens认为,他的标本与木乃伊和教室里的骨架属于同一认识论范畴。“塑化物不是个体记忆的对象,”他说,“它们是已故人类的新呈现。”
他还小心翼翼地规避德国宪法第一条,该条明确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侵犯”,这个短语在德国法院被用来反对从色情到矮人投掷等一切事物。德国官员允许“人体世界”在斯图加特开业,条件是von Hagens同意移除某些有损尊严的元素——主要是“篮球运动员”和“守门员”分别持有的篮球和足球。(人物本身被允许保留。)
这对一些批评von Hagens的人来说还不够。“这是令人惊叹的东西,”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国家医学图书馆的策展人和历史学家Michael Sappol说,“他是一位伟大的解剖学家,技术精湛。但大多数解剖学家都对他感到恐慌。”在19世纪之前,解剖插图很有趣;一个人物可能会向观众眨眼,或者快乐地在页面上行走。
然而,随着解剖学成为一门专业,这种视觉情绪被压制了——部分是为了向公众保证解剖学家是客观的科学家,而不是低俗的、盗墓的窥淫癖者。Sappol说,对他的许多当代同事来说,von Hagens的冒犯是双重的:他通过向公众展示一切来打破解剖学家的“知识崇拜”,并且他重新引入了情感体验。“我们被隔绝了对死亡和尸体的接触,”Sappol说,“所以这是令人兴奋的,也是有点淘气的。”
Von Hagens反驳说,“人体世界”的主要目的是教育。事实上,展览附带了大量枯燥乏味的医学信息。每一个大小标本都配有标牌、说明或注解;参观者的头脑很快就会充斥着关于腹股沟韧带和脂肪囊的描述。该展览自称为“三维的《格氏解剖学》”的自我宣传并不夸张。音频导览由von Hagens本人用单调的声音朗读,枯燥得足以让死者安息。
如果展出的标本吸引了你的眼球——如果它们举着皮肤供你检查,或者它们向前倾斜,眨着一只眼睛,挑战观众不得不看——那么,这有什么问题呢?Von Hagens打了个比方,就像一位历史老师:你更愿意听一个活泼的年轻老师讲课,还是一个唠叨、浑身是味儿的懒汉?“我们展示东西时会盛装打扮,”他争辩道,“所以这些标本在解剖学上被‘打扮’了。”
这听起来可能像是马戏团广告的自高Rationalization。然而,在“人体世界”里与人群待上一两个小时,似乎证实了他的观点。人们可能会期待一种怪胎秀的氛围;相反,标本周围的气氛是深思熟虑和沉静的。在它们之间漫步是一种亲密而又奇怪的动人的体验,就像走进空无一人的房屋,或者窥视刚去世者的衣橱。人群鸦雀无声,进行着只能被描述为集体内省的活动:那个身体是我,是你——只不过一个是空的,而奇迹般地,这个仍然有人。
Von Hagens施展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戏法。通过压倒性的医学细节,他设法将注意力集中在“人体世界”中无处不在却从未在任何说明中提及的元素上:精神,灵魂,每一个人体的微妙而持久的力量,却在它们缺席时才更为明显。“我希望缩小死亡与生命之间的差距,”von Hagens说。他以一种任何语言或图片都无法传达,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传达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