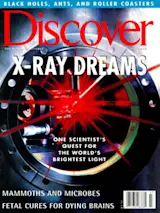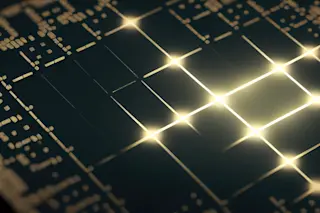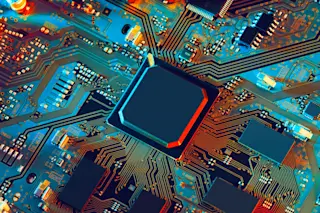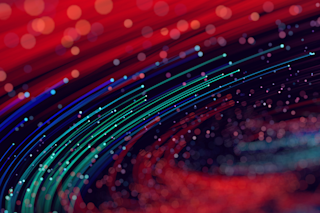氙气爆发出X射线的那天,查尔斯·罗兹错过了所有精彩。事实上,他差点就叫停了那场实验。罗兹是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原子、分子与辐射物理实验室的主任,他当时预料会是哑火,而不是烟花。是阿蒙·麦克弗森(Armon McPherson)预感到氙气可能会有异常表现。麦克弗森实际上负责着大部分实验的运行,他想继续用一万亿瓦的激光器轰击氙气。罗兹则认为X射线响应会很微弱,想等到有了更灵敏的探测器再来捕捉它。“查理告诉我,我会是白费时间,”麦克弗森回忆道。罗兹回家后,麦克弗森自己动手引爆了氙气。
他和罗兹都将在未来的许多年里生活在这次实验的余波中,而他们对此欣喜不已。罗兹现在表示,麦克弗森释放出的X射线洪流可能会催生出有史以来在任何波长下产生的最亮光源——一种新型X射线激光器。这种光用于显微镜,将为生物学家提供一种全新的观察方式。传统显微镜无法看到比可见光波长更小的物体,而可见光的波长比X射线长一千倍。电子显微镜在分辨细节的潜力上接近X射线,但它们只能观察用金属染料染色并固定在载玻片上的死亡组织。而有了X射线激光显微镜,生物学家就能穿透活细胞。他们可以拍摄细胞质中悬浮结构的全息三维快照,细节分辨率可达十亿分之一米。他们甚至可能放大到分子尺度,挑选出某段DNA,并找出它如何调控生命的化学反应。“你最初不会担心要看什么,”罗兹说,“你只管去看,就会看到新的东西。”
生物学只是应用之一。X射线激光器还可能蚀刻出比当今小一千倍的电子电路,将袖珍计算器变成超级计算机。作为通信载体,一束X射线所能容纳的数据量,是传统激光束在光纤中传输的一千倍。由于每个X射线光子携带的能量是可见光光子的一千倍,如果将X射线光子用于目前焊接、切割和钻孔的激光束中,它们将成为强大而具有穿透力的武器。
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的物理学家杰克·戴维斯(Jack Davis)说,当实用的X射线激光器上市时,“它真的将彻底改变一切”。戴维斯说的是“当”,而不是“如果”。他心中唯一的问题是谁会率先实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和日本的团队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各种方案。
X射线激光器已经存在,但尚不实用。它们有两种型号。第一种在其鼎盛时期是“星球大战”计划的关键武器。1982年,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名誉主任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提议在太空中引爆原子弹,为轨道上的X射线激光器提供能量。它们会“砰——滋啦,砰——滋啦,砰——滋啦……”地工作。它们会击穿来袭的核弹头,然后自身在引爆核弹的热量中蒸发。研究人员确实在20世纪80年代的地下核试验中启动了由核弹驱动的X射线激光器。该项目在利弗莫尔的最后一任经理斯蒂芬·利比(Stephen Libby)只说,这些试验产生了“一束强劲的X射线束,这就是我能告诉你的全部”。这些激光器是否仍然存在,无人透露。大概可以安全地假设它们是不可重复使用的。
1984年,利弗莫尔的另一个由丹尼斯·马修斯(Dennis Matthews)领导的团队展示了一种更小型的实验室X射线激光器。“Zappa Jr.”(小扎帕)虽然不是以热核爆炸启动,但它需要世界上最大的非X射线激光器作为“火花塞”,而这个激光器占据了整栋建筑。今天利弗莫尔的X射线激光器仍是这种老式型号。虽然可重复使用,但它太大太贵,远称不上实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几个研究小组已经建造了相当小的桌面设备,其工作波长是X射线词典定义波长的两倍、三倍甚至四倍。这些“软”X射线激光器可能很实用,但它们只是冒牌货——根本无法胜任真正X射线激光器能处理的工作。
现在,罗兹相信他即将发明一种能够产生极短波长——即“硬”X射线的X射线激光器,而且其所需功率远低于“小扎帕”。他说,它的工作方式与以往的方法有根本不同,需要一种新的物理学来解释。罗兹全身心投入新技术,正与竞争对手拉开距离——或许是他们正在远离他。尽管他提出了这些主张,罗兹在X射线激光器研究圈里绝对处于边缘位置。他究竟是领先还是落后,取决于你问谁。利弗莫尔的物理学家乔·尼尔森(Joe Nilsen)说:“查尔斯·罗兹根本不可能在X射线激光器的门槛上。”而戴维斯则认为罗兹是领头羊。“他是个引领潮流的人,”他说,“他在挑战极限。他冒着极高的风险。他是个罕见的、知道该做什么的人。”
罗兹本人不负其英雄般的评价。他有领袖魅力;他的员工崇拜他。当他压低声音时,他像约翰·韦恩一样隆隆作响,潜台词是“说重点”。56岁的他看起来敏捷、精干、充满活力,而且无所畏惧。他曾追赶过一个在他芝加哥家附近抢劫一位老妇人的劫匪。你会感觉到他会以同样的决心追求X射线激光器。“我的对手们,”他说,“希望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弱的对手。”
罗兹这种“拔枪就射”的风格不仅仅是生动有趣,它表达了他对科学研究的态度。他似乎认为大多数科学家把时间浪费在琐碎的事实上。“如果你问自己谁能在世界上取得成功,”他说,“是那些仅凭百分之几的信息就能做出正确决定的人。”他多1%或少1%都不在乎——在这方面他不挑剔——但他对如何存储信息却非常讲究。他的桌子上没有嗡嗡作响、占用空间的电脑。罗兹自豪地宣称自己是电脑盲,一个老派的纸笔物理学家。他所有的工作都以老式的纸质副本存在,塞在一排排金属文件柜里。
氙气爆发的那天,罗兹表现得异乎寻常地谨慎。十多年来,他一直在摸索着制造X射线激光器,凭直觉行事,同等程度地依赖实验、严谨的分析和运气,而理论几乎是事后才考虑的。他的目标很简单:在制造X射线激光器之前,他首先需要找到一种材料,在被传统激光束轰击时能发射出大量的X射线。他对氙气以及他测试过的其他材料的实验,一直没有取得突破,直到有一天罗兹凭直觉做出了一个飞跃。为什么不先让氙气凝结成微小的液滴——几十个原子松散地聚集在一起的团簇——然后再用激光轰击它们呢?他想,紧密排列的原子或许能以某种方式相互激发,从而发出比单独原子更多的光——包括X射线和可见光。
但即便如此,他对这个想法也并未抱太大希望。根据主流物理学,氙团簇发射的X射线不应比单个氙原子多。支撑这一结论的理论被收录在厚厚的参考书中,这些数据是经过几十年研究积累起来的。“这现在已经很清楚了,”罗兹咆哮道。尽管如此,他认为这个理论可能是错的。罗兹怀疑他和麦克弗森确实能从团簇中获得更多的X射线——但只是稍微多一点,不足以被他们粗糙的设备检测到。他认为在改进辐射测量技术之前进行实验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说按部就班对罗兹来说意义不大,那么对麦克弗森来说就更无所谓了。十年前,他以一年的聘期来到罗兹的实验室,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罗兹很快就看出麦克弗森有让事情顺利运作的本事。即使在业余时间,他也通过具有挑战性的爱好来放松自己。他曾一度切割宝石。现在他种植屡获殊荣的兰花。“别人很难种活的种子,”罗兹说,“他能让发芽率接近100%。”和罗兹一样,麦克弗森也凭直觉做决定。“我很多时候是凭直觉做事,”他耸耸肩承认道,“有时候很难为我在实验室里做的事情给出科学论证。”
所以,在氙气爆发的那天早上,麦克弗森开始用激光轰击氙团簇,在视频监视器上,他看到了快到几乎无法捕捉的闪光。氙气正在吸收激光脉冲的能量,并将其中的一部分反射回来。麦克弗森和罗兹都预料到了这一点,但麦克弗森认为氙气产生的光比应有的多得多——而且他预感它可能也在发射大量的X射线。“我告诉查理,这东西像固体一样辐射,”麦克弗森回忆说。当被激光激发时,固体的亮度是气体的上千倍。麦克弗森建议尝试用对X射线敏感的胶片捕捉这些闪光。罗兹从他身后盯着视频监视器,争辩说他得整晚整天不停地拍摄,才能捕捉到一丝X射线的痕迹。“你什么也看不到,”罗兹厉声说。
麦克弗森不顾罗兹的怀疑,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测试氙气。那天晚上,他拨动开关,用一束激光击中氙气,再拨动开关,击中更多的氙气。半小时后,他估计胶片已经曝光得差不多了;他冲洗了胶片,把它挂起来晾干。
第二天,罗兹发现他的同事异常兴奋。罗兹挠了挠头。他猜想,麦克弗森作为测量天才,可能又找到了什么实验室技巧,在胶片上勉强弄出几道微弱的X射线痕迹。他过去也施展过类似的魔法。但当罗兹看到X射线光谱时,用麦克弗森的话说,他“惊呆了”。根据他们俩所知的所有物理学知识,胶片应该几乎是完全透明的,但现在麦克弗森手里拿着的却是一张因暴露于X射线而变黑的胶片。“显然,”罗兹说,“这些蒸汽中漂浮的氙团簇辐射的强度比它们应有的要强得多。”它们像X射线超新星一样爆发了。“这意味着,”罗兹说,“这里有根本性的新东西。”
好吧,新的物理学——罗兹先放下了。也许有一天他会试着弄清楚背后的理论。那一刻,他专注于一个狭窄的目标:他要建造一台破纪录的X射线激光器。自1980年以来,他一直在为此努力。现在,在1993年6月,他所需要的X射线终于壮观地出现了。
罗兹很快就忙于准备论文和发表演讲。欧洲的几个小组已经在探测氙、氩和其他稀有气体的团簇,那里的研究人员对罗兹的结果感到兴奋。但他在利弗莫尔的竞争对手却不那么热情,甚至可以说是冷淡。丹尼斯·马修斯(Dennis Matthews)仍然是那里的X射线激光器项目负责人,他第一次得知这些发现是在1994年8月25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文章称罗兹发现了一种产生“强度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X射线激光脉冲的方法。对马修斯来说,这毫无道理。后来,他说,“我收到了查理·罗兹的一份手稿,说他们在研究氙团簇。那是一篇不错的科学论文,展示了一些很好的X射线发射,但没有提到激光发射。”
马修斯说得有道理。罗兹确实找到了一种产生强烈X射线爆发的方法,但这些X射线是向四面八方发射的。激光不仅仅要强度高,它还必须是相干的,即波长单一,并且聚焦成一束几乎不发散的光束。要制造一台真正的激光器,他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放大他的X射线,并让它们以相干光束的形式发光——这绝非易事。否则,他找到的不过是一个非常亮的闪光灯泡。
没有人比丹尼斯·马修斯更清楚罗兹面临的问题。马修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外表像个政治家——你可以把他的脸印在硬币上——他是实验室X射线激光器之父,是那种你现在就能实际使用的激光器。“我们的X射线激光器一直都非常传统,”他说,“它们的操作方式和光学激光器一样,只是处于X射线波长范围内。”
传统的激光器制造方法有一些明显的优势——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物理学家们至今已经有超过30年的相关经验,并且不需要新的物理学来解释它们的工作原理。魔法始于受激原子。如果你用一束能量脉冲击中一个原子,一个或多个电子很可能会吸收部分能量并跃迁到离原子核更远的更高轨道或壳层。你向一个原子注入的能量越多,它的电子跃迁得就越高。当这些受激电子在原子核正电荷的吸引下回落到较低壳层时,它们会以无线电波、光波或像X射线这样更短的波的形式释放能量,具体取决于它们落到哪里。如果你想让电子吐出X射线,你需要确保它们落入最内层的壳层之一。
一种方法——通常的方法,马修斯的方法——是为电子落入内层壳层创造条件,即不加选择地清空原子轨道,移除大量电子。这会产生一个带很强正电荷的离子。如果你像马修斯那样通过加热来电离原子,外层电子会先离开,内层电子最后离开。然后原子核会把它们拉回来。缺点是你需要巨大的热量——大约一千万度的恒星温度——才能蒸发掉足够多的电子,以触及产生X射线的内层。为此,你需要一颗原子弹或一台极其强大的激光器。
一旦你设法产生足够的能量来剥离原子的电子,你仍然需要放大X射线。这里的技巧是让原子在能量中浸泡足够长的时间,让自然规律发挥作用。当一个原子发射一个X射线波长的光子时,它很有可能会撞击另一个原子,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量子力学定律规定,它会刺激一个电子衰变到同一个内层壳层。当空位被填补时,另一个X射线光子射出,将这个过程向前推进。这种受激辐射的光,其亮度以比任何竞争波长都快的速度加倍再加倍,很快就淹没了介质,变得比所有其他光强一千、一百万、十亿倍。
然而,仅仅让X射线光子四处乱飞是不够的。你必须以一种让它们最终都朝同一方向传播的方式来放大它们。对于长波长激光器,你在激发原子的腔体两端各放一面镜子,使光束来回反射,并在过程中放大。原子向其他方向发射的光会直接逸出,而困在镜子之间的光束则会越来越亮。这一切发生得非常快。在几十亿分之一秒左右的时间内,你会得到一束穿过其中一面镜子(你特意做成了半透明的)的窄而亮的光束。瞧,你就有了一台激光器。
对于X射线,这个方案的最后一步很快就变得棘手——在万亿分之一秒(皮秒)内。这是因为,在不到那么长的时间里,大多数被剥离到足以产生X射线的原子都会衰变:它们的电子被从束缚它们靠近原子核的强大键中撕裂出来,自发地回落到较低的壳层。在万亿分之一秒内,光行进不到一毫米。从镜子返回的光束会发现它前面的大多数原子已经衰变,它们的电子已经回到了常规轨道,不再可能发射X射线。为了持续放大光束,你需要保持前方的原子处于受激状态。所以你需要不断地向原子注入能量,让它们在一千万度的温度下持续“爆裂”。要缩短X射线激光器的波长,你需要更大量的能量——大得多。使用传统技术,要将波长从10纳米(十亿分之十米)降到1纳米,你需要以快10000倍的速度输送1000倍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波长超过20纳米的“软”X射线“冒牌货”根本算不上X射线激光器。
如果你在设计X射线激光器,很容易会陷入一种奇怪的心态。突然之间,光速似乎变慢了。你数着皮秒,小心翼翼地培育着你的X射线束,等待它变得足够亮,然后你才能关掉电源——一个十亿瓦特,上下差几个零。你的X射线能到达镜子就已经很幸运了。或者也许不那么幸运,因为那样你就需要发明一种新的镜子。你想要X射线,记得吗,因为它们能穿透。现在你却要求它们反射。连麻烦似乎都在放大。
马修斯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些问题,因为他在利弗莫尔的团队已经解决了每一个问题。“事实上,”马修斯说,“我们已经制造了镜子,并且确实让X射线在放大器中来回反射了。”不幸的是,它们持续不了多久。马修斯用交替的硅和钼层制造他的镜子,每一层的厚度都是所需X射线波长的一半。它们能短暂地反射X射线,但在激光束产生的强烈热量下爆炸的金属箔片散落的碎片摧毁它们之前,这个过程就结束了。
产生那束光束的激光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激光器,它的名字叫“新星”(Nova)。它占据了整栋建筑,坐落在一个占地600英亩的园区中心,园区内点缀着棕榈树,道路纵横交错,弯曲的自行车道穿插其间。“新星”大部分时间都在吸收电力,将能量储存在巨大的电容器组中。大约每小时一次,它会启动。在十亿分之一秒内,它以一束绿光脉冲的形式发射出与整个美国在那一瞬间消耗的能量一样多的能量(10万焦耳)。“新星”可以将能量集中在一束光束中,也可以将其分成多达十束,这些光束通过白色管道冲向散布在建筑内衣柜大小的钢制靶室。每次发射后,研究人员收集他们的靶标,分析数据,调整计算机模型,并规划新的实验,排队等待下一次的能量冲击。
X射线靶标是安装好的方形金属箔,一两英尺宽,由银、金和许多其他金属制成。当“新星”的激光脉冲击中其中一个时,金属箔会爆发出X射线。实际上,不是一束而是两束激光束击中靶标,它们被聚焦成一条线而不是一个点。在十亿分之一秒内,“新星”持续加热,使金属箔上那条线上的原子保持受激状态。每个原子向四面八方发射X射线,但只有那些沿着被“新星”光束照射的线传播的X射线才能成功找到准备好发射额外X射线的原子。随着金属箔爆炸和“新星”脉冲消退,两束X射线激光束向相反方向射出。
早在1984年,马修斯的激光器产生的是软X射线,波长约为20纳米。1987年,他的团队使用硬的4.5纳米X射线制作了第一张X射线激光全息图。(一旦有了X射线,成像技术与光学显微镜大同小异:一个球面镜聚焦光线,光线穿过样本,然后落在光敏探测器上;全息图需要增加一束参考光束。)马修斯的X射线图像揭示了小至50纳米的细节,这比分子尺寸大得多,但分辨率是光学显微镜的十倍。这些X射线对罗兹来说还不够好,他想用极短的X射线——大约十分之一纳米——来解析单个分子。然而,马修斯认为他那更普通的X射线足以观察科学家想看的大多数东西。他认为,波长再短,X射线可能会穿透得太好。毕竟,骨骼在X光片中显现,只是因为部分X射线被阻挡了。“我们还没搞清楚,”马修斯说,“用非常短波长的X射线能做什么。”
无论如何,利弗莫尔的物理学家们近期内不太可能产生这样的X射线。理论上,马修斯认为使用一个非常大的电源,有可能获得短至1纳米的X射线波长。“比那更短,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但利弗莫尔的科学家们承认一个困境:他们用来电离原子所需的激光器——也就是泵浦激光器——太大太贵了。至今还没有其他人能够负担得起建造类似的设备。如果X射线激光器无法经济地复制,科学家们将不得不继续前往利弗莫尔朝圣,并且还要等待数月才能预约到时间。
作为替代方案,马修斯正试图让至少一部分X射线激光发射脱离“新星”。他正在筹集资金,设计和建造一台商用X射线激光器,小到可以放进一个房间。他说,现有的泵浦激光器可能足以制造一台功率适中、在实验室中有用的X射线激光器。
马修斯设想的房间大小的激光器听起来很像罗兹和麦克弗森正在追求的原型。然而,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罗兹找到了一种比利用利弗莫尔的蛮力方法更高效地产生X射线的方法。他不仅能产生波长比利弗莫尔最好的短十倍以上的X射线,而且他能用马修斯预见的任何能量的千分之一来触发它们。事实上,罗兹觉得计算他的X射线激光器将比任何传统技术可能实现的效率高多少,即便用纸笔计算,也是荒谬的。当然,前提是他能完成这项工作。
当罗兹在他的实验室里,在理论和实验之间来回穿梭时——距离不远——他经过一台宏伟的设备。就像“新星”主导利弗莫尔一样,这台仪器主导着他所做的一切。它不是激光器,甚至不大,但它解释了他所走的道路,以及为什么他如此渴望发明新技术。它是一台X射线显微镜。它可以制作三维全息图像,存储在计算机中并在屏幕上查看。他只需要一台实用的、短波长的X射线激光器就可以开始使用它。
罗兹说,发生的事情是“车跑到了马的前面”。而且是遥遥领先。在20世纪80年代初,罗兹成立了一家公司来开发这种显微镜,并申请了专利,该专利于1990年获得批准。要让它工作,他只需要一束能够深入穿透、捕捉明亮、详细图像,并在分子因热量开始摆动之前离开的X射线脉冲。设想是这样的:一束X射线脉冲会在一个极短的闪光中呼啸穿过一个细胞,持续时间不到一万亿分之一秒。在该脉冲结束时,它接触到的分子已经移动得足够快,足以使它们的图像模糊。X射线会击中一个探测器;生命中荡漾的活体化学图像最终会显示在屏幕上。一个永恒的瞬间过去。在被击中后大约十万亿分之一秒,细胞会蒸发。
尽管利弗莫尔在1987年已经发射了4.5纳米的X射线激光束,但它们对罗兹毫无用处。波长太长,无法分辨分子,而且相对昏暗的脉冲持续时间太长,以至于在拍照之前,它就会把罗兹想要拍摄的细胞和其他活体物质烤焦。罗兹需要更快、更亮的爆发。“很明显,”他说,“我们必须发明一些新东西。”为了产生这样的X射线脉冲,他估计需要找到一种方法,用大约每个原子一瓦的功率来激发某种材料。这能量可不小。除非他能找到某种杠杆作用的方法,否则这将需要一台大得不可思议的“新星”式泵浦激光器。他不能只是猛击电子;他必须控制它们,编排它们。“极高的功率,极精细的控制——一个不太可能的组合。你需要超人的力量和巴里什尼科夫的优雅,”罗兹说,“而这并不容易做到。”
超人先来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种名为“普罗米修斯”的新型短脉冲紫外激光器为罗兹提供了他所需的泵浦功率。
“普罗米修斯”在正常运行时,大约每秒发射一次一万亿瓦的光脉冲。要维持这个功率水平是困难的。事实上,每个脉冲只持续大约一万亿分之一秒。所以每个脉冲携带的总能量——一万亿除以一万亿——大约是一焦耳,这并不多。一个普通的100瓦灯泡每百分之一秒辐射一焦耳。普罗米修斯和灯泡的区别在于:灯泡散播能量;激光压缩能量。如果你收集一焦耳的灯泡辐射——在百分之一秒后,它是一个直径相当于北美大陆的光球——并将其压缩到小于一立方毫米,你就得到了普罗米修斯的一束脉冲。当其中一束脉冲击中一个目标时,它携带的能量聚焦到一个点上,相当于每个原子大约一瓦。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罗兹说。另一种获得每个原子一瓦功率的方法是将整个美国一年消耗的电力通过一个灯泡的灯丝。任何被如此强大的能量浪涌击中的东西——钨、氙,任何东西——都会立即像恒星中的物质一样发光。
与基本上是长时间缓慢“煮沸”电子的“新星”不同,“普罗米修斯”施加的是短暂而有力的冲击。有了他的新激光器,罗兹第一次能够对原子中的电子施加比原子核所能抵抗的更大的力。“电子环顾四周,”罗兹说,“他看到了什么?他突然看到这个巨大的大猩猩,它比他看到的任何其他东西都强大得多。”即便如此,根据标准理论,这些数字也算不了什么。普罗米修斯的一束强大但微小的脉冲,由于其微小,只能击中蒸汽中相对较少的原子;由于其强大,它会触发一些X射线。“整个诀窍,”罗兹说,“是使用柔术。”
罗兹用“柔术物理学”来描述当他用“普罗米修斯”的脉冲击中他钟爱的氙团簇,而团簇的回应是像小超新星一样发射出X射线时发生的事情。像往常一样,是电子在起作用。
所有能形成团簇的原子所属的元素在化学上都很“无聊”。化学家称它们为稀有气体,因为它们大多是惰性的,意味着它们排斥其他原子,不会结合形成分子。即使你将稀有气体中的原子冷凝,迫使它们靠得很近形成微小液滴,它们也不会形成分子;它们只是聚集成一团团的。每个原子的最外层壳层都充满了电子,达到了饱和状态。由于离原子核较远,这些外层电子有很大的自由度。所以在原子团簇中,你有一堆外层电子只是闲逛着,等待着有事可做。
罗兹相信,在团簇中,外层电子以某种方式协同合作,吸收来自泵浦激光器的能量。不知何故,它们比在孤立原子中更有效地做到这一点。用量子力学的语言来说,电子与光子耦合。如果你做一个大胆的假设——电子可以以某种方式联合起来——那么一个巨大的、覆盖整个团簇的“伪电子”确实会像捕蝇纸一样与一群光子耦合。“除非我们想到别的,”罗兹说,“我们目前只能接受这个说法。”
当一个“团簇电子”或随便它是什么,吸收了超出应有量的能量时会发生什么?标准的答案是,这些高能原子就像一锅沸腾的电子,然后电子会从原子中跃出,外层电子先行。然而,罗兹认为,一个巨大的“团簇电子”并不会蒸发掉。相反,它像一个高压锅一样待在那里,吸收的能量比理论上应有的多一千倍。不知何故,这些能量随后直接传递给最内层的电子,导致它们开始相互撞击,上下跳动,甚至从深层内壳直接跳离原子。这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罗兹无法确切说明。不过,另一种看待它的方式是,将“普罗米修斯”的紫外光看作一系列电磁波。它们像海啸一样冲刷着原子,使外层电子剧烈地上下晃动,偶尔会从内层壳层撞出一个电子。
由此产生的原子构成了非常奇怪的离子。起初罗兹称它们为“空心原子”。他现在称它们为“瑞士奶酪原子”,因为电子可能从内部任何地方弹出。无论你怎么称呼它们,如果真的能首先从内部移除电子,这有两个巨大的优势。首先,你节省了能量。你不需要像使用蛮力电离那样,为了达到内层的、产生X射线的壳层而轰掉那么多电子。其次,你节省了时间。你不需要将电子完全“煮”掉,然后等待它们返回。
“柔术物理学”并不违背物理定律。它没有消除暴力的需要;它只是给了罗兹更多的杠杆。“粗略地说,这意味着,”罗兹总结道,“如果你把分子做得恰到好处,它就会伴随着X射线‘砰’地一声爆炸。”他仍然需要非常用力地撞击团簇,但之后他就可以袖手旁观,让自然来完成剩下的工作。
大多数理论家觉得这个理论难以接受。“查理关于空心原子的‘瑞士奶酪’观点非常有争议,”杰克·戴维斯说。“人们提出异议,不是针对结果,而是针对解释。他们不怀疑他在实验室里得到的结果。那是大自然给他的。部分问题在于,没有多少研究人员拥有测试这些想法的设备,而少数拥有的人又用的是独特的激光器,产生独特的结果。复制别人的万亿瓦光脉冲充其量也是一个难题。英国的一个小组轰击了氙团簇,但得到了教科书式的结果。另一个小组尝试了氖,得到了壮观的X射线爆发。”
罗兹似乎很享受这场争论。他的理论所受到的反应,他说,“完全具备了真正新事物的特征。”在他于柏林做的一次演讲中,一位顶尖物理学家听到了最后。最后他只说了一句:“胡说八道。”这让罗兹大笑起来——他笑声如雷。“总是有大量的怀疑,”他说,“你得把这东西硬塞进他们的喉咙。”
在去年发表的两篇关键论文中,罗兹不仅将他的理论应用于自己的数据,还应用于其他六个强辐射的例子,这些例子来自他人所做但至今无人解释的实验。“我拿了那六份数据,”他说,“我发现,在每一种情况下,不作任何调整,一切都说得通。”他的“由内而外”理论给出的数字与实验结果相符。“这太惊人了。”然而,一位审阅其中一份手稿的审稿人说,他可以用已有的理论,立马解释其中一半的案例。“我能解释所有案例,”罗兹反驳道,“难道我不应该得到更多赞誉吗?”
罗兹并不关心他关于氙团簇理论的受欢迎程度。他有太多其他事情要担心——也就是回应那些说他只制造了一个“X射线灯泡”的批评者。利弗莫尔的“新星”激光器通过沿着一条线轰击其目标,让X射线在沿线传播时放大,从而将其X射线规整成相干光束。“普罗米修斯”没有足够的能力聚焦在整条线上。它通过将所有能量集中到一个点上来实现其一焦耳能量的巨大威力。X射线从这个点向四面八方爆发。罗兹想,他该如何聚焦和放大从这个微小点发出的X射线呢?
“传统上,”罗兹说,“我的做法是制造一个波导。”波导是一种由反射材料制成的管子或管道,用来传导光或其他电磁波。“嗯,在这些功率水平下,它会爆炸。我们做过实验来验证。我们用了玻璃毛细管。内部,当然,完全被炸毁了。”罗兹又爆发出一阵大笑。“完全失败了。不过,看看会发生什么也挺有趣的;没人指望波导能行。最终的解决方案,”他说,“看起来简单得可笑。你在等离子体中自己制造波导。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告诉电子该做什么。告诉它们制造一个波导,在光穿过等离子体时保持聚焦。我们想出了一个包含优美物理学的解决方案——一个配得上巴里什尼科夫的解决方案。”
乍一看,在等离子体中编排任何形式的运动似乎都是徒劳的。通常,离子和电子是随机乱飞的。但那是因为等离子体通常是热的——你通过注入热量将电子从原子中剥离出来。在像“普罗米修斯”提供的这种极短的脉冲中,电子没有时间变热。“在这些强度下,”罗兹说,“很多电子被剥离,但你会得到奇怪的条件。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等离子体。”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理论家约翰代尔·索莱姆(Johndale Solem)于1987年加入罗兹的团队一年,研究如何在这种冷等离子体中组织电子。他开发了一个数学模型,显示在等离子体中有可能形成通道来引导X射线。在他的模型中,当泵浦激光脉冲穿过时,它会在其尾迹中留下一条离子脊柱。在适当的条件下,从这些离子中逃逸的电子会在这条脊柱周围形成一个负电荷管。这个管会通过反射来限制X射线,就像玻璃纤维的壁限制光束一样。
当然,所有这些都只是理论。而且还有一个难题。索莱姆的计算只表明,在适当的条件下,理论上可以在等离子体中形成一个稳定的电子管。他们没有给出如何实现这些条件的线索。在罗兹能够进行实验之前,他仍然需要某种技术来首先产生这个通道。为此,他需要创建另一个数学模型,这个模型要展示从初始条件——在他那万亿瓦的光斑击中氙团簇之前——到通道形成那一刻会发生什么。一旦通道形成,索莱姆的计算表明,一切都会顺利。但如何从A到B呢?这对这位纸笔物理学家来说是一个非常谦卑的时刻。“我们之前所有的东西都是解析完成的,”罗兹说,“没有用计算机。这个问题非常不同。只有计算机才能追踪等离子体中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这意味着要处理数百万个数字。”
罗兹开始寻找能为这个等离子体建模的人,并为安排超级计算机使用时间所需付出的努力而烦恼。在美国,人们要么不感兴趣,要么说有兴趣但从未跟进。然而,在莫斯科,罗兹找到了有空闲时间的理论家和性能不算顶尖的计算机。当然,罗兹喜欢他们的风格——他们用高效的代码来弥补计算机性能的不足。他和这些聪明的俄罗斯人开始了正式合作。“他们做了计算,”罗兹说,“来这里访问了一次,给我看了结果——那幅图基本上就是一个曲线图。”他们到达的那天,对罗兹来说,是和氙气爆发那天一样伟大的时刻。
“我当时站在门口,”罗兹说。他看到一张电脑图形放在桌子上,他说,立刻,“一切都绝对、完全清楚了,这东西能行,以及为什么行。”在图上,罗兹看到一个巨大的能量峰值沿着等离子体中的一个通道直冲而下。他已经知道这样的通道可以存在。他现在看到的是,这个通道会从他可以用他那万亿瓦的光斑在等离子体中实际创造的初始条件下自动形成。他看到了他可以从A到B。“我们做了实验,”他说,“结果完全吻合——分毫不差。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惊人稳定的过程,而那些计算对于我们理解通道形成至关重要。”最近的照片确实显示了通道和明亮的X射线束。它们直接穿过等离子体,形成一条比“普罗米修斯”最初激发的空间长70倍的线。“换句话说,”罗兹说,“太棒了!”又是一阵大笑。“那是一道巨大、明亮的X射线束。”
最近,罗兹估算了他的光束有多亮,以及它达到峰值功率的速度有多快。这些数字是热核级别的。在十万亿分之一秒的十分之一的时间里,这些小团簇辐射X射线的亮度相当于一颗一百万吨级的核弹。
现在,罗兹要实现他制造X射线激光器的目标,只需要证明他可以放大这束光。早期的计算看起来很有希望。他的团簇发射X射线的速度非常快,以至于它们紧跟在“普罗米修斯”脉冲的尾部。它们在受激原子有时间衰变之前就击中了它们。他的光束实际上是一道非常短的光痕,不到一毫米长,泵浦脉冲在前面,X射线紧随其后。理论上,当X射线束穿过通道时,它应该会变得越来越强。到目前为止,罗兹还没有在实验室中证实这一点,但他似乎有信心能够做到。
“既然其他所有部分都吻合了,”他说,“放大作用应该会自动发生。所有那些数字似乎都对得上。”他说,很快,他们就能拍摄分子的照片了。他知道他们会遇到问题,但他以典型的罗兹式傲气迎接它们。“第一个会很难,”他说,“第二个会容易些,第三个更容易。等你做到第十个的时候,就成了例行公事。一周后你转个身就能拍一张。一个月后,他们会把 literally 一篮子的照片放到你桌上。你会有多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