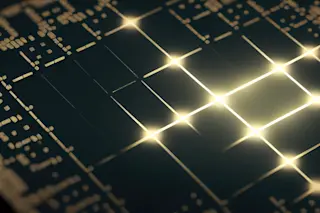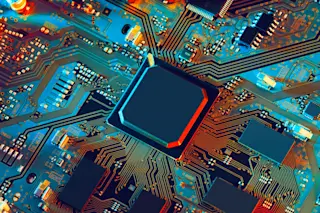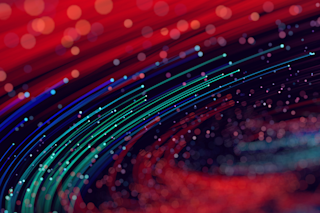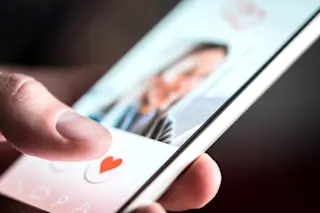西雅图可能是这个国家最美丽的城市(哦,纽约,别担心,我仍然爱你)。我在这里物理系完成了我的研究生工作,每次回来都有些伤感,因为它实在是太绿意盎然,太充满活力了(所以这里的人都需要一个纹身套袖了吗?)。尽管我有些伤感,但我很幸运有机会在这里就科学、宗教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许多话题发表一系列演讲。太平洋科学中心在西雅图中心附近的一家酒吧举办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科学咖啡馆。周二,我在那里就时间和宇宙学做了一次演讲,听众非常投入,非常富有思考。这个话题显然与神话和宗教息息相关,我们都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周三,我在该市的绿色之城(Emerald City)一家很棒的 NPR 电台 KUOW 上,接受了Steve Sher 的采访。在这两种情况下,确定性这个问题都对我来说浮现了出来。Steve Sher 既幽默又有见地。他的问题促使我花了很多时间反思确定性在科学和宗教中的作用以及人们对它的渴望。我认为,确定性是问题的根源。当然,在个人的科学工作中不是这样——我真的很想确定我的研究小组在过去 7 年里一直致力于开发的大规模天体物理学模拟代码能够准确地重现恒星爆炸波和湍流恒星形成云(这是我们研究的两个课题)的物理学。我的同事在罗切斯特大学也想绝对确定他们为斯皮策太空望远镜开发的可探测器能完全按照计划运行。在我们进行的每一次调查,以及我们写的每一篇论文中,我们都希望并需要尽可能多的确定性。这是理所当然的。当人们寻找某种终极的、包罗万象的答案时,确定性就成了问题。这正是科学与宗教辩论变得重要的地方。当宗教机构以确定性之名要求严格遵守教条和信条时,像我这样的科学家——习惯于开放式的讨论和发现——会正确地感到不适。但是,当以科学之名,有人认为所有真理都必须遵循狭隘的还原论时,那些有更广阔视野的人会感到不适。当科学为了确定性而变成科学至上主义时,对世界的一种重要的创造性回应就消失了,就像在仓促追求宗教教条时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确定性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反应。外面的世界可能非常可怕,作为回应,人们想要一些“宏大”的东西来抓住。我认为,作为一个物种,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而我们做出的选择很可能会决定我们的命运。我们以确定性之名越是紧抓不放,就越有可能以某种形式落入不屈不挠的偏执——这不太可能对我们面临的巨大、迫在眉睫且可能致命的挑战有太大帮助。
亚当·弗兰克是罗切斯特大学的天体物理学教授,他使用超级计算机研究恒星的形成和死亡。他的新书《永恒之火,超越科学与宗教的辩论》刚刚出版。他将加入 Reality Base,就科学与宗教进行持续的讨论——你可以在此阅读他之前的帖子,并在 Constant Fire 博客 上找到他更多关于科学和人类前景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