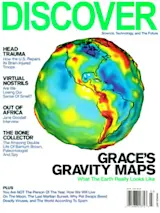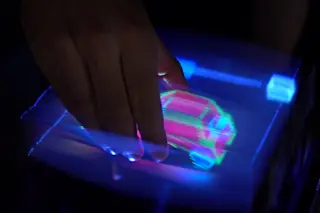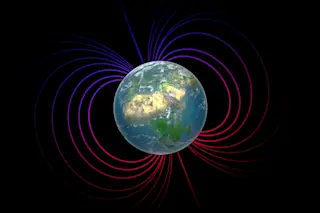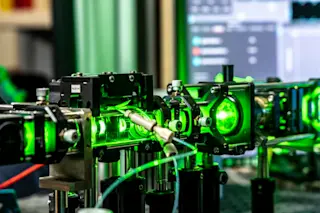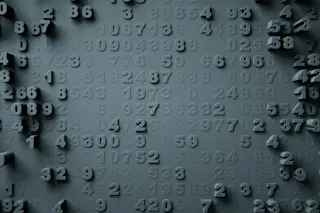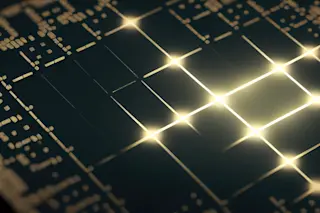我想知道有多少人翻阅了《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特刊,看着封面上的小银镜,并为自己能够跻身于杂志编辑们认为配得上这份特别荣誉的 3 亿人行列而感到由衷的自豪。毕竟,我们面临着严峻的竞争。
我仿佛能看见《时代》周刊的编辑们穿着挺括的衬衫围坐在会议室的桌子旁——因为担心冒犯来自红色州或蓝色州的读者,或者两者都得罪——最终放弃了,将整个难题抛诸脑后:如果这些恼人的网络博主读者无论我们选择谁都会给我们脸色看,为什么不干脆选择*他们*呢?
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有一种扭曲的逻辑。互联网使得人们能够在没有任何编辑过滤或构建的情况下获取信息,那么又何必费心扮演编辑的角色呢?更好的是,为什么不拥抱这个互联网,而不是继续与之对抗呢?让我们向那些大量的博主和 YouTube 用户展示,这次我们站在*他们*一边。
“欢迎来到你们的世界,”文章这样说道。(他们欢迎*我们*?我们不是*先*在这里的吗?)“因为你们掌握了全球媒体的缰绳,创立并构建了新的数字民主,并且不计报酬地在他们自己的游戏中击败了专业人士,《时代》周刊 2006 年度人物就是你们。”
哦,谢谢。但这种虚伪的谦虚让人感到谄媚。它仅仅暴露了编辑们仍然多么看重自己作为意见塑造者的角色:我们从自上而下的媒体中解放出来,直到自上而下的媒体自己宣告这一点,才算真正的解放。
那么,我们真的被解放了的证据在哪里呢?诚然,YouTube、Facebook 和 Wikipedia 改变了内容的生产方式。但对于从中获利的 corporations 来说,这仅仅是娱乐时间如何向消费者计费方式的转变。我们不再支付费用去电影院观看电影,而是支付费用制作和上传我们自己的电影到网上。我们不再支付唱片公司费用去听他们艺术家在 CD 播放器上的音乐,而是支付电脑公司硬件费用、互联网接入公司带宽费用以及软件公司媒体播放器费用来完成这一切。
“硅谷的顾问们称之为 Web 2.0,好像它是某种旧软件的新版本。但这真的是一场革命,”《时代》周刊热情地说道。抱歉,但革命是历史上的那些时刻,当暴民冲进宫殿,砍掉那些剥削他们的人的头颅。
相反,《时代》周刊愿意承认互联网用户的力量,这暗示了企业界已经安然度过风暴的信心:如果 YouTube 上正在播放的内容是“人民”所能做出的最好的东西,那么媒体垄断就没什么好害怕的了。即使是网络上最受欢迎的视频,也只能火几天——最多而已。大多数政治讨论都非常愚蠢,让有线新闻的争吵看起来都很有智慧。不如让他们继续“吃博客”。
我对互联网连接人们和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促进协作的潜力感到非常兴奋。仅维基百科就证明了整个实验的价值。但认为消费者与向他们销售商品的 corporations 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这是一种幻想。
我们仍然使用昂贵的消费技术创作内容,并将它们上传到 corporations 拥有的服务器,通过 corporations 拥有的渠道。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这一切都是使用 corporations 的软件完成的,这些 corporations 的利益已根植于其代码之中。许多视频网站的用户协议要求我们放弃对自己创作内容的部分或全部权利。iTunes 像营销人员监控 MySpace 和 SecondLife 上消费者行为一样,密切监控我们对音乐和视频文件的使用情况,而 Gmail 的计算机则阅读我们的电子邮件对话,以便决定向其中插入哪些广告。每一次按键都成为我们消费者画像的一部分;每一次自我表达的尝试都被简化为品牌偏好。
如果《时代》周刊在 1995 年——在互联网被简化为一个电子购物街和市场调查之前——就宣布我们为年度人物,那可能是一种大胆,甚至会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然而,当时,该杂志还在凭一篇耸人听闻且不准确的关于网络儿童色情的封面故事来嘲笑互联网。在此期间,华特迪士尼及其同类的媒体巨头可能已经清理了时代广场,但现在我们的孩子在新闻集团旗下的 MySpace 上为了吸引眼球而“卖淫”。企业界已经足够自信地取得了胜利,以至于现在将其作为媒体权力转移的所谓象征卖给我们。
是的,我们使用媒体的方式不同了,坐在椅子上上传东西,而不是坐在沙发上下载东西。但最终,我们仍然被粘在电视机前,观看的大多是垃圾,像愤怒的白痴一样争吵,出卖我们最后的隐私,并为此向大型 corporations 付出更多的钱。
当时代华纳旗下的 CNN 在《CNN 特别报道》节目中宣布年度人物时,该节目播出了一期内容,这不仅仅是为其姊妹杂志,更是为其母公司的在线服务 AOL 和 Road Runner 做广告。无论如何,所有被加冕为年度人物的我们,实际上都只是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