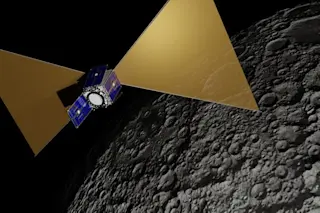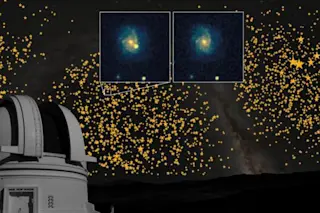一年多以前,我参加了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组织的一次会议,主题是如何通过鼓励科学家与媒体之间加强合作来增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与会的科学家大多是科学院的成员,科学院既是一个荣誉学会,也是美国政府的科学政策官方顾问。我在房间对面看到一个瘦高的人,他看起来有些熟悉。他从容的动作暗示着他平静的外表下隐藏着一种内在的激情。当我走近到足以看清他名牌时,我看到他就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卡尔·萨根,我曾与他通信,但从未见过面。
我们互相介绍了自己,开始了一段现在看来令人心酸的对话。萨根提到他听说我患上了一种可能致命的癌症,他问我情况如何。我回答说我做了手术,据我所知现在已经完全治愈了。他主动说他也有过一次与癌症的擦肩而过。他被诊断出患有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这是一种可能发展成白血病的疾病,但他接受了治疗,他说已经治愈了。不幸的是,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因骨髓移植并发症去世,离圣诞节只有几天。事后回想,我不知道他当天见面时平静的外表是否预示着即将发生的事情。
那天晚些时候,在一次关于向公众传播科学重要性的集体讨论中,我提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悖论:那些能够有效地与公众沟通的科学家,往往发现他们的同事对此报以轻蔑,甚至以影响他们职业生涯的方式惩罚他们。我的发言促使萨根雄辩地发言了15分钟。他描述了他也曾受到其他科学家的抨击,但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字斟句酌地选择用词——对他来说,这些不利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严重。当他说出这些话时,我感到我的其他科学院成员屏住呼吸,等待萨根是否会提到他曾遭受科学院成员自身施加的尖刻侮辱。事实上,他策略性地避开了几年前发生的丑闻,当时他成为科学院漫长历史上少数几个被暂时选举为会员但随后在特别投票中被单独否决的人之一。
萨根被拒通常不会在学院之外为人所知,因为成员们被要求对选举事宜保密。然而,一些身份不明的成员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他们将此事泄露给了媒体。(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错过了那次会议。)简单来说,正如媒体所描述的,萨根是被提名的众多科学家之一,他的候选资格通过了初步筛选阶段,他的名字出现在寄给学院成员的选票上的长名单中。投票结果显示他位列得票最多的60位候选人之一。这些顶级候选人通常在年度会议上被接受为当选者,无需进一步讨论。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萨根的临时当选在会议现场被单独提出并受到质疑。根据学院章程,受到质疑的提名人将被取消,除非其候选资格得到在场并投票的三分之二以上成员的支持。经过激烈的辩论,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投票否决了萨根的当选。这一罕见的当众羞辱结束了他的候选资格。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千多名科学家被选入科学院,但我只记得另一位候选人被否决,很少有其他人甚至挑战失败。学院会议上的大部分反对意见都围绕程序问题,或者萨根对科学研究的贡献据称不足。毫无疑问,他的一些反对者确实对他取得的成就评价不高。然而,萨根的研究广为人知,并且显然被科学院成员认为足够重要,以至于他们最初暂时选举了他。他在解释金星独特的大气层、火星外观的变化(由沙尘暴引起,而不是像之前假设的运河或植被季节性变化)、地球和金星上的温室效应、地球有机物的起源以及地外生命的条件方面,功不可没。他还在水手号、维京号、先驱者号、旅行者号和伽利略号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任务改变了我们对所有外行星的理解。
很可能萨根之所以失去了他在科学院的潜在席位,不是因为他未能产出足够重要的科学研究,而是因为他在普及这些研究方面取得了太大的成功。对公众来说,萨根是迄今为止最著名的美国天文学家,也是任何学科中最著名的美国科学家之一。这种声誉源于他向公众解释科学的独特能力。他的电视系列节目《宇宙》于1980年首次播出时,吸引的观众比之前任何其他公共电视系列节目都多,并持续保持这一记录多年。它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能激发公众对天文学的兴趣和对美国宇航局昂贵的行星探测计划的公众支持。但萨根的沟通技巧却矛盾地引发了许多科学家的强烈反弹,他们不相信他能同时是一位严肃的科学家和一位魅力十足的电视名人。
是什么让学院拒绝萨根如此悲剧,又最初如此难以理解,正是科学家们自己经常提出的所有有效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公众理解科学如此重要。我至少看到了五个这样的理由,值得详细说明,以便我们能够理解国家科学院拒绝萨根所暴露的态度带来了如此大的问题。
首先,科学并非晦涩难懂,只为少数人所知。我们每个人——无论是诗人、清洁工还是核物理学家——都必须能够进行科学思考,并理解一些科学,才能度过我们的一生。我们每天都面临着依赖科学的决策,比如是否吸烟、吃什么、与谁发生性关系以及使用什么保护措施(如果有的话)。即使是那些不依赖具体科学事实的决策,科学仍然是获取世界准确信息的最佳方法。
第二,我们中的一些人最终会成为政府或企业的决策者。这些人做出的决策从根本上影响着每个人的福祉,但他们对科学的了解并不比普通大众多。然而,他们被要求决定如何处理(以及花费多少钱)核反应堆、全球变暖、环境毒素、昂贵的太空计划、生物医学研究以及生物技术的应用。决定我们饮用的牛奶是否可以安全地来自经过生长激素处理的奶牛,最终话语权属于非科学家,而不是科学家。为了明智地做出这些决定,决策者必须从受过科学教育的公众中选拔出来。
第三,作为选民,我们都对这些决定负有最终责任,因为我们是决定哪些候选人和哪些议案会获胜的人。我们需要足够的科学常识来选择那些在面对科学问题时会做出明智决定的决策者。
第四,即使科学与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无关,强大的科学事业对于我们的经济、教育体系和社会也至关重要。这需要大量的年轻人对科学足够兴奋,从而决心成为专业的科学家。科学家与公众的良好沟通对于激发这种兴奋至关重要。
最后,科学家们自己应该出于自私的原因而有兴趣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他们的工资和研究拨款取决于国会、州立法机构和私人基金会中掌管钱袋的非科学家。那些资金提供者根据他们认为科学的重要性来做出决定。
所有这些要求公众理解科学的论点,都是科学家们正确地提出并比任何人都更理解的。因此,你可能会期望他们对像卡尔·萨根这样投入大量精力培养这种理解的少数科学家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和激励。然而,矛盾的是,科普工作者面临着普遍的冷漠、敌意和惩罚,例如荣誉和晋升被推迟甚至被拒绝。萨根被科学院拒绝只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
结果,那些擅长沟通的科学家绝大多数都处于职业生涯的后期。他们等到获得终身教职,从而更能承受同事的敌意。年轻或未获得终身教职的科学家在公众面前相对沉默,因为他们意识到否则可能会带来职业生涯的毁灭。然而,对于年轻科学家来说,成为有效的沟通者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是研究最活跃、受行政职责分散最少、以及年轻人的最佳榜样。
当然,这些概括性的说法也存在例外。科普工作者在同行中的看法似乎因科学领域而异。他们在进化生物学(例如,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和医学科学及分子生物学(刘易斯·托马斯)中更容易被接受甚至受到钦佩,但在化学、数学和天文学(卡尔·萨根)中数量较少且更不被容忍。你的做法也起着作用:那些生动地展现自己个性(又是萨根)的科普工作者比那些专注于科学发现本身(例如,理查德·道金斯)的容忍度更低;那些目标受众是全体公众(又是萨根)的科普工作者比那些主要针对大学生的(理查德·费曼)受到更多抨击。但这种矛盾的趋势依然存在,需要解释。为什么科学家对那些既促进科学家利益也促进公众利益的同事表现出如此多的冷漠或敌意?
一方面,与公众和同事沟通需要截然不同的风格。当我们为同事撰写研究文章时,我们被训练避免简化;力求精确,使用专业术语,插入所有适当的限定词(如果,但是,也许),并提供所有相关细节;避免生动、诗意的语言,因为它可能暗示我们试图用华丽的词藻而非正确的论证来取信于人;以非个人化的方式写作,用第三人称(作者做了这个实验)或被动语态(实验已完成)取代第一人称(我做了这个实验),因为科学应该是关于真理而不是关于个人自我;并详尽地感谢同事,以免我们似乎在声称不应得的荣誉。
当然,如果我们愚蠢到将一篇以那种风格写成的文章投稿到面向普通大众的杂志(比如《发现》),它会直接被扔进废纸篓——原因也很充分,因为它会枯燥乏味,难以理解。相反,面向公众的科学解释必须简洁、直接、生动。当我们为大众读者写作时,我们必须使用非技术性语言,并以第一人称表达,必要时进行简化以使我们的观点清晰。对于我们科学家来说,要扭转一生的程序设计,去赞扬一位我们可能努力压制多年的写作方式的同事,是很难的。看到一位同事违反了所有这些学术写作规则却逍遥法外,这让我们感到愤怒。
科学家也是凡人,他们对那些有效的科普工作者所受到的关注,嫉妒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卡尔·萨根所说,“一位毕生研究钼原子超精细结构这样晦涩事物,却除了世上另外三位钼专家之外无人问津的科学家,看到记者们围着我,听我发表关于地外生命可能性的最新论断,自然会感到嫉妒和愤怒。”
最后,科学家倾向于认为,任何屈尊向公众解释其工作的同事,都已不再是严肃的科学家,这样做是因为他或她已无力从事真正的科学研究。确实,科普工作者往往是年长的科学家,但同样,那是因为年轻科学家害怕职业生涯的毁灭。
科学家们回避清晰的写作和演讲所带来的不幸结果,公众的困惑并非唯一。还有另一个悲剧,一个受到关注少得多的悲剧:大多数科学著作,即使是科学家,除了作者狭窄领域的专家,也难以理解。让我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它只涉及最近的一篇研究文章。我几乎是随机从每年发表的数十万篇研究文章中选择的。我选择这一篇特别是因为它来自世界上两本最具影响力的科学期刊之一,据称致力于科学家之间的广泛交流。这就是《科学》杂志,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从物理学家到心理学家的所有美国科学家的伞形组织)的周刊。《科学》发表涵盖所有领域的文章。根据刊头,其 [AAAS 的] 目标是“促进科学家的工作,促进他们之间的合作……并增进公众对科学方法在人类进步中的重要性和前景的理解和认识。”《科学》给未来投稿者的说明中写道,“提交的稿件应能被不同学科的读者理解。”
我打开最近一期的《科学》杂志,随意选择了一篇在杂志15篇研究报告中间的文章。目录标题是:通过非细胞毒性TRAF2依赖性途径激活TNF受体1介导的SAPK/JNK。在这个标题中,只有“非细胞毒性”一词是我对文章主题的唯一线索。细胞毒性是指对构成植物或动物身体的活细胞有毒。因此,我现在确信这篇文章的主题领域不是物理学或心理学,而是细胞生物学。由于我从事专业生物学研究39年,我的研究领域包括细胞生物学,所以我比大多数其他科学家更有可能是这篇文章的目标读者。然而,我从未听说过SAPK、JNK、TNF、TRAF2,或它们的受体或途径,所以我对这篇文章的主题一无所知。这个标题也没有给我任何理由怀疑它有趣、重要或与我的工作相关。通常,我会跳过这种难以理解的文章。
我翻到第200页,读了报告的第一句话:“p55肿瘤坏死因子受体1(TNF-R1)相关信号转导因子TRADD与FADD的相互作用会触发细胞凋亡,而TNF受体相关因子2蛋白(TRAF2)是激活核转录因子核因子kappa B所必需的。”这句话引入了更多不熟悉的术语(p55、TRADD、FADD、细胞凋亡——其中大部分在整篇文章中都没有定义)。它包含了一串由九个名词和名词形容词组成的短语(p55...TRADD),我很难弄清楚哪个名词被用作形容词来修饰哪个其他名词,还有一串由五个名词和形容词组成的短语(核转录因子核因子),我不确定重复是故意的还是印刷错误。我最终意识到,缩写TNF和TRAF的定义隐藏在句子里(你可以自己试着找找看),于是我继续阅读了这份简短报告的其余部分,但最后我仍然不知道它讲的是什么。
我并非单独挑出这份报告来嘲笑它或将其标记为例外。几乎任何其他科学期刊中的大多数报告都能同样好地说明我的观点。相反,我将其引用为第二个悲剧的完全典型例子——即便是科学家也不可能理解大多数由科学家撰写的文章。也许这份SAPK/JNK报告揭示了一些可能让我自己在研究中取得突破的发现。但除非我花费大量时间去理解这份报告(例如,请同事向我解释,或阅读大量教科书中的背景材料),否则我永远不会知道。我不会花那个时间,因为每周都有数千份科学报告发表,我不能把更多时间浪费在这一份特定的报告上。相反,我会继续寻找我能理解的、并且我能识别出它可能与我的兴趣相关的文章。
不幸的是,伟大的科学进步尤其来自于将一个领域的发现应用于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领域。例如,如果原子物理学家没有将他们关于原子量为14的碳原子不稳定性的发现应用于古埃及纺织品,我们就不会有放射性碳测年法。以难以理解的方式描述的研究会大大降低其价值,因为人们很可能忽视其在直接领域之外的潜在应用。
科学家们设置如此巨大的障碍,令人悲哀。解决这个问题会非常容易——例如,我们可以少发表20%的报告,但通过将每篇已发表报告长度的20%用于定义术语和向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介绍主题,从而将可理解性提高10,000%。英国版的《科学》杂志《自然》最近发表了一篇社论,讨论了可读性问题,并推荐了正是这类解决方案。编辑写道,作者可以请领域外的同事阅读他们的文章。他们至少应该在《自然》编辑催促他们删除第一段中第n个未解释的缩写时,积极回应。
卡尔·萨根在解释SAPK/JNK激活方面会做得更好,无论那是什么。正如刘易斯·托马斯向我们展示的,在细胞生物学中清晰地解释事物与在天文学中一样可行。但几乎所有美国科学家都知道萨根被国家科学院拒绝以及普及科学的其他后果。每个科学家都能够认识到这对自己的切身利益的明显影响。
结果,向公众解释科学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委托给了非执业科学家的科学记者。甚至《科学》杂志也使用记者在名为“研究新闻”的引言部分向科学家解释最近的科学进展。然而,记者,无论他们多么有天赋,都无法取代科学家本人作为考虑从事科学事业的年轻人的榜样,也无法在预算听证会时在国会面前作为倡导者,或者只是作为对其主题最了解的人。这需要像萨根这样的人。
当然,再也不会有第二个卡尔·萨根了,他的逝去显得格外痛苦,因为我们太需要像他这样有能力的科学家了。一个还不够:我们需要成千上万个。但我们永远也得不到他们——除非科学家和他们的组织彻底改变他们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