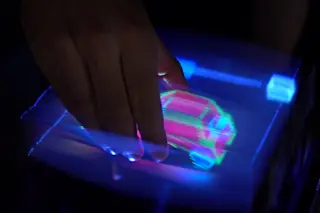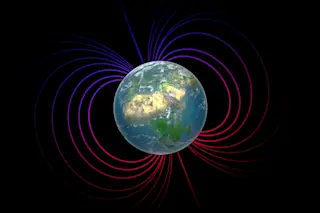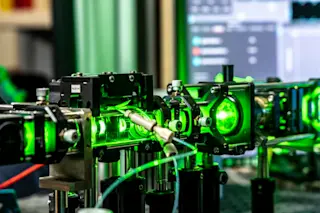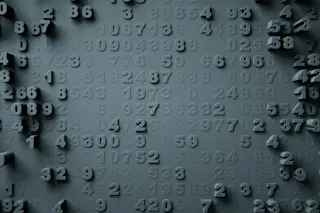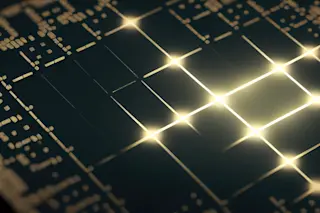2001年秋季,五人在暴露于通过邮政信件传播的武器级炭疽杆菌(炭疽病)孢子后死亡。这起至今未破的罪案引起了国家和国际社会对生物恐怖主义和生物战争日益增长的危险的关注。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David R. Franz表示,未来的生物恐怖袭击可能难以避免。他花了25年多的时间研究——并准备应对——生物战争和生物恐怖主义的医疗对策。Franz在获得生理学博士学位之前是一名兽医,现任中西部研究协会的副总裁兼首席生物科学家。他也是国家农业生物安全中心的创始主任。20世纪90年代末,Franz曾三次作为首席检查员代表联合国特别委员会对伊拉克进行生物战争检查。
在您检查伊拉克期间,您发现了生物武器。
DF:是的,我们发现了。在1998年那个时期,我们发现了。我认为那不是一个高质量的项目。
您对最近的检查没有发现生物武器感到惊讶吗?
DF:不。在我们第二次进入之前,我已经在MSNBC和CNN上表示,如果这次我们找不到生物武器,我不会感到丝毫惊讶。
听起来我很有先见之明,但在我接着的发言中,我在MSNBC和CNN上说,我们肯定会找到化学武器。
为什么还没有发生生物恐怖袭击?
DF:我被问到的最难的问题是为什么还没有发生。它并不像每个人说的那样容易。当你分析所有可能的场景时,你会发现技术上对坏人来说存在困难,幸运的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比普通人更不担心它,普通人只知道生物可能会带来坏事。
我想到的是一系列技术障碍。在最低端,像牛的口蹄疫……在光谱的另一端是经典的病原体——炭疽、鼠疫、兔热病。在那里存在重大的技术问题。
为什么最低级别的袭击没有发生?那是一个行为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在我看来,这是意图问题。而且,不知何故,它还没有发生。
我们不能开发出能够检测到袭击——空气中的炭疽——的传感器吗?
DF:如果我们有了那个,我们可能就不需要考虑疫苗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口袋或钱包里放一个小东西,可以戴上以保护我们的呼吸道。但是,我认为我们达不到那一步。生物探测器很复杂。你需要针对病原体的抗体,或者PCR引物,而且探测器需要大量的维护和保养。
新兴疾病与生物恐怖之间有关系吗?
DF: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我的看法,但我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来思考:生物恐怖主义=新兴传染病+意图。
如果我们能够阻止一个想要造成伤害的恐怖分子吗?
DF:我认为这会非常困难。如果我们做到了,很可能是通过情报部门的发现。我们听到有什么计划,或者有人在地下室或某个洞穴里有一个小实验室,或者我们在世界某个地方的科学同事与某个听到事情的人合作。
假设您无法阻止它,然后呢?
DF:我研究了这些病原体,并说对于医疗对策,我们无法列出一个“1到N”的清单,然后说我们要按列表逐个制作疫苗——数量太多了。所以我研究了那些(危险的)异常值。
现在我们有足够的天花疫苗来免疫人口。我们现在有炭疽疫苗和炭疽抗生素,并且我们有一些储备,并为口蹄疫做了很多其他准备。
然后在其下方,在我们负担不起进行特定对策的情况下,我倾向于监测和通用诊断。诊断更容易通过FDA。任何需要注射到人体内的东西,或者人们口服的东西,都需要经过更多的审批程序。
然后在其下方是强大的生物技术和基础生物研究基础设施。未来,我认为我们会开发出更通用的对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
还要多久?
DF:我总是说30年。
从长远来看,您是否会推动病原体向更狡猾、更具抗药性方向进化?
DF: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这取决于病原体。
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吗?
DF: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我们无法阻止生物恐怖分子。我们可能会通过威慑来阻止一些,如果发生,我们就有这些通用的对策和一个良好的公共卫生系统,然后对于我们无法处理的情况,我们需要让人们具有韧性。
您指的是什么?接受它会发生,然后处理它?
DF:差不多。永远不要接受恐怖主义——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与之斗争——但要能够处理它,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而不是其他任何方式。
我认为公众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信息。他们想听到的是它不会发生,并且如果发生了,他们会受到保护。
DF:我想到两个例子。一个是以色列。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更有韧性的社会。但这并非偶然。他们专注于教育,专注于理解恐怖主义。
然后我记得在卡特里娜飓风后看到的一段新闻,是关于农村地区的卡津家庭。他们带着船、枪,去查看邻居。他们习惯于自给自足,并且拥有紧密的社会结构。这些东西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我也认为这是一种韧性。
有人计算过一个人被生物恐怖分子袭击的几率吗?
DF:你更有可能被卡车撞。我们每年有44万人死于吸烟相关疾病……我们每年有2-8万人死于流感,12万人死于交通事故。我们有五个人死于生物恐怖主义。
我确信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为什么要把钱花在这件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上,而不是花在这些已知的事情上?
DF:一个原因是,我们愿意让我们的同胞死去,如果他们知道这需要很长时间,而且他们有点享受导致死亡的过程。就像吸烟一样。我们愿意让老年人或免疫系统不好的人死于流感,因为他们可能很快就要死了。我们不愿意冒哪怕是很低的死亡风险,如果有人故意这样做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做,但没有人可以对我们做。
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生物恐怖分子,难道你不会研究一种出乎意料的、不太危险的生物,然后让它变得更糟吗?
DF:坏消息是生物学非常不稳定;好消息是生物学非常不稳定。对于我们这些对对策感兴趣的人来说,你认为你已经掌握了一种疫苗,或者你认为你拥有完美的抗病毒药物——然后你会发现它有毒,或者疫苗保护了老鼠但没有保护灵长类动物。幸运的是,对于那些想利用生物学对付我们的人来说,情况也一样。你可以召集一群专家,分子生物学家、病毒学家,让他们说“我能做到”,但当你进入实验室,它不像在会议室里那么容易。
您最担心什么?
DF:我可能最担心的是高度传染性的人类病原体——流感、天花——它们可能对这个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因为世界变得更小了,而且我们今天还有艾滋病病毒/艾滋病。
这有什么关系?
DF:我认为我们再也无法根除天花,因为我们无法为艾滋病患者甚至HIV患者接种疫苗(因为他们可能会对疫苗中的病毒易感)。
我担心的另一件事是一个叫做“重装”的概念。假设你在美国十个城市拥有两公斤高质量的粉末状炭疽。它可能不会完全有效,但可以感染很多人。然后你说‘两周后,我将袭击下一个城市,我不会告诉你是什么,’然后你袭击下一个城市。这是可行的,并且会很难处理。
是因为伤害还是心理创伤?
DF:如果他们说‘下一个目标是底特律,’你可以应对。如果他们不说(地点),那将产生真正的心理影响。如果你知道有10,000人患有吸入性炭疽病,其中很多人会死亡,你还想去市中心或任何地方吗?
如果有什么让我感到害怕,那就是传染性病原体,因为一次疫情可以从一小群人开始,然后就……蔓延开来。
DF:我认为我们会很快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可能会减少旅行,我们去超市时可能会戴口罩,我们可能会更经常洗手。
我们应该如何担心农业生物恐怖主义?
DF:农业威胁的严重程度低于我们可能与大规模自然灾害相比的阈值。但我担心口蹄疫,因为它可能摧毁我们的经济。口蹄疫可能给我们带来数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如果你重写历史,9-11袭击从未发生过,有人会认为飞机被劫持并撞向目标是可能的吗?那么,未来的袭击会不会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DF:回到我的公式:生物恐怖主义=新兴传染病+意图。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医疗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来监测新兴传染病。所以,我认为我们在生物方面比在下一次恐怖事件——有人驾驶飞机撞击桥梁,那些离谱的事情——方面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