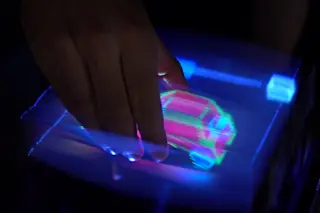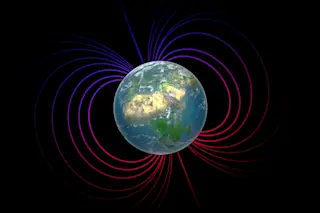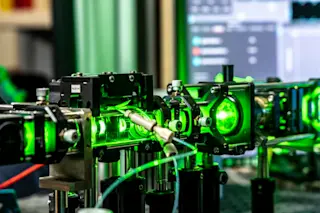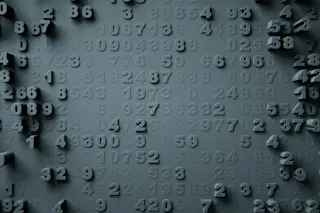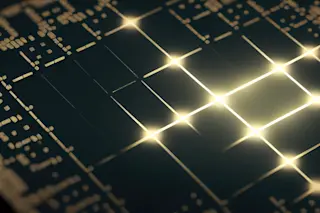我写作的时候,正凝视着我的“钱兔”。它是一个棕色的、没有毛的老东西,多年来被磨得光滑,它也用一只略微突出的塑料眼睛回望着我。这只兔子几乎要爆开了。每次我从国外旅行回来,我都会把口袋里的零钱通过它背上的缝隙倒进去。然而,再次离开前,我从不记得取出合适的货币。因此,这只兔子有一个现金流问题。
我决定把小塑料塞子从它底部拔出来。一大块英国英镑首先堵住了流出,坚实而沉重,每枚硬币都印有伊丽莎白戴着王冠的侧面肖像——在最老的硬币上是年轻女子,后来是英俊的妇人,但始终如一的是女王。接下来是德国马克和德国鹰,在一个如今如此爱好和平的国家,它们显得异常返祖:在5马克硬币上,猛禽的羽毛和爪子张开,舌头伸出,仿佛即将捕杀或刚刚被电击过。无论哪种方式,它都显得严峻。西班牙的25比塞塔硬币紧随马克之后;它中间有一个孔。5比塞塔硬币上描绘了一个身穿戏服的人,他要么在里奥哈地区踩葡萄,要么在踩高跷跳舞,很难分辨是哪一种。
然后是“播种者”(Semeuse),她装饰着法国法郎。她的长发从她的弗里吉亚帽(革命解放的象征)下飘扬;她的裙子以薄纱般的褶皱紧贴着她修长、优雅的双腿。她在日出时分穿过一片田野,漫不经心地挥动右手,将左手袋中的种子撒向风中,这似乎有着某种意义。也许只是因为我是个亲法者,但对我来说,法郎是完美的硬币。它不纪念僵化的君主制或好战的过去;它颂扬生命,以及法国的生命本应是怎样的:感性的、尊严的、人道主义的。我曾无意中试图把10比塞塔递给安妮克,这位年轻女子每天早上在面包店里递给我法棍面包。几乎就在那枚叮当作响的小硬币落到她柜台上的盘子之前,她就发现了。
人们对他们的钱有一种感觉。你知道一枚五分硬币、一角硬币或四分之一硬币放在口袋里的感觉,以及它们中的许多放在银行账户里的感觉;安妮克通过视觉、声音和触觉就能分辨比塞塔和法郎。不久前,我问她对欧元有什么看法,这种新的欧洲货币很快将取代法郎和其他国家货币——欧元的电子交易将于1月1日开始,新的硬币和纸币将在三年后发行。她不想谈论它。“那将是地狱,”她说。
第一枚名为法郎的硬币铸于1360年。它描绘了国王“好人”约翰(Jean le Bon)骑马凯旋的形象。实际上,约翰当时刚从英国监狱获释,百年战争大约进行到四分之一,此前他发誓要支付12.5吨黄金的赎金,但他并没有。解决方案是向他的人民征税。作为回报,约翰承诺给他们一种强大而稳定的货币——因此在金币上出现了骑马的形象。法郎现在由镍制成,但它作为一种国家货币——尽管有过长时间的中断和形式的改变——已经持续了638年。(税收也一样。)明年某个时候,从他俯瞰塞纳河的高窗办公室里,巴黎铸币厂厂长伊曼纽尔·康斯坦斯(Emmanuel Constans)将主持最后一枚法郎的铸造。他说他一点也不会感到遗憾。
高大、精致、银发、五十来岁的康斯坦斯是法国经济、财政和工业部的高级官员。他也是一位坚定的欧洲主义者,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工作了六年。在我去年五月见到他两周前,各国政府领导人齐聚布鲁塞尔,宣布明年一月将成为“欧元区”的11个国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西班牙和葡萄牙;爱尔兰、芬兰和奥地利。欧盟15个国家中的三个——英国、丹麦和瑞典——已决定暂不加入;希腊希望加入,但被暂时排除,因为其预算赤字、公共债务和通货膨胀率过高。在我见到康斯坦斯仅仅四天前,第一批欧元已在巴黎铸币厂位于波尔多郊区的现代化工厂铸造。法国人民可能仅以51%对49%的微弱优势批准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该条约于1992年2月明确承诺欧洲国家实现货币统一),但法国铸币厂现在是欧洲大陆第一个铸造这种货币的。
六年的准备是必要的,以便欧洲大陆就这种东西的外观、材质以及名称达成一致。每个人都认为——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共同货币将被称为“埃居”(écu)。这是一个中世纪法国硬币的名字,如果你像德国人喜欢的那样写成ECU,它也代表欧洲货币单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各国货币的加权平均值,已在欧洲机构中作为记账单位。然而,事实证明,德国政府从不喜欢这个词。在1995年的一次峰会上,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坚持埃居必须取消:他解释说,“ein ECU”听起来太像“eine Kuh”——也就是说,在德语中,新硬币很容易与“一头牛”混淆。“金币”(Ducats)和“弗罗林”(florins)被提上桌面又被否决了。据法国报纸《解放报》报道,午餐时间临近时,西班牙首相提出了“欧元”(euro),这并非首次。在座的政府首脑们用各自的语言低声念着这个词。希腊人报告说,“欧元”听起来危险地像希腊语中“尿液”的意思。但在这些事情上,希腊的分量不如德国。于是,“欧元”就这样定下来了。
大约在同一时间,瑞典人要求并成功改变了硬币的成分。铸币厂厂长们决定大量使用镍;它有吸引力、耐用,而且法国在新喀里多尼亚的矿山生产大量镍。法郎是纯镍,镍合金硬币在世界各地也很常见——但在瑞典却不是。那里禁止使用镍,因为人们认为处理镍硬币会导致过敏性皮肤反应。感谢瑞典人,面值最低的欧元硬币将完全不含镍。1、2、5分硬币(欧元中有100“分”——很可能按照当地语言发音)将是镀铜钢;10、20、50分硬币将由一种在芬兰发明的新型黄色合金制成,名为北欧金。它主要由铜组成,含有少量锌、铝和锡。
只有1欧元(价值略高于1美元)和2欧元硬币会含镍,而且大部分会安全地夹在铜合金中。这种夹层工艺由德国克虏伯公司获得专利。另一方面,这些硬币将是双色的——1欧元是黄色环绕镍质中心,2欧元则相反——这种复杂的制造工艺是法国的。除了具有典型的欧洲特色外,这些复杂的层次也将使硬币更难伪造。“这两种硬币将是世界上最安全的硬币之一,”康斯坦斯说。
对欺诈的担忧是欧盟委员会希望所有国家的硬币都外观相同的原因之一——不同硬币的数量越多,识别假币就越困难。对公众反应的担忧导致各国政府否决了这一想法。每枚硬币都将有一个欧洲面(反面)和一个国家面(正面)。因此,从2002年开始,欧元区将有88种不同的硬币(8种面值乘以11个国家)流通。然而,就欧元纸币而言,它们将由各国中央银行根据法兰克福新成立的欧洲中央银行的指令发行,欧元官僚和银行家的担忧占据了上风。纸币上不会有国家标志:它们在整个欧元区都将是相同的。
用伟人画像装饰纸币(这在世界各地钞票上很常见)的想法被否决了,因为担心会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负责欧元的欧盟委员会委员伊夫-蒂博·德西尔吉(Yves-Thibault de Silguy)在一份相关入门读物中解释说:“鉴于欧洲大陆的历史几乎是冲突不断,其中没有比这次更血腥的了,因此很难就历史人物达成共识。”中央银行家们转而选择了不同时期的建筑。七种欧元纸币每种都描绘了一个时代,从古典主义到哥特式再到现代,并伴有重复的主题:背面总是一座桥梁(通向未来,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正面则是一扇窗户(向世界敞开)或一个拱门(同理)。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建筑——比如加尔桥或勃兰登堡门。它们是欧洲共同遗产的通用表现形式,所有国家特异性都被抹去。
德西尔吉补充说,如果欧元纸币有国家面,中央银行家们就会面临一个特殊的流通问题。每年夏天,北欧人带着钱南下地中海,但南欧人北上的流量很小。举例来说,如果芬兰纸币和西班牙纸币不同,它们很快就会在西班牙明显堆积起来。西班牙中央银行将不得不从自己的流通中将其筛选出来,并寄回赫尔辛基,因为只有芬兰银行才能决定何时淘汰一张破旧的帕沃·努尔米(Paavo Nurmi,这位伟大的跑步运动员出现在现有芬兰钞票上)并印制一张新的。
硬币磨损没那么快,所以硬币上印有国家头像不会带来同样的问题。欧洲反面(背面)的设计方案是一个大数字旁边有一个地图:在全球上的欧洲,或者分解成其组成国家,或者没有边界地统一,这取决于面值。各国可以自由决定硬币的正面(头像)。
因此,从2002年开始,硬币将像一种化学染料,追踪人们在欧元区的流动。有朝一日,你会在法国的口袋里发现一只被电击的鹰,并知道有德国游客曾到过附近。肯定也会有很多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的硬币,甚至可能有一两个胡安·卡洛斯。在处决路易十六两个世纪后,法国人将再次用印有君主肖像(而且是外国君主)的硬币购买面包。
不过,巴黎铸币厂预计,这里的绝大多数硬币仍将是令人放心的法兰西共和风格,而且是美丽的。“我们的首要挑战是让硬币变得美丽,”康斯坦斯说。“硬币在艺术层面上得到公众认可非常重要。”将会有新的玛丽安娜,她是共和国的典型象征,戴着(像“播种者”一样)弗里吉亚帽。新的玛丽安娜意在显得“意志坚强”,展现她建设欧洲的决心,但她看起来却有些男性化。新的“播种者”保留了旧版的外形,但她描绘得过于模糊,仿佛只是一件空荡荡的连衣裙。
从现在到2001年底,铸币厂的目标是生产76亿枚欧元硬币,总重3万吨,这将需要近2英亩的储存空间。其生产能力已增加两倍;印钞现在是法国经济中最繁荣的行业之一。到2002年初,法兰西银行打算印制超过20亿张欧元纸币。其他国家也在进行类似的努力:整个欧元区将需要大约700亿枚新硬币和160亿张钞票。2002年1月1日之后,公民将开始在当地银行兑换旧币。总的来说,大约14万吨金属将从欧元区撤出流通,熔化并在世界市场上出售,但不会太快,否则市场将崩溃。
商业银行自然会比其他任何企业都更受欧元转换的影响,而且像铸币厂一样,他们已经准备多年,每个银行都有自己的“欧元先生”(或“欧元女士”)来指导这个项目。法国资产最大的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的“欧元先生”是罗伯特·布尔索。作为该银行的执行副总裁,他是一位充满活力、黑发的男士,长相英俊粗犷,略带好斗,正是法国人喜欢演员的那种形象。
我拜访他时,他刚从美国回来,在那里他向一群美国金融家解释了欧元将如何颠覆他们的生活:国际商业交易将很快像使用美元一样频繁地以欧元结算,欧洲股市也将很快变得比美国股市更有价值,因为投资将在欧元区内流动并从世界各地涌入,包括美国的养老基金。(投资者会乐于只关注一个汇率,而不是11个。)这项启蒙任务显然让布尔索乐在其中。他说,不久前,他的美国同行都没有认真对待欧元;现在他们总是打电话向他征求意见。“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经济集团,”他说,“它不仅仅是货币的技术性变革。”
但是,要建立一个在全球市场上与美国抗衡的经济集团,布尔索和其他欧洲银行家们首先必须经受住技术变革的考验。1999年1月1日,欧元将成为欧元区的法定货币,各国货币之间的价值将不再波动,而是成为欧元的固定百分比;而欧元本身将以12月31日下午2点欧洲货币单位(ECU)的任何价值固定。资本市场将转向欧元,银行将开始以欧元进行相互交易。但是,实际的硬币和纸币要到2002年1月1日才能到达银行客户手中。“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管理三年的两种货币价值表达,”布尔索说。“我们将不得不一下子重新设计我们所有的软件,使其能够处理法郎和欧元这两种金额。这就是困难所在。”
通往欧元之路还有其他软件障碍。例如,将美元兑换成法郎需要乘法——大约1美元兑换6法郎。但将美元兑换成欧元则需要除法,因为大约1欧元兑换1.1美元。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是世界领先的货币兑换商之一,其现在进行美元-法郎兑换的程序无法进行除法:它只设计用于乘法。在了解了几个这样的例子之后,你开始明白为什么布尔索有数百人致力于准备法国农业信贷银行使用的数万个软件程序。然而,只有在12月31日下午,他们才能精确地知道一欧元有多少法郎;然后他们将利用假期周末切换银行的所有账户。
三年后将面临不同的危机。“我们有1700万客户,”布尔索说。“我们必须更换他们口袋里的所有钞票。当我说口袋里时,我还指他们藏在家中角落罐子里的所有钞票,因为法国有很多人这样做。所有这些人都会来到我们的出纳员面前。为出纳员供钞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估计需要800辆布林克斯(Brinks)运钞车。而且这些兑换不会是整数,它们需要计算和找零等等。我们最担心的是每笔交易将耗费的时间。”
同时,银行的所有自动取款机都必须在2002年1月1日左右进行技术人员访问——不能提前,因为在此之前它们必须吐出法郎,也不能推迟太久,否则会有愤怒的客户。除了将其软件切换到欧元版本外,每台机器都需要新的欧元纸币墨盒,因为欧元纸币与法郎的尺寸不同。钞票夹持滚轴也必须调整,因为欧元将印刷在更厚的纸张上。届时,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必须向商家提供新的硬币。否则,当第一位携带欧元的顾客到来时,收银员将无法找零。
对于欧元区各地的商家来说,地狱始于2002年1月2日。在三年的过渡期内,他们或多或少地一直在做准备:张贴欧元和法郎两种价格以适应顾客,分发宣传册,如果规模足够大,还会为员工举办培训课程。欧尚(Auchan)是法国非常受欢迎的“大型超市”连锁店之一——规模大到有些店的员工需要乘坐旱冰鞋穿梭——最近开始开设课程,让员工玩一种大富翁式的棋盘游戏,以奖励那些精通欧元的人。
但是,到了2002年,乐趣将止步,届时欧元和国家货币将并行流通。在法郎退出流通的同时,商店将被要求接受两种货币。他们将不得不设立单独的结账通道,或者投资带有两个抽屉和双重计算功能的收银机。对于我当地的面包店或报摊来说,欧元可能是他们首次投资收银机的动力。在所有商店,人们都可以预见到排长队和 нервная 紧张。
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个过渡期最长不超过六个月:国家货币的有效期不迟于2002年6月30日。(之后,如果你在床垫下发现一笔钱,你仍然可以在中央银行的办事处兑换。)然而,转换过程很可能会比这快得多,可能只需几周时间。一些大型零售连锁店希望一夜之间完成转换。但他们遭到了另一个利益集团的反对:自动售货机行业。可怜的自动售货机所有者们正面临一个痛苦的问题:何时是将他们的机器切换到欧元的最佳盈利时机?这个问题无法回答,因为没有人能预测欧元将以多快的速度“渗透”到自动售货机用户的口袋和日常生活中。该行业的游说者已要求政府在2002年期间继续提供旧硬币,并警告公民携带两种金属硬币。他们提出了一个可怕的景象:愤怒的消费者无法买到可乐或避孕套(这里常见的自动售货机商品),将怒气发泄在机器上,是的,但最终会将怒气发泄到整个欧洲统一进程上。根据欧洲自动售货机协会的数据,欧盟有320万台自动售货机和700万台其他接受货币的机器,如停车计时器和付费电话。“一千万个投币器不可能在一天内更换,”该协会说。
2.9亿人也不能。
那些拥有自己的“钱兔”——经验丰富的世界旅行者——的人将立即看到欧元的好处。“想象一下,如果你从纽约去波士顿都得换钱,”布尔索说。“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欧洲的生活!”但这里没有人会低估欧元所要求的调整程度,至少在心算方面是如此。“想象一下,美国的价格突然不再是美元,而是比索。你需要时间来适应。”
转向欧元将像生活在一个外国,学习一门新语言。而且它不仅仅涉及算术上的挣扎。一天早上,我与巴黎大学的年轻社会学家斯迈恩·拉切尔(Smaïn Laacher)喝咖啡,他是欧盟委员会召集的一个社会科学家小组的成员,旨在思考欧元可能对人们——欧盟委员会指消费者——产生的影响。但拉切尔解释说,金钱远不止是一种消费手段。“它是社会凝聚力的一个要素,”他说,“它也是一种认同要素——人们通过它来认同国家。有了欧元,我们正在从一个宇宙走向另一个宇宙,因此这种认同体系将会受到扰乱。”
拉切尔说,正如民族主义在那些对其他国家知之甚少的人身上往往表现得更为强烈一样,对货币的依恋可能对那些换汇经验较少,以及对任何形式的货币经验较少的人——穷人——更为重要。拉切尔投票支持欧元,但他非常担心这次转换会搞砸——由此产生的政治阻力将有利于极端主义者的崛起。国民阵线,这个反移民、反全球化、强烈反欧元的政党,最近在法国选举中声势日渐壮大。
拉切尔和这里的其他人强调,欧元没有历史先例。欧洲人在罗马帝国时期曾享有共同货币,在拿破仑时期也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但这些跨国货币在根本上与今天的国家货币没有区别。“货币一直以来都是由军事力量或政治力量保障的东西,”雅克·比鲁斯特(Jacques Birouste)说,他是南泰尔巴黎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与拉切尔同在欧盟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会任职。“首先界定领土,然后施加权力来规范商品和货币的交换。但欧元并非按照这些历史轨迹组织:货币是首先被界定的,而不知道它所指的身份是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创新的局面——所以这是一个极端的局面,一个充满风险的局面。”
比鲁斯特将欧元区公民比作他作为心理学家研究过的一群人:试飞员。“这个类比在于冒险,”他说。“我们将被迫放弃受国家保护的身份,投入一场冒险去寻找另一个身份。”明年一月在银行长队中抱怨的人们;在拥挤的超市货架前茫然盯着价签的购物者;加班的布林克斯运钞车司机和自动售货机维修工——所有这些人都将半自觉、半自愿地为一次巨大的集体信仰飞跃做好准备。
信仰什么?在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我找到了一个答案,尽管是个人而非官方的:一位名叫弗朗西斯·沃林(Francis Woehrling)的经济学家。沃林出生于战前阿尔萨斯的一个日耳曼语环境中,成长为法国人,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接受经济学教育,他回到欧洲是因为他想帮助建立一种欧洲货币和一个欧洲联邦。他说,欧洲人将相信并将其新身份的源泉视为欧元本身——以及新的欧洲中央银行,相当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
欧洲中央银行理应比美联储更能独立于政治干预。当失业率高企时——今年春天法国的失业率多年来首次降至12%以下——政客有时会忍不住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向中央银行家施压,要求降低利率,以期鼓励增长和消费。但从长远来看(根据沃林和其他货币主义者的观点),这种政策只会助长通货膨胀。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中央银行将有权抵制这种压力。它将超然于纷争之外,通过主导货币供应的缓慢稳定增长来追求其控制通货膨胀的首要指令。它将拥有这样做的权力,因为欧元区的货币供应量将足够大,不会过多地受国际货币市场异想天开的影响——尤其不会受美联储行动的影响。沃林认为,这种实力将有利于欧洲经济,也将有利于欧洲心理。
“在欧洲,我们曾以为可以随意操纵金钱,所以我们做了各种错误的决定,”他说。“许多人相信政府可以介入并解决失业问题,我们曾有中央银行四处奔走,表现得好像他们可以做些什么。现在,我们不再有这些伤害我们的神经质父母,我们突然有了一个非常可靠的父亲——欧洲中央银行。我们将认同这个非常理性且强大的父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正在成长。我们不再是一群争吵不休的人。然后我们会说,‘我们为此感到自豪。’”
“美国人拥有《宪法》、《独立宣言》、边疆和西进运动——这都是美国的一部分。联邦储备银行本世纪才成立。所以在美国货币出现之前,美国有150年的时间来思考美国。但在欧洲,我们没有向西走的马车:我们有钱。那将是某种‘我们能行’的可见标志。”
“所以,我认为这种新身份的组成部分是:‘我们是高度发达、理性的人民;我们解决了其他任何人都没能解决的复杂问题。我们将为世界提供一种稳定的货币。我们能行。’”
5月初,各国政府首脑在布鲁塞尔开会宣布欧元区成立,仪式因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人选之争(法国对所有挑战者)而演变成一场争吵,这一新闻与法国报纸头版另一条新闻争夺版面:巴黎学生起义三十周年。整个1998年5月,报纸每天都用整版篇幅详细回顾1968年5月。电视屏幕再次充斥着学生占领索邦大学、拆毁铺路石建造路障、被警察殴打、以及在烟雾缭绕中解释只有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满足他们的黑白画面。很难从中找到任何相关的意义,但一些评论员仍然尝试了。《世界报》在一篇社论中认为,98年5月的革命——欧元——是68年5月的延续,或者至少是其中一个支流的延续。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支流,而是另一个:代表着对想象力的呼唤,代表着个人自由和对世界的开放,用两个五月都经常重复的口号“要现实:要求不可能”来概括。
在欧洲历史的背景下看,也就是说,在几个世纪血腥战争(没有比这次更血腥的了)的背景下看,欧盟是一个不可能变为现实的事物。欧元是该项目中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步。最近,它被视为欧洲在全球化经济中唯一的希望,但这并非最初的想法。最初的想法是不再重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元,除其他外,是一项历史性的理想主义行动,它能够团结像赫尔穆特·科尔和丹尼尔·科恩-本迪特(1968年5月起义的魅力领袖)这样多元化的政治家。科恩-本迪特现在是欧洲议会的绿党成员,他是欧元的积极倡导者;他甚至合著了一本公民手册。该书在一处写道:“在20或30年后,当欧洲身份扎根时,欧洲人将对欧洲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愿景。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将像巴伐利亚和普鲁士之间……或布列塔尼和卢瓦尔河之间一样不可思议。”
也许吧——但从金钱开始的想法仍然显得奇怪。也许这最终会被证明是高明的:也许金钱,这个足够难以达成一致的东西,将成为规避民族主义者沉默,并建立更深刻的新事物——一个欧洲联邦——的手段。欧洲人作为试飞员,欧洲人作为乘坐印有其中央银行标志的马车西进的拓荒者——更准确的形象可能是另一种“钱兔”:作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心理学实验中的实验室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