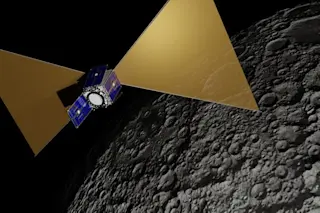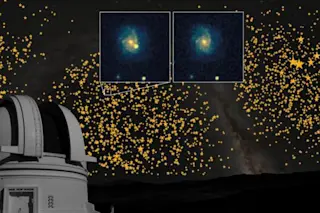这张摄于1950年8月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照片,展示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奥地利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并肩而立。两人都望着镜头。爱因斯坦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衫和一条用吊带固定的肥大长裤。他的身体有些佝偻。哥德尔则穿着一套白色亚麻西装,戴着一副猫头鹰般的眼镜,显得精瘦而近乎优雅,他表情的严肃被脸上一种奇特的性感所柔化。两人神态自若,配合着摄影师。显然,他们是朋友。他们相识并不令人意外。他们都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成员,办公室也很近。作为第三帝国的逃亡者,他们都感受过历史的严酷气息,并且共同拥有丰富、浑厚的德语,一个以歌德而非莎士比亚为记忆枢纽的语言世界。尽管爱因斯坦是物理学家,哥德尔是数学家,但他们都拥有超越各自学科的智识上的胆识。
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于1931年发表,当时他年仅25岁,如同15年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重写了现代科学的基本规则。哥德尔证明了,初等算术是不完备的,而且将永远不完备。无论你基于哪个公理系统进行计算,总会有一些真理陈述超出了该系统的范围。将这些陈述作为额外的公理添加到系统中,也无济于事。扩展后的系统仍然是不完备的,这种“感染”会循序渐进地向上蔓延。
爱因斯坦曾对博弈论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奥斯卡·摩根斯坦说,他之所以去高等研究院,主要是为了能和哥德尔一起走回家。(“Um das Privileg zu haben, mit Gödel zu Fuss nach Hause gehen zu dürfen.” 原始德语中有一种温和的敬意,难以完全翻译。)他们经常这样做,直到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然而,他们的科学上的亲近感却源于深刻的个人差异。爱因斯坦是一个毫不动摇地自信的人。哥德尔则在争议面前退缩,并两次精神崩溃;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他是个体弱多病的人,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则是个疑病症患者。1933年两位老人相遇时,年轻的哥德尔的才华尚未走出学术的象牙塔,学术界只是窃窃私语。另一方面,爱因斯坦已经54岁,接近他创作生涯的尾声。尽管他仍保持着一种无所畏惧的玩乐精神,但也获得了一种大理石般的庄重感,超越了名声本身,成为本世纪的神话人物之一,他那圆润、忧郁的脸为全世界所熟知。
这些差异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友谊的性质上。在写给传记作家卡尔·塞利希的信中,爱因斯坦的秘书曾提到,每当爱因斯坦出现在研讨会或会议上时,都会引起“敬畏的寂静”。即使是言辞犀利的沃尔夫冈·泡利(另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也无法将这位伟人当作凡人对待。哥德尔似乎也持有某种类似的态度。在他写给母亲的信中,他似乎很乐意地证实,通过与爱因斯坦的友谊,他正沐浴在“反射的光辉”中。“我至今去过他家两三次,”他在1946年写道。“我认为他很少邀请别人去他家。”
然而,在他们宏伟的科学成就中,爱因斯坦和哥德尔都孤军奋战,所以他们的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别无他人可以倾诉。尽管他们谈话的内容已失传,但我们可以想象,在那漫长的晚间散步中,他们至少会讨论一个话题。1948年,哥德尔将目光投向了爱因斯坦最杰出的创造——广义相对论,并成功地从其符号的蒸馏器中提炼出了一个全新而辉煌的宇宙。他通过提供一个精确的方程解来做到这一点——这个场方程允许计算引力场的强度——而他的分析体现了他所有工作的独特特征。它原创且逻辑连贯,论证清晰,却具有完全而令人信服的权威性。一种精湛的品味贯穿始终。没有炫技。
这很奇怪。非常奇怪。
广义相对论的核心思想——时空的融合——并不难理解。毕竟,时空在日常生活中也已经融合了。我们定位一个事件(例如,肯尼迪总统遇刺)既涉及它发生在哪里(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也涉及它发生在哪里(1963年11月22日下午约1:30 EST)。三个数字足以在一个三维地图上标记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空间:经度、纬度、海拔。如果再加上一个数字——时间,这个地点就被定位为一个时空中的事件。如果一个事件可以用四个数字来定义,那么一系列事件就可以用一系列这样的数字来定义,它们就像大象排成一列那样一个接一个地跟随。
广义相对论随后在时空的几何形状与时空内运动物体的行为之间建立了遥远的联系。想象一下,一块弹珠放在床垫上。轻轻一碰,弹珠就会直线滚动。但如果也在床垫上放一个保龄球,弹珠即使受到同样的轻击,也会沿着下陷的表面滚动,其路径从直线变为曲线。保龄球的重量会使床垫的介质变形,而变形的介质会影响弹珠的运动。
将保龄球和弹珠换成行星、恒星或旋转的星系,将床垫换成时空本身,一个普通的比喻就变成了伟大的物理学理论的核心原理。在一个没有大质量物体的宇宙中,时空没有变形,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是直线。当物质出现时,最短路径就会弯曲。这一理论的第一个也是最受称赞的验证发生在1919年,当时天文学家证实,太阳的质量会导致光线弯曲,正如爱因斯坦所预测的那样。
“对我们这些相信的物理学家来说,”爱因斯坦曾写道,“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区别只是一种幻觉。”这是一个忧伤的说法,是在爱因斯坦临终时所说,但它直接源于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想象一下,一群观察者随意地散布在宇宙中。每个人都能够将自己生命中的事件组织成一个线性顺序——即上面描述的世界线。每个人都坚信自己的生命由一系列“现在”组成,这些流动的时刻从过去到现在的流向未来。狭义相对论提出了相反的说法。散布在时空中的观察者都确信,他们的“现在”感是普遍的。“现在”毕竟就是“现在”,不是吗?显然不是。时间流逝的速度取决于一个人的移动速度:当地球上过去一个小时时,在一艘以近乎光速远离地球的宇宙飞船上可能只过去了区区几秒钟。完全有可能,一个人的“现在”可能是另一个人的过去或未来。
哥德尔对场方程的解, vindicated 了爱因斯坦理论最深刻的洞察,即时间是相对的。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只表明,时间不存在于传统的意义上,而不是说时间完全不存在。爱因斯坦的论点更为微妙。他认为变化是一种幻觉。事物不是“成为”,不是“曾经”,也不是“将要成为”:它们仅仅“是”。时间就像空间;它完全就像空间。我去新加坡旅行,并不是把新加坡带入存在。我到达新加坡,但这座城市一直都在那里。同样,我通过在时间中位移来到达未来的事件。我并没有把它们变成现实。如果没有任何东西被创造出来,那么就没有变化。